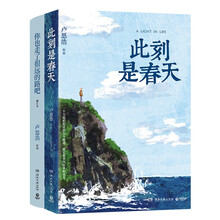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杂文卷》:
日前读到台湾柏杨的一篇文章,他认为华人是一个喜爱吵闹的群体。他说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那一定是中国餐厅。如果你去某会场,主席台上的人在吼,台下的人在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也不用问,一定是华人的地盘。这种感觉其实不只是柏杨有,好多在国外呆过的人都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朋友曾称,他在回国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处在吵闹的包围中或噪音的天罗地网里。走在北京街头,随处都可听见秧歌的锣鼓和唢呐声;走进商店,到处都是“赔本甩卖”的吆喝声;长途客车或火车上,总有一些久经沙场的“大嗓门”来显示他的卓越;即使是黄山、峨眉山这样号称“天下幽”的风景区,也会有导游小姐的大喇叭和极不协调的音乐为你伴行。
这是人的素养和习惯问题,不那么好办,厌烦吵闹的人认为这是吵闹,喜欢它的人则认为是热闹。北京街头那些扭秧歌的老头老太,就听着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唢呐声才觉着舒服,一日不听,一夜难眠。那正月里的庙会,人挤人,人挨人,推推搡搡,闹闹哄哄,其实什么名堂也没有,可就有人喜欢得不行,他们要的就是这么个热闹。再说中国人的住房大都爱往人多的地方挤。早年上海有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现在浦东开发了,大家又一个劲往浦东挤。北京亦然,哪片小区人满为患,哪片小区房价死高;反之,偏处一隅的地方白送一个大客厅也没有人要,人家图的是人气旺,人气旺者热闹也。
这就是中国人的特色,在实质性的问题上从骨子里透着一种冷漠,而外表却追求虚浮的热闹,以至到了对吵闹也觉着可爱的地步。
世界本是平静的,所谓的热闹都不过是人制造出来的,并夹带着人的某种企图。那种耍猴卖艺的入,总是先打个场子,敲一阵锣鼓,把人招来,然后才开始玩耍,人越多他越耍得来精神,因为给钱的人也会越多。商家、歌厅门前常播放着高分贝的音乐,以致响过半条街去,为的是引得人们的注意,只有多人注意了,这生意才有开头。红白喜事的热闹那是一种宣言和告示,知晓和凑热闹的人越多,越显示其隆重、热烈和风光。
其实,制造热闹不只是民间的,官方更多更排场。什么文化节、艺术节、民俗节无日不有,每值此时,那些举办城市如同过年,又是搞卫生,又是整街容,又是插彩旗,又是扯标语,风风火火,好不热闹。
一个什么检查团或什么要人要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也会搞得很热闹,整治街容,扯大标语,交通管制,晚上如同过节一样满街灯火通明。领导作报告或发表什么讲话,绝不像克林顿那样,独自一人往白宫草坪上一站就开讲,咱们得把气氛营造得很热闹,庞大的主席台上插着旗帜,摆着鲜花,坐满要员,会场里演奏着各种音乐,报告期间总是不时地鼓掌,掌声稀少时,报告人在适当的地方就将嗓门提高,直至大吼,以强调重视,从而赢得掌声,用掌声来说明其讲话的重要。如逢什么重大纪念日,那就更要大造一番热闹了,报刊影视总是抢先一步铺天盖地地大发一通相关的消息、通讯、专题、图片、系列片之类,之后便是举行各种类型的群众文艺活动,载歌载舞,庆祝升平,再下来举行纪念大会和能够充分展示其“伟大意义”的仪式,红旗猎猎,鲜花如潮,人山人海,乐声震天……要使得人们在这种轰轰烈烈中无法不感到这是一个非凡的时刻。不错,形式确实能起到渲染主题的效果,但我还是要说,这一切都不过是制造出来的热闹,是一种虚热闹,因为它不完全代表民心和民愿,更不完全是人们自发起来进行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