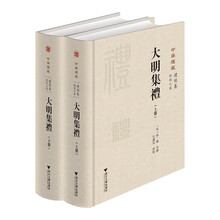《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翻译文学卷)》:
昏黄的冬日来临了,四处弥漫着无聊。铁锈色的大地上铺着一层白雪,犹如一条磨得露出织纹的寒碜的桌布,上面满是窟窿。这张桌布不够宽大,有些屋顶依然暴露在外,它们就这样屹立在那里,有的呈黑色,有的呈棕色,有的是木椽顶,有的是茅草顶,像一艘艘载着被煤烟熏黑的大片阁楼的小舟。这些阁楼如同密布着肋骨似的椽子、屋梁和桁梁的漆黑的大教堂,椽梁就像冬天的阵风用来呼吸的黑黢黢的肺。每天黎明时分,那些在夜间就已浮现、被夜风吹鼓了气的一排排崭新的烟囱和烟道(像魔鬼手风琴上的黑管)便清楚地露出原型。扫烟囱的人总是摆脱不掉乌鸦的纠缠,它们在黄昏时分就已经密密匝匝地趴在教堂附近那些枯叶尚未脱落的黑色树枝上。这些乌鸦经常在空中扑簌簌地飞上一圈后又绕回来,每只鸟儿都紧紧地贴在树枝上自己占据的那块位置上,黎明到来后才成群地飞走,像阵阵煤烟和片片尘埃,忽高忽低,变换出各种奇形怪状,不绝如缕的呱呱的哀鸣声把一道道霉黄的亮光叫得黯然失色。随着寒冷和无聊袭来,日子开始变得更加坚硬,像陈年的面包。人们开始兴味索然、慵懒冷漠地拿钝刀切这种面包。
父亲开始足不出户。他封起那些炉子,研究起永远捉摸不定的火的本质,体验舔舐烟囱出口闪亮的煤烟的冬季火蛇的成咸的金属味和烟气味。那段时间,他总是在不同房间的某个高空地带痴迷地干着形形色色的修理小活儿。你在白天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看见他蹲在一把梯子的顶端,在天花板下面,在长窗上方的檐板旁,在吊灯的平衡锤和链条旁边鼓捣着什么。他模仿室内油漆工的做法,使用的是像两只巨大高跷的梯子。他觉得可以那么近距离地仰看漆有天空、树叶和鸟儿的天花板简直开心极了。他开始与各种实际事务渐行渐远。母亲对此感到忧心忡忡和闷闷不乐,试着引诱他谈点儿什么,谈一谈月底到期的账单之类的事情。这时,他总是听得心不在焉,神情迷惘,面露焦虑之色。有时,为了跑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把耳朵贴到地板的一条裂缝上,他会做出警告性的手势,拦住母亲继续往下讲,还竖起双手的食指,强调这种调查的重要性,接着又开始专注地聆听起来。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些古怪的举动后面那个令人伤心的根源,以及在他内心已经酝酿成熟的某种悲哀情结。
母亲对他完全束手无策,可是他对阿德拉却恭敬有加,非常在意。对他来说,打扫自己的房间是一项伟大而重要的仪式。他总是提前做好安排,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带着恐惧与喜悦交加的兴奋感注视着阿德拉的一举一动。他认为阿德拉的所有动作都蕴含着一种更深刻的象征意义。那个姑娘用青春而决然的姿势在地板上推着那根长柄刷移动的时候,父亲简直不堪承受。这时他泪如泉涌,无声的笑意把他的脸都给扭歪了,嫉妒的喜悦冲击得他的身子直打哆嗦。他兴奋得浑身发痒,几乎快要疯狂了。阿德拉只要向他晃一晃手指头,装出挠痒痒的样子,就能把他吓得惊慌失措,穿过所有的房间,砰砰地关上身后的一扇扇门,最后倒在最远的那个房间的床上,在阵阵痉挛性的大笑中一个劲儿地打滚,想象着那种他觉得难以遏制的挠痒。因此,可以说阿德拉摆布父亲的力量几乎是无限的。
那时,我们第一次注意到父亲对动物有一种如痴如醉的激情。最初,这是一种猎人和艺术家浑然不分的激情。这恐怕也是一种生灵对另外一种血缘相近但并非同类的生命形式在更为深邃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惺惺相惜,是在某个未曾勘探过的生存领域进行的试验。只是到了后期,情况才发生了离奇、复杂、完全邪恶和有悖自然的转折,这种转折最好还是不要在此公之于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