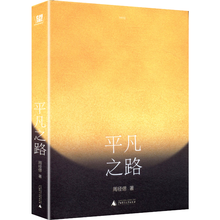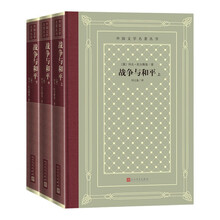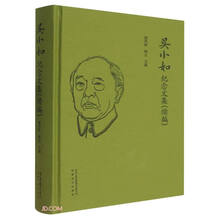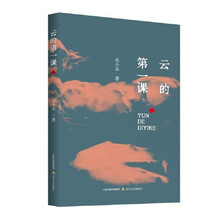第二天早起,我到井台绞水。老曹问我:“夜黑地的羊羔肉你咋能咬下?我从夜黑地直煮到今早上,尔格还咬不下。你该顶个生吃了么?”绞满水,他担上走了,慨叹道:“娃娃们凄惶的。”慨叹磨盘样沉,井水样清纯。
老曹问我好,是不放心我,他希望我样样项项都好,生怕有一星半点不好。
插队那会儿,我们踩着雪进沟拾柴,天黑实了,人没回来,急坏了曹老汉。他走出村,反穿皮袄,官路边候着。我推柴车推得头晕眼花,猛不丁见路边蹴着个白糊糊人影,吓得泼骂起来。老汉当下没言传,后来对旁人讲:“小高可把我骂结实了。”下乡七年,那样结实地骂人,我也就这一回。
农田基建兴修水利,爬坡掏冻土,他不放心我们,怕被冻土砸着,自己拎一把镢头上去了。微驼的背,罗圈腿,右手拇指一个大肉瘤。口中“嘿嘿”地叫着,看上去动作不快,却有力有效。三年过去了,我们也可以把镢头抡得“嘿嘿”地,蛮像那么回事,碰巧了,还能放下桌面大小的冻土。老曹显见得老了,拔一棵油菜,要往手心吐三回唾沫。
一年初秋,女知青小向深夜拎一盏马灯进阳岔沟观察虫情。老曹听说了,急忙派人寻回来,黑着脸在社员会上美美批评一气。可是,灾难并不因为他格外留神就不降落到知青中间。猪场的小柳给刚下猪崽的老母猪砍青榆叶,从七米五高的土崖上摔下来,颈椎骨折,胸以下高位截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