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俊俏聪明,家道殷实,家庭舒适,性格又开朗,人生中多种至高无上的幸福,似乎都汇聚在她身上了。她在世上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她是小女儿,上头有一位姐姐。父亲再慈祥不过,对女儿百依百顺。姐姐出阁时,爱玛年纪虽小,却自然而然成了家中的女主人。她母亲去世太早,因此母亲的种种爱抚,她只有丁点儿朦朦胧胧的印象。母亲的空缺由一位家庭女教师来填补。这可是位贤德女子,对爱玛关爱有加,丝毫不逊于一位慈母。
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中一下子就过了十六年,与其说是一位家庭教师,还不如说是位挚友。两位千金小姐她都十分喜欢,对爱玛感情尤深,两人之间,更多的是一对姐妹似的亲密关系。即使在泰勒小姐名义上仍算是家庭教师时,由于脾气温顺,她几乎就没做出过要管束的架势;如今,师道尊严的影子更是早就荡然无存。两人就像一对贴心朋友般朝夕相处,爱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泰勒小姐的意见她是十分尊重的,但大主意都由自己来拿。
若说爱玛的处境有什么可虞之处,那就是她有权任意率性而为,并且对自己的估计往往略为偏高。这些毛病自然会对她的许多人生乐趣造成损害,不过目前尚未被她察觉,远没有列为可能给自己带来祸害的根源。
不如意的事还是来了——尽管那来势还不算太凶太狠——也远非以让人憎厌的形式出现。泰勒小姐结婚了。失去泰勒小姐使爱玛初次尝到哀愁的滋味。在好友大喜的日子里,爱玛破天荒第一遭闷闷不乐兀自久久呆坐。婚礼完毕后,一对新人离去,剩下父亲与她共进晚餐,漫漫长夜,绝无指望还会有第三个人来,让气氛可以变得活跃一些。饭后,父亲像往常一样,安定下来,准备就寝。爱玛只能怅然枯坐,默思自己的损失。
这桩婚事,她的好友获得幸福的前景是不容置疑的。韦斯顿先生人品出众,家境优裕,年纪相当,举止谦和有礼。当初自己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也曾殚精竭虑,没少花气力。想到此处,她多少有些得意,殊不知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从今以后,每一天的每一小时,她都会感到失去泰勒小姐的伤痛。她回想起泰勒小姐的情谊——十六年的仁爱与深情厚谊呀——从自己五岁起泰勒小姐就如何教她,带领她玩耍——在她健康时如何全心全意地爱她,让她快乐——她幼年体弱多病时又如何精心照料,使她痊愈。这上头她欠的情分是还不清的呀。然而,最近七年的交往,紧接着伊莎贝拉的出嫁,只剩下她们俩。两人相依为命,平等相待,开诚相见,这个阶段的大事小事就成了更加温馨、更为亲切的回忆。泰勒小姐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朋友与伴侣:天资聪颖、见多识广,能干且又乐于助人。性情温和,家务事无一不精,对这家人的事还真的很上心,对爱玛更是特别地关怀,包括她的每一种喜好与每一项行动计划。爱玛每生出一个想法都可以推心置腹向她倾诉。她又是这么挚爱自己,对这种爱,你简直是一点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这样的变化叫她怎么能忍受呢?不错,她好友新的住处距离自己家只有半英里;但是爱玛知道,住在不到半英里外的一位韦斯顿太太跟住在自己家的一个泰勒小姐,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尽管自己天生禀赋与家庭条件都算不错,现在却不免要面临精神孤独的苦恼了。她自然是挚爱父亲的,不过他可做不了自己的伴儿,无论是谈正经事还是说笑话,他都跟自己不怎么接得上茬儿。
父女俩年龄上差距太大(伍德豪斯先生结婚相当晚),这一不利条件再加上他体质与生活习惯上的因素,就使问题更显得突出了。父亲从小便体弱多病,身、心双方面都缺乏活力。他暮气沉沉,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老上许多。尽管他因为心地善良,脾气和顺,去到哪里都受到欢迎爱戴,却从未因才智出众而为人敬重与称道。
爱玛的姐姐结婚后虽说住得不算很远,就在伦敦,距离不过十六英里,但绝不是天天可以见到的。爱玛得在哈特菲尔德熬过多少个十月、十一月的漫长黄昏,才能等到圣诞节来临呀。只有在那时,伊莎贝拉夫妇才会带着他们的几个小孩回来,使家中充满人气,也让她能享受到与人交往的乐趣。
海伯里是个地盘很大、人口众多的村子,几乎顶得上一个乡镇了。哈特菲尔德尽管有单独的草地、灌木丛和宅第名称,实际上还是海伯里的一部分。而偌大一个海伯里,居然就找不出一个能和爱玛旗鼓相当的角色。伍德豪斯家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大户,全村人都敬重他们。她父亲对谁都客客气气。爱玛在本地认识的人不少,但是在她看来,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能替代得了泰勒小姐,哪怕只替代半天也不成。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变化呀。爱玛对此只能唉声叹气,妄想有奇迹发生。一直到父亲睡醒过来,她才赶紧收起愁容,强作欢颜。父亲精神上需要有人支持。他神经脆弱,极易心情沮丧。处熟了的人他就是喜欢,谁走开他都老大不愿意。什么样的变化他都不想见到。结婚必定会带来变化,因此总让他感到不痛快。对自己大女儿的结婚他至今怨气未消,一说起她仍然是一副哀恤悲悯的口气。其实那全然算得上是一场美满姻缘。而现在呢,他又不得不与泰勒小姐分手作别了。出于自己多少有些自私的脾性,而且又压根儿想不到别人没准会有跟他不一样的考虑,他一门心思认定泰勒小姐做了件对自己对他们都是可悲的事情,若是她这一辈子都在哈特菲尔德度过肯定会幸福得多。爱玛尽力现出笑容,尽可能快活地说东说西,不让父亲往这上头想;可是到了用茶时分,父亲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午饭时说过的话照样说了一遍:“可怜的泰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回到这儿来。韦斯顿先生居然会注意到她,这真是糟糕之至呀!”
“我可没法赞同您的看法,爸爸;您知道的,我没法赞同。韦斯顿先生是那样一个性情温和、讨人喜欢、出类拔萃的人,正该娶上一位好太太的。你不至于想让泰勒小姐随我们过一辈子,忍受我的种种怪脾气,不让她有自己的家吧?”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又有什么好?这里有那儿三倍那么大呢;再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怪脾气嘛,我亲爱的。”
“我们可以经常去看他们,他们也可以经常来!见面的机会多的是!我们可得先去。我们得尽早拜访新婚夫妻。”
“我亲爱的,这么远叫我怎么去?兰德尔斯可不近。我连一半路都走不动的。”
“唉,爸爸,谁说要您走去了。我们自然是坐马车去啦,这是不消说的。”
“马车!可是为这么一小段路,詹姆斯是不会乐意套车的。再说,我们做客时,那对可怜的马儿又安置在哪儿呢?”
“拴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不就得了,爸爸。您很清楚这些事儿早就安排妥了。昨儿晚上都跟韦斯顿先生说好了。至于詹姆斯,您尽管放心,他还巴不得去兰德尔斯呢,因为他闺女就在那儿当侍女。要是让他送我们去别处,那倒还真不好说了。这件事全亏得您呀,爸爸。您给汉娜找到个好去处。谁都还没想起,您就推荐了汉娜——对您,詹姆斯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
“当时想到了她我确实很高兴。事情倒也真是凑巧,因为我无论如何不愿可怜的詹姆斯认为我们没把他的事放在心上;而且我拿得准这姑娘一定会出落成一个非常好的仆佣的;她很有礼貌,嘴巴也甜;我对她印象不错。她一见到我,总是行屈膝礼,向我问好,模样儿真讨人喜欢;你让她来做针线活儿那阵,我注意到她总是轻轻扭上门把儿,从不砰地一推就算。我看准了她会是一个好侍女的。再说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这也是个莫大的安慰,总算身边有个过去看惯的人呀。你明白吧,不管詹姆斯何时去看女儿,泰勒小姐都会听到我们的消息。我们谁有什么事儿,他都会一五一十向她禀报的。”
爱玛费尽心机让这些较能让人高兴的思绪维持下去,千万别戛然中断。同时希望借助十五子游戏,让父亲好歹度过这个艰难的夜晚,莫再为别人女儿的事懊恼操心。十五子棋局摆好了,可是紧接着走进来一位来访者,这就使得棋桌派不上用场了。
奈特利先生是个三十七八岁、颇有见地的人,同这家人不仅是认识已久的至交,而且还有着特殊的亲戚关系,因为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哥哥。他住在离海伯里一英里左右的地方,是这儿的常客。他每次来总是受欢迎的,这一回比平日更受欢迎,因为他是直接从伦敦与他们都有关系的亲戚家过来的。他外出数日,回来后晚饭吃得很迟,然后又步行来到哈特菲尔德,报告说布伦穗克广场那边大家都很安好。他来得正是时候,让伍德豪斯先生高兴了半天。奈特利先生兴致勃勃,和颜悦色,总能让伍德豪斯先生心情好转。老爷子提出的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和她那几个孩子的问题也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之后,伍德豪斯先生心存感激地说:“你太好了,这么晚了还出来看望我们。只怕路极其不好走吧。”
“哪儿的话,先生。今晚月色很美,天气一点也不冷。我离你们烧的旺火可得远一点呢。”
“不过你一定觉得路上又潮又脏吧。但愿你没有着凉。”
“脏,先生!你瞧瞧我的鞋,一星星泥点都没有沾到。”
“哦,那倒怪了,因为最近我们这里雨水可不算少。我们吃早饭那阵一场大雨足足下了有半个小时。我都提出让他们把婚礼推迟一下了呢。”
“哦,对了,我还没有恭祝你们快乐呢。我很清楚,你们双方必定感受到何等样的快乐,所以不急于表示我的衷心祝贺。我希望一切都很顺利。大家当时情况怎么样?谁哭得最厉害?”
“唉,可怜的泰勒小姐呗!这件事真叫人伤心唷。”
“对不起了,应该说是可怜的伍德豪斯先生和小姐吧;反正我不能说是‘可怜的泰勒小姐’。对你和爱玛小姐我都非常敬重。不过说到自立门庭还是仰仗别人的问题,只讨一个人喜欢总比要让两个人高兴更容易做到一些吧。”“尤其是两个人里还有一个是那么任性,那么纠缠不清呢!”爱玛开玩笑地说,“你心里准是这样想的,我知道的——要是我父亲不在边上,你也一准会这样说出来的。”
“我也相信一准是这样的,我的好女儿,”伍德豪斯先生说,还叹了口气,“恐怕有时候我真是非常任性和纠缠不清呢。”
“我的好爸爸!您可别以为我指的是您,奈特利心里想的会是您。您想到哪里去啦!哦,不是的!我说的不过是我自己。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错儿,这您是知道的——挑我的错儿逗乐——这全是开玩笑呀。我们相互之间总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事实上,能看到爱玛?伍德豪斯的缺点的人寥寥无几,奈特利先生恰好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是唯一敢于当面告诉她的人。虽然这事让爱玛心里不怎么舒服,但她知道,若是让父亲知道,只怕就不仅仅是不高兴的问题了。因此,她绝不愿意让父亲猜疑,自己的宝贝女儿并非是人人心目中的一个完人。
“爱玛知道,我从不对她乱说奉承话,”奈特利先生说,“可是我方才并没想批评任何人。泰勒小姐原先要讨好两个人,现在她只需获得一个人的欢心了。怎么说她也是赢家呀。”
“好吧,”爱玛说,但求这个话题快点结束,“你不是想知道婚礼的情况吗?我很乐意告诉你,因为我们大家都表现得不错。每一个人都准时到场,每一个人都喜气洋洋、容光焕发。没见到谁掉眼泪,显得愁眉苦脸的也是绝无仅有。啊,真的没有;我们只是想到两家才隔开半英里路,肯定会天天见面的。”
“亲爱的爱玛对什么都能处之泰然,”她父亲说,“可是,奈特利先生,对于失去泰勒小姐她其实是非常痛心的。别看她现在觉得没什么,以后会越来越不舍得的。”
爱玛把脸偏到一边,强自微笑,泪珠儿却忍不住挂了下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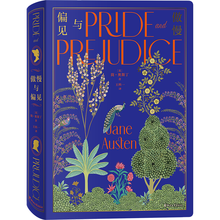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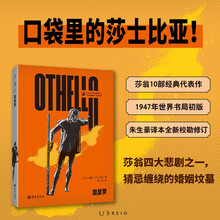
——英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凯特尔博士
在所有伟大的作家中,奥斯丁的伟大是难以捕捉的。
——弗吉尼亚·伍尔芙
简·奥斯丁的小说在许多方面达到了18世纪小说的尖峰。她将分别从内部和外部对人物进行刻划的描述的现实主义和评价的现实主义的种种优点结合起来,融汇于一个和谐的整体之中。她的小说充满着真实感,没有冗长的描述,也没有欺骗和诡计;她的小说富于对社会的机智议论,又没有喋喋不休的评论,她的小说还有一种社会秩序感,同时又没有损害人物的个性和自由。”
——伊恩·P·瓦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