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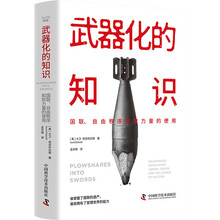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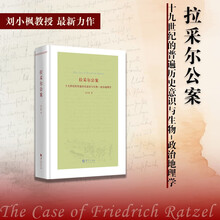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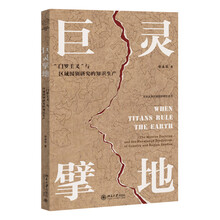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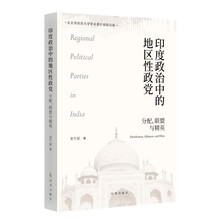


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柯克却满怀希望地期盼美国秩序的复兴,将其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上下纵横三千多年,不无洞见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西塞罗卓越过人,曾反对武力革命,失败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悖论的是,革命时代和制宪时代的美国人敬重这位带头抵制暴力变革的人。
因为西塞罗是有关“有秩序的自由”理论的代言人,而当时的美国人正试图实现有秩序的自由。他的作品被纳入美国人所接受的教育体系之中:在整个17和18世纪,对西塞罗的研习都是英国和美国教育科目的重心。他们学习的修辞是西塞罗式的,而且他们自己的大气磅礴的政治修辞术也是对西塞罗的模仿。另外,西塞罗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律师,而建国年代的大多数美国政治领袖都学习过法律,许多人还是执业律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在罗马时代对自然法理论进行过清晰阐释的是西塞罗,这一法律理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们至关重要。
西塞罗出身于骑士(equites或knights)家庭(骑士是指最初必须自带装备到罗马军队骑兵团服役的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公民),凭雄辩获得罗马共和国最高等级的公职。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为被独裁者苏拉的追随者错误地指控的人做辩护。西塞罗是那个堕落时代里难以被腐蚀的人,他的雄辩无人能及,而且他知识渊博。公元前70年,他起诉曾劫掠西西里的罗马总督维雷斯(Verres),后者逃到国外,西塞罗公正勇敢的名声以及作为一名杰出律师的地位由此树立。
公元前64年,当时任执政官的西塞罗镇压了喀提林(Catiline)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将为首的密谋者处死。罗马的律师团结一致反对那些企图支配共和国的军人,西塞罗则是这场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尤利乌斯·凯撒希望能与西塞罗做朋友,不过后者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有一年,诚实能干的西塞罗在辽阔的亚细亚行省西里西亚(Cilicia)任总督,在他回到罗马时,共和国的崩溃已指日可待。
在那场危机中,西塞罗与庞培和元老院议员们站在一起,反对凯撒,随后,庞培战败被杀。西塞罗拒绝担任剩下的元老院军队的指挥,回到罗马,在那里受到凯旋的独裁者凯撒很好的款待,有两年时间在政治上处于休眠状态。期间,他写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著作。凯撒遇害后,西塞罗努力恢复宪制,在元老院叱责马可·安东尼(Mark Antony),并试图团结各省总督一起反对接替凯撒的三巨头(Triumvirates)。尽管屋大维(Octavian,即后来的奥古斯都)试图将西塞罗的名字从受罚者名单中拿出,最终却还是被马可·安东尼及其同伙流放。
公元前43年12月,马可·安东尼的士兵在西塞罗的海边别墅找到他,对他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割下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将之带给安东尼这位放荡不羁的冒险家,后者当时正在罗马广场的一个选举现场。普鲁塔克这么描述道,安东尼“让人把他的头颅和双手绑在西塞罗发表演讲的讲坛上面。罗马人目瞪口呆,不敢观看这一景象,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不是西塞罗的脸庞,而是安东尼的灵魂”。
共和国和西塞罗一起陨落了。多年以后,第一位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看到他的小孙子正在读西塞罗所写的一本书,便对他说:“孩子,这个人学识渊博,是一位爱国者。”
作为共和美德的典范,西塞罗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有重大意义。美国的领袖们曾仔细研读过西塞罗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国家篇》(Republic,写作于公元前57年他从流放地回来到公元前49年内战重新爆发之间)和《论职责》[Duties,或《论职务》(Offices),编纂于凯撒独裁统治时期他被迫退休之际]。他们中那些受过较好教育者几乎可以背下西塞罗主要的演讲词,而且熟读过西塞罗的信函——这让他们对西塞罗的洞见有了一种亲切感,超过对古代任何其他人的了解。他们在西塞罗的作品中发现了被浓墨重彩阐释的自然法理论——它对理解美国的社会秩序至关重要,他们在这方面研读的是西塞罗的《法律篇》(The Laws)一书。
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写道:“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Nature)相和谐的不偏不倚的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永远存续,不会改变;它依靠指令让人履行职责,它依靠禁令避免人犯错。而且它施与好人的指令或禁令不会白费功夫,尽管它们对坏人没有任何作用。试图变更这一法律便是犯罪,企图废除其中的某一部分也是不被允许的,将它完全废除更不可能。元老院或人民都不能让我们免于其中的责任,我们也无需找外人阐释或解释它。罗马和雅典不会有不同的法律,今天和明天不会有不同的法律,这一永恒不变的法律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都适用,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位主人和主宰——也即上帝,因为上帝是这部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强制实施它的法官。”
一直到罗马掌控意大利其他地区,罗马人只知道适用于土生土长的罗马公民的民法(civil law,jus civile)。它是一套复杂的习惯法体系,并非通常的由元老院和民众正式立法后颁布的法律,而是因罗马人自己长期使用发展起来的——很像许多世纪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后者也是从具体判例确立的先例中内生性发展出来的成果。随着这套法律体系日趋复杂,它在某种程度上被罗马裁判官或首席司法官(他们几乎可以被称为罗马的大法官)的年度裁决理性化。
不过,一旦罗马将权力扩展到整个意大利,它就有必要承认——事实上是创制——第二套法律体系,以适用于不属于罗马公民,并因此不享有罗马人的特权、也不习惯民法的许多人。这一套新的法律体系逐渐被称为万民法(law of nations,jus gentium)——意即它们不是国家法,而是一套立基于多少为非罗马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习俗的法律准则。另一位司法官或寄居人法官(praetor peregrinus,judge for strangers)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将在各个“外来”民族占主导地位的不同形式的法律协调起来,或者让这些形式适当地与罗马民法保持一致是很困难的。因此,司法官们不得不探求能够适当地应用于这些不同法律体系下的案例的正义原则——也即那些基于伦理规范、人类的普遍观念、理性人的特质之上的原则,以及基于普遍正义原理之上的原则。这就发展出了第三套法律体系:自然法(natural law,jus naturale),以区别于习惯法(无论是民法还是万民法)和成文法(或由民众正式立法且由元老院认同的实证法)。
作为法理学和政治学用语的自然法可以被定义为由某种超越政治国家的权威确立的一套松散的行动规则体系。这些规则被认为是源自神圣的律令,源自人性,或者源自人类长期的共同体经验。
一方面,自然法必须区别于由国家颁布的实证法或成文法;另一方面,它必须区分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也即区分于表达某些(如生物学或物理学)自然现象一般规律的命题。有时,自然法也被混同于“自然权利”的学说——后者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基于希腊和罗马的自然法概念。
西塞罗的作品——从他驳斥维雷斯的演讲词直到其生命最后的文字——包含了最为详尽的对自然法的早期讨论。西塞罗对自然法的下述理解仍在影响着某些人的头脑:人类法只是仿效了永恒法。这些永恒法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地球上只有人才是理性的存在。衡量国家法律有效性的标准是它们是否符合理性。
换一种说法就是,自然法是对习惯法或实证法的基于普遍伦理原则的诠释。自然法不是成文的法典,而是以人类普遍规范为参照实现正义的手段。在英国法中,这种方法被称为“衡平”(equity),正如亨利·梅因爵士所言,英国衡平法院的法官将罗马人所写的有关衡平的整段文字都写进他们那些具有持久效力的判决之中,尽管他们没有公布他们引用的来源。
诉诸自然法的做法让罗马法律避免因罗马社会的变迁而过时。梅因写道:“要不是自然法理论赋予罗马法某种与众不同的卓越之处,我不知道罗马人的法律是否还有任何理由优于印度人的法律。就这个特殊情况而言,罗马社会让这一绝妙且十足完美的法律保持了其简单和对称的特性,同时,罗马社会的其他方面注定要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对某一国家或行当来说,在提升完善自己时有其清晰可辨的目标具有无比的重要性。”因此,考虑到罗马自然法的和谐特性以及能够通过理性扩展的特质,它的寿命超过了罗马的政体结构。
在西塞罗死后的几百年间,裁判官和法学家们(或为罗马政府认可的法律权威)对民法和万民法进行了诠释,这样,整个罗马法体系就渗透着一种并非简单人为确定的正义观。在罗马帝国初期,哲学家兼政治家塞内卡(Seneca)详细阐释了西塞罗非常雄辩地提出的自然法观念。即使在罗马衰亡之后,自然法原则也影响了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皇帝公布的法律系统汇编。经由基督教会和经院学家,特别是经由博洛尼亚(Bologna)法律博士们以及圣托马斯·阿奎那的作品,西塞罗的自然法直到7世纪一直主导着法律理论。在南欧,这些自然法理论在经历过“黑暗时代”的失序后又重新涌现,罗马法中的自然法要素也适时地在北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通过一个微妙的渗透过程——也影响了独立的英国普通法,尽管英国国王们试图排斥罗马理论。
西塞罗在他的《法律篇》中写道,最高法来自上帝。它的渊源比“成文法或国家的出现”还早。民众将法律定义为成文的规章,命令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不过,大众是错的。博学之人知道,“法律是内置于自然中的最高理性,它规定什么该做、什么该被禁止。一旦在人的思想中获得稳固的位置和充分的发展,这种理性就是法律。因此,他们相信法律就是智慧,其天生的功能就是命令做对的事,禁止做错的事。他们认为这种特性的希腊文说法源自每人各得其所的观念,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我相信它的名称源自选择的观念。正如他们将公平的含义赋予法律这个词,我们让法律一词有了选择的含义,虽然这两种含义都是法律的应有之义。如果这么理解是准确的话——而我也确实认为这种理解一般是对的——那么正义的缘起就在法律之中了,因为法律是自然力量,它是智慧人的思想和理性,是衡量正义和不义的准绳。”因此,从根本上看,法律是有关人类伦理规范的知识。
如果真正的法律的确是智慧人的正义理性,是一种上帝的恩赐,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关人性的法律优于民法或万民法,优于裁判官的判决,优于凯撒或安东尼的命令。国家的法律应该与自然法保持一致,人们可以将执政者的不义诉诸道德真理的永恒法。
西塞罗非常尊重传统和先例、宪制和秩序。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应当质疑每一部习惯法或成文法相对于自然法的合规程度,相反,一般的人为法是我们展示自己对永恒的道德法的理解的手段(不管它们多么不完美)。自然法不是与国家所立之法相反的一套固定法典;自然法应被理解为道德想象力,而且自然法让我们能够透过理性富有人性地应用习惯法和成文法。按照西塞罗的说法,自然法是阐释人们借以构建共同体生活规则的道德原则。
不过,在严重危机的时刻,执政者们的真正合法性可能需要诉诸自然法来衡量。如果某位独裁者(比如凯撒)或一群寡头(比如西塞罗与之斗争的第一和第二“三巨头”)蔑视或推翻一个国家的宪制,那么其命令便不具有真正法律的道德效力。如果国家的暂时主人是没有正义的——也即如果他们的行事有违自然法,拥有正义理性之人就没有服从他们的道德义务。西塞罗在《国家篇》中写道:“确实,在国内冲突中,如果美德的重要性高于数量,我想弄清公民们的质量而不是搞清他们的数量就是应当的。”民众也可能行事非法不公:人们当以神启的永恒法作衡量私刑(mob-law)的标准。美德和强力之间总是存在着张力,而且即使多数人暂时支持强力,美德也不应就此屈从。
西塞罗绝不是一位革命者。不过,在随后的成百上千年间,自然法理论被那些决意要推翻现存政治秩序的人拥抱。于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诉诸于“自然和自然神”(Nature’s God)。通常情况下,治安法官们运用自然法的概念让一套已确立的习惯法和实证法体系变得人性化、现代化以及协调化:自然法是进步的工具,不是革命的武器。
如果某种根深蒂固的秩序已不再在其实证法中承认少数人甚至多数人的权利主张,那么,反对者就会诉诸于道德法,也即正义理性之法、人性之法及正义的源泉。以自然法为自己辩护的反对者就可以拿起武器。根据西塞罗的理论,即使在20世纪的德国这个受实证法影响最大的国家,反对希特勒的人也通过援引被希特勒颠覆的宪法以及自然法来证明他们抵抗行动的合理性。极权国家的法令与道德法之间的冲突在当代比在罗马共和国晚期更加激烈。
A.P.登特沃斯(D’Entreves)写道:“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的那个农民小共同体的微不足道的法律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国际性文明的普世规则。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将神圣智慧与世俗智慧融汇贯通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自然法,就没有美国或法国革命,而且有关自由平等的伟大理想也不会在获得人心的支持后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西塞罗和罗马共和国一同消亡了。不过,西塞罗给后世留下了混合了希腊理论与罗马实践的自然法遗产。早期罗马人的一项英勇习俗是将某个人“奉献”给诸神,这样,通过他的献祭,共同体就可能在做错事时获得宽宥。西塞罗最后完全献身于罗马人的祖制(mores majorum)和道德法。在其公职生涯的某些时刻,西塞罗会胆怯或犹豫,可是到了最后,他展现出罗马人古老的高尚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