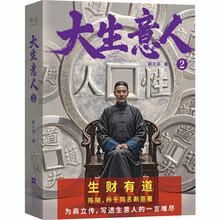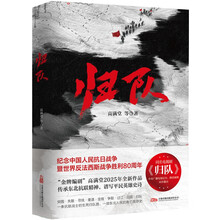影片开始时,比基尼核试验基地上臭名昭著的“蘑菇”云在翻滚升腾。
应该让观众既有初次看到,又有再度看到这股“蘑菇”云的感觉。
“蘑菇”云应该非常雄浑、硕大,成长得十分缓慢并由乔万尼·菲斯哥的乐曲的开头几个节拍伴奏,烘托出它的翻滚升腾。
随着这股“蘑菇”云在银幕上升腾而起,烟云下面〕,渐渐呈现出两个赤露的肩膀。
观众只看见这两个肩膀,是被齐头齐腰截去的部分躯体。
这两个肩膀紧紧搂着,上面沾满了灰烬、雨水、露珠或汗水,任人随意想象。
关键在于让人感到这露水或汗水是由〔比基尼核试验基地上的〕“蘑菇”云在斗腾飘逝的过程中洒下的。
这一画面势必造成一种非常强烈、非常矛盾的感觉,既感到清新,又陡生欲念。
两个紧搂的肩膀肤色各异,一深一浅。
菲斯哥的音乐伴随着这一几乎令人反感的紧搂动作。
两只不同的手的差异应该十分明显。
菲斯哥的音乐由强到弱,渐渐隐去,一只〔经特写镜头而显得很大的〕女人的手放在黄皮肤肩膀上,不再动弹,所谓“放”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抓”似乎更确切些。
一个沉浊而又平静的男人的嗓音诵读般地响起:他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
这句话可以随意运用。
一个十分沙哑,也很沉浊的女人的嗓音,似背诵那样没有抑扬顿挫地回答:她她我都看见了。毫无遗漏。
菲斯哥的音乐重又响起,此时,女人白皙的手正好又在肩膀上捏紧,松开,爱抚着,并在这黄色肩膀上留下了几个指甲印。
仿佛这指甲的印痕能暗示出,它是对“不,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这句话的一种惩罚。
然后,女人的声音重又响起,这声音依然平静,毫无生气,像背诵似的:她我连医院也看到了。对此,我确信无疑。广岛有医院。我怎么能对此避而不见呢?医院、走廊、楼梯、病人,在摄影机无情的拍摄下逐一展现在画面上。(观众在银幕上始终看不到正在观看这一切的她。)现在镜头又回到那只在黄色肩膀上不停地抓掐的手。
他你在广岛并没有看到过医院。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
然后女人的声音变得更加客观。(含义深奥地)强调每一个字。
此时,博物馆的画面一一展现。光线刺眼而令人讨厌,同打在医院上的灯光一样。
资料解说牌接连闪出。
原子弹轰炸的种种物证。
支离破碎的各式模型。
一根根扭曲的钢筋。
一张张蜡制的被烧焦的人皮,一堆堆烤糊的头发。
等等。
她我曾四次去博物馆……他广岛的哪个博物馆?她在广岛,我曾四次去博物馆。我看见一些人在那里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人们若有所思地在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一幅幅照片、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解说牌之间徘徊。
在广岛,我曾四次去博物馆。
我瞧见了游人。我自己也思绪万千地观看了钢筋。经战火焚烧的钢筋。被炸断了的钢筋,变得像肉体那样不堪一击的钢筋。我见到了成束的胞膜:谁会往这方面想昵?那是一张张飘飘荡荡、残存的人皮,还带着清晰的蒙难的痕迹。我看见了一些石块。被烈火烧焦的石块。被炸裂的石块。还有一些不知是谁的一缕缕发丝,那是广岛的妇女们清晨醒来时发现已全部掉落下来的头发。
我在和平广场感到酷热难当。和平广场上热得足有一万度。这我知道。这就是和平广场上太阳的温度。对此,怎能一无所知呢?……至于草儿,那就不消说了……他你在广岛什么也不曾看见,一无所见。
博物馆的画面始终在一一展现。
然后,镜头从一幅被烧焦了的头盖骨照片闪到和平广场(广场与这个头盖骨的画面重叠)。
博物馆的展品连同被烧焦的人物模型。
一组有关(回顾)广岛的日本影片的镜头。
蓬头散发的男人。
一名妇女从混乱中冲出,等等。
她复制品做得尽可能逼真。
影片拍摄得尽可能逼真。
那幻景,显而易见的,是那样逼真,以至游客都潸然泪下。
人们依然会满不在乎,然而,面对此情此景,一个游客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她〔……仅仅是哭泣而已,以便忍受所见所闻中的这番惨景。还有,伤心够了走出博物馆,却还不至于丧失理智。〕她〔游客在那里驻足沉思。我们想必可以说,凡能发人深思的种种机会总是精心炮制的,这么说并无丝毫讽刺的意思。然而,那些纪念性建筑,尽管人们有时会对它们一笑了之,却是这些机会的最好借口……〕她〔在这些发人深思的机会……通常,用这种豪华的排场把发人深思的机会提供给你们时,你们倒反而什么也不想了……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如此,假设别人正在沉思默想的这一景象还是挺鼓舞人的。〕她我始终在为广岛的命运而哭泣。始终在哭泣。
银幕上映出一张根据一幅照片拍摄而成的广岛全景。这幅照片系广岛经过原子弹浩劫后所摄,那是一片不同于地球上其他沙漠的“新型荒漠”。
他不。
你竟会为此而伤心流泪?闪现出和平广场的画面。在夺目的阳光下,广场上空空荡荡,这炎日使人回想起炫目的原子弹火球。
然而,在这片空寂处,再一次响起了男人的声音。
有人(在午后一点钟?)在这空空荡荡的广场上游荡。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以后摄制的新闻记录片进入画面。
蚂蚁、蚯蚓纷纷钻出地面。
继续交替映出两个肩膀的画面。女人的声音重又响起,这声音变得惊慌失常,与此同时,一幅幅画面也变得凌乱、快速,异常疯狂。
她我看了新闻记录片。
第二天,这是史料记载,并非我胡编乱造,从第二天起,一些有名有目的动物重又从地底下和灰烬深处钻了出来。
一些狗被照了相。
从此要流芳百世了。
我都看到了。
我看了新闻记录片。
我看过这些影片。
第一天的影片。
第二天的影片。
第三天的影片。
他(打断她的话)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一无所见。
一条断肢残体的狗。
人群、儿童。
伤口。
被烧得哇哇叫的儿童。
她……还有第十五天的影片。
广岛重又遍地鲜花。到处是矢车菊和菖兰,还有牵牛花和三色旋花,这些花以花卉中迄今未见的非凡活力从灰烬中复活。
她我丝毫没有胡编乱造。
他这一切,全是你胡编乱造。
她丝毫没有。
如同这种在爱情中的幻觉,这种使人永远不会忘怀的幻觉还存在那样,在广岛面前,我同样也产生了我将永远忘怀不了的幻觉。
如同在爱情中那样。
外科手术钳接近一只眼睛,要把它挖出来。
新闻记录片在继续播放。
她我也见到了广岛的一些死里逃生的人和当时还在娘胎里的婴儿。
一个俊美的男孩朝我们转过脸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个独眼童。
一个皮肤烧伤的少女在对镜自怜。
另一个双手扭曲的盲女在弹奏齐特拉琴。
一位妇女在奄奄一息的儿女们身旁祈祷。
一个男人因若干年来无法入睡而备感痛苦。(别人每周一次,领他的孩子来探望他。)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