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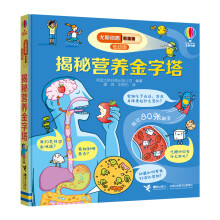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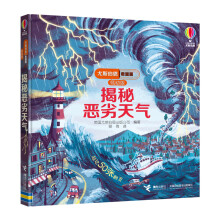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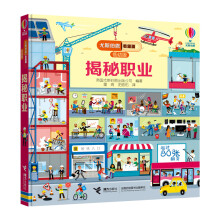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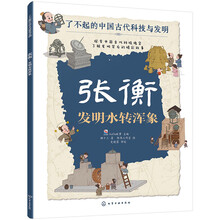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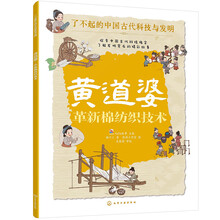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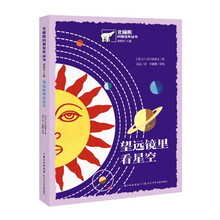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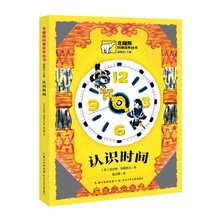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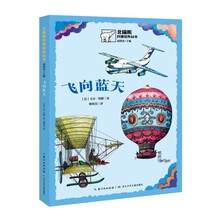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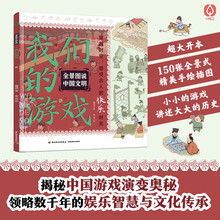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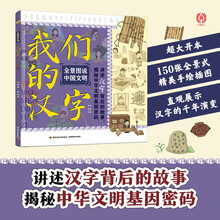
这本书就像一段穿越时空的旅程,沿着千百年来人类仰望星空的印迹,揭示出宇宙所蕴藏的无可比拟的美感与秩序。
用一张张可以双手摊开的二维图像,来刻画行星、星云,星系,星系团、甚或是时空中的一切。人类的动机除了勇气、必要与别无选择,还有作为与生俱来的骄傲。
1.跨度大:4000余年来人类描述代表宇宙的图形的演变历史
2.可视化:百余幅不曾出版的精美星空图,兼顾科学与艺术的双重想象
3.趣味化:始于神话,收于科学,遥望星空之余,领略传说魅力
宇宙是什么样子的?太阳、月亮、行星和满天繁星是什么样子呢?当人类仰望着天空,心里一定会有很多疑问。
迈克尔•本森的这本《宇宙图志》共分10章,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了人类认识宇宙的故事,天文学的记录方式随着时间演变有着不同的演绎。他挑选了百余幅艺术性强和意义深远的插画及星空图,以人类对于天空理解的时间渐进顺序排列,其中很多收藏于世界著名的科学图书馆,而很多图在今天并不为人所知。
浩瀚宇宙,很大程度上,从感官上来说并不可见。这本书从文化史(可视化)的角度来系统展示人类认识宇宙的漫长历程,展现了人类对宇宙的想象。书中的插图都非常经典,大多是欧洲中世纪的作品,在国内从来没有被系统地介绍过。这本书就像一个精心策划的展览,感受一些大自然自身蕴藏着无可比拟与塑造的美感。一种宏观的美感产生于遥远而陌生的宇宙之中。作者的艺术背景让他跳出抽象的概念与数据,专注于图像。解说部分致力于勾勒出认识发展的轮廓,通过连贯的时间线索,把这些作品还原到相应的年代中。
这本书几乎不需要任何背景知识、只要对其中所涉及的历史,宗教、艺术、科技等任一文化元素感兴趣,就可以信手翻阅,并有所收获。与天文数据拍摄不同的是,艺术家植入了自我的主观判断,以视觉美感的角度选取拍摄的角度与环境。
序
Owen Gingerich
欧文·金格里奇
看呐!这非同寻常的视觉样本正在你手中。其中记录着是人类心目中的天国的神秘与美好。
千百年来,夜晚因为野兽的出没而充满了恐怖,但是星月亘古不变的流转也带来宁静祥和。这阕夜曲引起了敬畏与惊叹。圣经诗篇的作者这样感叹道:“我望着你所陈设的星宿,世人算什么,竟让你顾念。”
被这节律激发的还有好奇心。太阳在地平线上的周年往复运动与四季相关,因此也关系到动植物的生物节律。月亮的相位变化提供了一个较短也较为方便的时间间隔,但是它也十分复杂。尽管19年和235个月的长度只相差几小时,但一个太阳年中的月份数从来不会是整数。更复杂的是日食,它们是月球的阴谋,会带来不详。随后,正因为这些恐惧和好奇,天文学诞生了。
最后,天文学开始有了记录——记在纸莎草上、羊皮纸上、碎布纸上,不仅仅是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宇宙图志》这本书正是这样,一份关于奇迹、发现和理解的彩色记录。这本书没有要成为天文史的野心,但每个章节中的图片大致都按年代排列,因此会带给读者类似的感受。迈克尔·本森的文字和思考把这些图像置于人类常识的图景当中。当然,书里也提及了制图的历史,从中世纪羊皮卷上一丝不苟的手绘,到如今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如此看来,这本书更像是一曲对审美情趣的颂歌。
如今天文学家的数量比1950年以前所有的天文学家加起来还要多。除了个别例外,这个群体大都敬重以艺术和科学揭示宇宙的前辈们。尽管如此,现存的十世纪以前的作品也只有寥寥几页,说明这样的早期手稿实属稀缺。如果只看近一千年,并以1540年为界,我们会发现,在一大半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人们确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由水、火、土、气四种元素构成。那时候,美洲刚被发现,活字印刷术还不成熟,没人知道血液通过心脏循环,天花还是没有疫苗的天谴,保健则需要根据占星术确定的日期周期性地放血。
但在1540年,那个世纪最华丽的图书——彼得·阿皮亚(Peter Apian)的《御用天文学》(Astronomicum Caesareum)出版了。书高近18英尺(45.7厘米),114个页面上的彩色手绘极尽精美,还有许多结构复杂的活页。作为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礼物,它真是物有所值。阿皮亚得到的回报是一个新的纹章、授予诗人荣誉的权利,和可令私生子合法的特权。书中的活动星盘,包含了自公元150年以来的托勒玫地心说的所有细节。通过纸轮和指针,行星的位置能够精确到1度(这点仍在托勒玫系统的误差范围之中,要知道糟糕的时候结果会相差5度以上)。阿皮亚的《御用天文学》是本书的重要资料来源,共有6幅跨页插图散见于各章之中。
阿皮亚的鸿篇巨制代表了托勒玫地心说的最高水准。这部优美乃至耀眼的作品可谓站在了人类探索的变革前沿。因为三年之后,另一部伟大的天文著作横空出世——尼古拉斯·哥白尼日心说的代表作《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古旧书市场上,阿皮亚和哥白尼至今仍在比拼。《御用天文学》要价高达一百万美元,《天体运行论》的价格早已经超过了两百万)。异乎寻常的是,《天体运行论》的原始手稿仍然在世。当年哥白尼留下了它,交给纽伦堡的排字工人的只是一份抄本(这抄本也许并未被好好保存)。在本书的第146页可以看到画着示意图的日心说手稿,这是科学界所见证的伟大联合的一份纪念品。
哥白尼革命性的学说在当时并未被立刻接受。人们站在一个自行转动的球体上,赤道处的自转速度达每小时一千英里——这个想法实在是荒谬——人为何还未被甩到空中呢?《圣经·诗篇 104》中不是说上帝“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吗?正因如此,在随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哥白尼的日心说只作为计算行星位置的方法,而非对真实宇宙的描述。后来得益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的著作,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在本书里也可以看到相应的著作内容。
想来你已经按捺不住,打算自行翻看这本书了。不过,请允许我再谈谈几张图片吧。对我特别有启发和吸引力的那几张。
“月球”一章中有一组有趣的望远镜观测图片,时间跨度为五个世纪。这一章非常精彩,有些细节并不一望即知。相较地图学,伽利略对地形学兴趣寥寥。后者关注高度与深度,会让月球更像是地球。但伽利略的月球图片(见79页)描绘非常精确。这幅图确定于1609年12月18日绘制。制造望远镜时,伽利略要求设备能把观测物的右侧显示在上方,因此他的素描中北方在画面顶部。托马斯·哈里奥特的正面图也是如此,但由于在满月时绘制,图上没有阴影也没有山峦。其实,哈里奥特比伽利略更早开始绘制月面素描。可他的设备无法看清环形山,因此直到他看了伽利略的作品,改进设备以后,他才开始记录环形山。哈里奥特最好的月面全图(从未发表过)在地图学上的意义完全超越了伽利略的作品。与伽利略不同的是,他没有任何对月面地形和月面山脉高度的描述。
在伽利略开创性地使用望远镜进行天文研究之后不久,大部分天文学家使用开普勒式的镜片组以获得更大的视场。但他们看到的是翻转的倒像。起初,天文学家绘制的月亮仍是月面右侧朝上。第87页玛利亚·克拉拉·艾玛特在1693-1698年间所绘制的“满月”(plenilunum)就是这样。画面下方,距月球南极不远处是带有明亮辐射纹的南部第谷环形山。而在1878年威廉·戈特黑尔夫·洛尔曼绘制的巨幅月面图(第96-97页)中,上方为南,巨大的北方月海(澄海和雨海)在底部。
艾蒂安·特鲁夫洛于1875年绘制的湿海(第99页)的细节无比动人。画面的下边缘处是巨大的伽桑狄环形山,它在北方。下一页中,湿海和伽桑狄环形山则在满月边缘的两点钟位置。而湿海出现在现代的地质平面图中时(第108页),它北部的伽桑狄环形山又重新回到了顶部。宇航员所用的真实月球地图的方向总是上北下南。
……
第五章 宇宙结构
他们生活在童年,
世代繁衍。对它们来说,太阳
曾是农民红润的面庞,月亮在云彩中偷看,
银河就像长满白桦的小径一样令人欣喜。
——米洛什,琴斯洛
亚里士多德-托勒玫宇宙论中的地球中心和多层天球设计统治了宇宙学理论一千五百多年,比西罗马帝国的历史长了三倍。托勒玫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模型——他的本轮和均轮,让天文学家们得以较为准确地预测天体运动。托勒玫理论只是部分解决了复杂的行星运动问题。其固有问题在中世纪的十个世纪里并没有多少人关注。例如,它完全无法解释行星向西的逆行,它们通常是在恒星背景上向东运动。
和古代的其他宇宙论相比,亚里士多德-托勒玫体系完全基于对天体长达几个世纪的实际观测,而非简单地将它们诉诸神灵。尽管有时善变的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会让上帝主宰天庭,但是他们的王国是在最外层天球之外的。当我们凡人从天球内部向上看时,上帝是从外往里看。作为这个复杂系统要素的行星和恒星在中间不停运动着,值得被仔细研究。
古希腊人给出的天文模型,被托勒玫和他的继承者们改造为严密的数学理论,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预言许多天体的运动。它能够解释月相和日月食。古希腊的埃拉托色尼就据此估计了地球的直径。它也提供了方法来理解行星,太阳和月亮的运动,还能追踪行星在黄道上的偏离(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上的视运动轨迹)。虽然地心说以地球为中心,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成熟而有效的工具。
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的天文历法数据,对天象的细致观测传统,处理数据的系统化的数学方法——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了后来 “哥白尼革命”的基础。这位波兰天文学家将他的理论建立在托勒玫原理的基础之上,虽然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在1543年出版以后,彻底颠覆了托勒玫的天体等级系统。本质上,哥白尼试图重拾高度复杂的古代天文学技术方法。以太阳为中心而非地球。这个转变让他得以摆脱较为复杂和困难的环节,同时保留许多核心原则。即使他保留的部分也被后来的天文学家替换了。
在某些科学史研究者看来,哥白尼对地心说的不满源自的托勒玫系统中众多复合圆环所引入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几个世纪以来的天文学家都在尝试弥合地心说与观测到的天体运动之间的矛盾。他们向托勒玫的系统中加入众多混合元素:本轮、载轮、均轮和偏心轮交织着不停转动。最终,哥白尼对已经成为戈德堡式笨重发明的理论有美学上的偏见。它甚至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确性。如果“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那么可以说哥白尼看到了这个理论的粗陋与虚伪。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哥白尼也许并非对托勒玫的数学理论感到愤懑,只是简单地为古代宇宙学体系中的遗留问题所困扰。这其中就包含了神秘的行星逆行。根据天文学家欧文·金格里奇的说法,哥白尼可能还对托勒玫系统中随意安排的行星位置不满。相比之下,哥白尼的日心说带来了秩序。
“他意识到周围的行星都自动各就其位。周期最短的水星距离太阳最近,慢腾腾的土星以三十年为周期绕太阳旋转,离得最远;其他的行星则按比例位于中间。这种布局有着无法抗拒的美感。而且它还解释了托勒玫地心说中的谜团:火星,木星和土星会周期性地中止在恒星背景上的东向运动,转而向西运行几个星期,这就是逆行。为什么这种现象总在行星和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相对时发生?…… 托勒玫无法解释,但是哥白尼可以。以太阳为中心,那么火星逆行就会在运动较快的地球超过火星时出现。这总是在行星离地球最近并与太阳分居地球两侧时发生。之前的神秘巧合如今成为合理的事实。这样的安排提供了一整套观念。哥白尼就这样发明了日心说!”
……
I. 序 欧文?金格里奇 6
II. 前言 迈克尔?本森 9
1. 创世 16
2. 地球 36
3. 月球 70
4. 太阳 112
5. 宇宙结构 136
6. 行星与卫星 174
7. 星座、黄道十二宫与银河 214
8. 日月食与凌星 252
9. 彗星与流星 276
10. 极光与大气现象 300
致谢 317
图片版权 318
中英文名词对照 321
索引 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