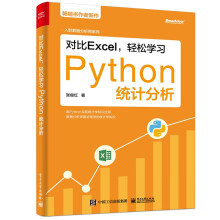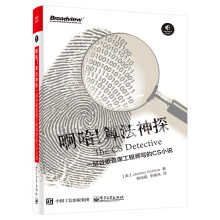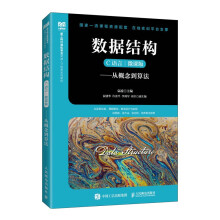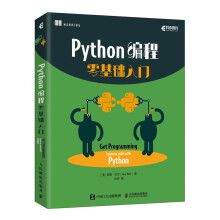《文化遗产研究(第4辑)》:
关键词:人类学
人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各种复杂交错的关系。假如我们先把人类学做一个最简单的简化,这个Anthro-pos最关键的问题是区别于(2haos,也就是神性的世界。我们知道1501年正处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时代,而它也正是整个西方或者世界史的近代的开端。宗教改革带来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重新界定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所以人类学这个概念、这个学科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露出它的第一缕曙光,非常合乎逻辑。首先,这个“人”的问题是相对于神性的世界而言的。另外一方面,“人”是相对于自然界、动物界而言的。人刚好是处于神性跟自然之间的,非常复杂、吊诡、无奈的生物群体当中。所以,人的中间层面是相对于上下而言。在整个近代的发展中,尤其在18世纪以后,现代学术体系日益复杂,近代形态的大学实际上最早的根源是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在博洛尼亚大学之后,才有巴黎索邦大学、布拉格大学、海德堡大学这一系列欧洲古老学校。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18、19世纪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所有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学术体系基本上是继承于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之所以现在称其为柏林洪堡大学,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柏林新增了两所大学,即美国人在西柏林创建的柏林自由大学,以及后来的柏林理工大学或技术大学。因此,现在柏林著名的大学有三所,真正古老的是柏林洪堡大学,它是黑格尔以及很多大思想家、哲学家工作过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其体制最根本的模式是由蔡元培仿照柏林洪堡大学的模式,继而在中国进行推广形成的。另外一些教育体制是向英语国家的教会学校学习然后慢慢在中国进行推广的。还有一些是1952年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得来的。在1952年大学科系调整之后,中国的整个大学体制更多的是苏式模式。因而今天的我们还生活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学体制之中,而一些很关键的学科设置就是这么演变来的。人类学作为一种学问慢慢进入大学体制,实际上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作为一个简单的分类,人类学即16世纪初出现的体质人类学。而文化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英、德、法三个国度都对文化人类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跟文化人类学相关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的大学制度中已经在表面上分得很远了。这个Ethnologie是德语对文化人类学的表述,在英语中是CulturalAnt。hropology。关于历史维度的是考古学,它跟人类学有共同交叠的地方,就是必须做田野,是一种实证性的、艰辛的研究工作。从文化空间的维度来讲,就是民族志、民族学,这部分是先从德语区开始的。
为什么在19世纪末期真正定型的文化人类学会有很多复杂的面向?因为人类学本身是一个启蒙理性的产物。客观地说,人类学是关于智人}tomoSapiens的研究。但实际上人类学更多的是开化了的文明人对自然人的研究。所以从历史时间的维度来讲,比如考古学,我们跟逝去的、古老的文明打交道,通过器物推断他们当年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再往前推断他们的精神生活、信仰、习俗、社会关系,这个没有太大的杀伤力。人类学本身的杀伤力在于它这种启蒙理性的根芽,它是欧洲启蒙并且工业化真正成功,全世界的殖民已经成型之后的一种学问。而作为当代文明社群的欧洲白种人本身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只有在纳粹时期,白种人本身成为人类学的热门。体质人类学家为纳粹做了很大的贡献。为了论证雅利安人的高贵,体质人类学家甚至做了很多关于脑容量的测量。因此人类学可以为文化上的某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提供根据,这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它也可能在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意义上为某一种种族主义提供根据。一方面,人类学理所当然地是研究全人类,研究神界与自然界之间很特殊的种群,也就是人;另一方面人又有历史空间的、文化空间的、种群的差异,所以人类学实际上在相当的时期都有这么一段历史。
我们和这次来开会的贺霆教授以及徐新建老师都在讨论,人类学的对象为什么恰恰把人类学的创建者给排除了?我们应该让所有人既是人类学的主体,又是人类学的对象。大概在20世纪初的英国,发展中的人类学与当时博兴的社会学结合,到现在为止在中国最发达的人类学实际上是所谓的社会人类学,这个SocialAnthropology是从英国学派来的。而英国学派跟燕京大学的人类学家,比如吴文藻体系的人类学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到现在为止,从吴文藻到费孝通,还有一个很革命的老太太雷洁琼,北京大学的社会人类学院里,基本上除了雷门弟子就是费门弟子,他们几乎主导了目前文化人类学的中国版图,这一部分就跟英国传统靠得比较近。另外就要讲到傅斯年。我们提到中国的学术体制,除了蔡元培,我们还要感谢傅斯年,也就是后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的小兄弟,“五四”的时候他也算一号人物,被称为“傅大炮”,是一个很有实践性和力量的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