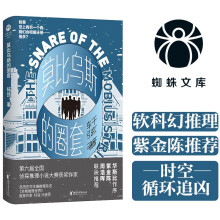多面的胡仙与另一只眼
一、“狐”耶?“胡”耶?
国内对于关公、观音、八仙、文昌、城隍、门神、土地爷、灶王爷等神灵多有专书研究。在官民合力下,关公、观音、城隍、八仙等影响深远,相关的文字记述和传说很多,研究的专著也不少。遗憾的是,或者是因为“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这些著作大多是材料的累积,就事论事,从触及中国民众宗教实践的本质特征,缺少洞见。这一不足给也人造成好像中国人不会读自己祖辈留下的古书似的。与之迥异,近百年来,西方人在读中国的古书时,总是能读出些新意,让人耳目一新,拍案叫绝。
20世纪早期,法国社会学家葛兰言在读现代国人看来诘屈聱牙的《诗经》时,读出了早期中国社会与国家甚至中华文明是从两情相悦的男女在水畔山坡的对歌和欢笑声中开始生发、升华、形成的。在读明清以来关于“秘密宗教”的诸多宝卷时,欧大年读出了中国民众对女性神灵的敬拜,认为中国民众宗教的根基是“信仰女性神祇、奇理斯玛式领袖和期待未来佛”,所以中国民众对于耶稣和基督教教义天然就存在抵触心理,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韩森在读宋代以来的志怪、笔记、话本和方志等文字时,发现了民间在接受官方推崇或强制推行的信仰的同时,官方也在不断地接纳与校正民间的部分信仰并进而推广的频繁互动的辨证关系。面对浩繁且众说纷纭的义和团运动的史料,柯文解读出了不同参与主体的不同感受和这些后来被辑录的史料的主观性与随意性,说明在后人眼中热热闹闹、扑朔迷离的义和团是“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叠加和多声部合唱,每个异质群体都在根据自己当下的兴趣、爱好唱着自己的调。韩书瑞在读妙峰山因风蚀而模糊程度不一的碑刻铭文时,读出了潭柘寺、大觉寺等寺庙中的僧侣、京城的五顶和丫髻山、皇族以及关注妙峰山的学者等各种竞争性力量对妙峰山成为北京民间的一个文化中心的作用,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仰者、参与者的阶序对妙峰山庙会兴衰的影响。
这些迥异的见解也使得近些年来的海外学者——真假洋人——的著述在国内学界大行其道。夏志清、李欧梵之于现代文学如此,费正清、黄仁宇之于历史学如此,施坚雅、杜赞奇等之于社会学人类学亦如此。关于民众宗教的研究,杨庆堃、武雅士、王斯福等的理论建构同样是被效仿的经典。
正如本书前文已经提及的景军、流心、周越一样,阎云翔等这些于20世纪晚期在海外留学,并依然在中国做田野,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华人,犹如水陆两栖的族类,他们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回审自己的母文化,有了对母文化的陌生化式的敏感。因为善于讲故事和叙述,行文晓畅,理论思考深入浅出,其研究不但很好地向西方介绍、阐释中国纷繁复杂的诸多文化事象及其丰富内涵,在国内外也拥有数量不菲的读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些人的研究既延续了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杨庆堃等老一辈在海外学习过的学人研究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也弥补了长久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时认知的先天不足或者说片面。西方学者这种认知上的不足既源自爱德华?萨义德早已批评过的自我中心、先入为主、居高临下的任性的“东方主义”,也源自田野调查的局限和因对异文化的陌生而生发的对田野知识细腻把握的偏差。
2005年,康笑菲在博士学位论文《边缘的权力:晚期中华帝国的胡仙敬拜》基础上修订成书的《胡仙敬拜:帝国晚期和现代中国的权力、性别与民众宗教》也是这一“两栖族类”研究中的佼佼者。2009年,该书由姚政志翻译成中文,定名为《狐仙》在台北博雅书屋出版。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获得博雅书屋的授权,在大陆出版发行简体字版本,书名更替为平白却诱人的《说狐》,并忝列该社的“社会经济史译丛”。用人类学和历史学混融的视角,康笑菲重读笔记、志怪、小说、方志等众说纷纭的古文献,读出了关于胡仙的文字表述体系中潜在的意味。这既给国内时下还有些热度的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也给“乡土宗教”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她与景军、周越等人的研究一道,将杨庆堃等前辈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稳步推进,在一定意义上开创了中国乡土宗教研究的新时代。
要特别指明的是,在这里,我没有使用学界习惯性使用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以及民众宗教、大众宗教等术语。因为这些惯用术语是在官民、雅俗、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甚至宗教/信仰与迷信、正祀与淫祀,尤其是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先进与落后、高级与低级等二元语境下产生的,并且在不尊重历史悠久的基层信众实践的前提下,就先入为主地进行了优劣好坏高低的价值评判与定位。
就康著中译本的书名而言,论繁体还是简体,没有变的是那个“狐”字。按照英文字面意思,将书名译写为“狐仙”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考虑到当下仍然在广为实践的这一宗教事实,尤其是敬拜者的虔诚和他们在乡野将其神位名书写为“胡仙”的事实,那么将该书名译写为“胡仙”或更为可取。因此,后文使用的是“胡仙”,而非“狐仙”。对于译者、出版者、发行商而言,康著中译本书名用“狐”这个字眼儿,应该不仅仅是信、达、雅的翻译之果。要么是参与诸方对践行了千百年的中国本土宗教,尤其是老百姓当下正在践行的宗教很“隔”,要不就是首先将关于“胡仙”的乡土宗教视为不足道也的“怪力乱神”。当然,不排除仅仅是因为康著这个商品销售的策略。毕竟,哪怕是中国已经迈入城镇化、都市化时代,“狐仙”“狐狸精”也依旧是都市人因消费、娱乐“鬼”而熟悉的。反之,“胡仙”却潜藏于乡野,在光洁亮丽的都市没有存身之所。
有鉴于此,乡土宗教这一概念指称的是底层信众的宗教实践,而非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宗教归属的分类言说等意识形态。换言之,乡土宗教关注的是过去、现在以至将来民众实践的宗教。这里的“乡土”既指陈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所孕育的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指这种特征在尚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以及转型后的未来中国的余音、余韵。
二、起承转合:八面玲珑的胡仙
不同于早年杨庆堃概论式地在制度性宗教框架下对中国乡土宗教的社会功能主义研究,也不同于周越完全是对中国当代乡土宗教的田野经验研究,《胡仙》一书是对历代的笔记、志怪、小说等文献进行爬梳,结合相应的社会生活实践场景,对所有与胡仙相关的文献进行系统解码,试图以历时发展的胡仙敬拜为案例解读中国乡土宗教以及中国文化的特征。由此,康笑菲也就读出了下述新意:
第一,明白地勾画出了胡仙敬拜的发展演变的官方化和去官方化,即韩明士所谓的官僚政治的和个人的——道与庶道——信仰这一矛盾互动的历程,是官民之间、外来者与本地人之间、男人与女人、妾/情人与妻之间等多个对立群体进行权力争夺、冲突和妥协的产物。
第二,强调文本记述和宗教实践之间一直互相影响的动态关系,即将文人的记述、写作还归到相应的社会场景和生活实践中来分析解读,这正是以往对胡仙相关的文学研究相对缺乏的一面。
第三,视野开阔,也不乏深刻。作者始终试图以胡仙的案例来透析中国乡土宗教的特征,以及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的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作者还将中国的胡仙敬拜与日本的丰收之神——稻荷神——的敬拜进行了简单的对照,使得对中国有着漫长历史的胡仙敬拜的认知有了横向比较的视野。
第四,对“胡仙”这个词进行了有意义的、精当的历时性话语分析,细致入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注意到北方方言中儿化音“胡仙儿”与“胡仙”两个语汇在生活交流中完全不同的意义,兼顾了“胡仙儿”在不同语境、不同人嘴中的多样性。这正好是胡仙敬拜蕴含的道德价值判断、人际关系和世界观的语音化呈现,是乡土宗教的基本特质之一。
康著前两章属历时性研究,分别梳理中国早期传统中的胡仙和胡仙信仰的扩散。后续四章分别从胡仙与家户敬拜、胡仙与灵媒、胡仙与地方崇拜、胡仙与官方四个层面关注位居边缘的胡仙与人们之间的互动赛局,阐释人们如何通过敬拜胡仙从而在公与私之间、官方与非官方之间和男女之间达到权力的平衡与“社会的均衡”。在这一权力格局失衡和至衡的动态过程中,男女的性征、性欲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追求超验能力和神圣权力的工具与策略。
在第三章《胡仙与家户敬拜》中,作者解读了包括蒲松龄《聊斋志异》在内的诸多文献,分析指出:如同唐宋就曾经有的“狐能致富”的观念,在明清的文本中,被胡仙附身的妇女实际上是家庭财富的源泉,地位低下的妇女利用胡仙附身来谋取她们自己在父系权威中的权益。这一现象与同期北中国经济基础相关。虽然明清时代的北中国因为棉花的大面积种植纳入了大的市场贸易体系,但由于天气等自然条件的局限,北中国仍然普遍性地较南中国贫穷。人们卖女儿、妻子,或者出租妻子、女儿的身体来获取生存和财富是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不同于狐男和俗女所隐藏的“类商业关系”,在狐女和俗男的关系中凸显的是家庭男尊女卑的阶序。虽然狐女有着带来或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且贤惠到给夫买妾,相夫教子,但狐女永远是边缘性的,得不到男权世界最终的认可。在家庭中,狐女的权力不得不受制于既定的道德秩序。如果到了失控的状态,狐女就会遭压制与根除。《聊斋志异》的资料来源和成书后对读者生活的影响暗示了民俗和文学创作之间共享与互动的关于狐女的基本认知。但是,对父权和夫权的家庭伦理的短期逃逸、匿名,使得狐女与俗男获得了金风玉露般的浪漫承认,甚而证明了女性的能量与权力。
以此观之,如果突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界对《小二黑结婚》的误读——意识形态化的教条式解读,那么就会分明地看到,“三仙姑”这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活跃于黄土地的“狐女”令人妒忌的旺盛的欲望与生命活力,以及因此而生的令乡村内外各色精英忧心忡忡的巨大能量和权力。她不但挑战五四以来精英所批判的父权、夫权、王权、族权等男权阶序,也直接挑战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智识精英在西方人标准之下命名为“科学”与“文明”的玩意儿,并以其特有的方式使动荡岁月黄土地的生活风生水起,成为枯寂的黄土地上流动、变幻、冷笑的幽魂。
或者,康笑菲上述观点可以进一步简括为历史文本中胡仙信仰的“性政治学”。地位低下的女性受压抑的身心需要释放,需要男狐这样的修饰符号和载体。对女人,尤其是对女性身体,拥有支配权的男性对财富等有着更多的欲望,而男狐则有提供财富的非凡能力。换言之,男狐既能满足一个家庭中女性的欲望也满足该家庭男性的欲望,使本身就充满斗争和妥协、并有着既定阶序的家庭日常生活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一新的平衡鲜明地体现在“性”这个节点上。人(俗女)和仙儿(狐男)之间的这种类商业关系常常是脆弱的,很容易就单方面终止。这种脆弱性甚至影响到了在家庭这个竞技场敬拜胡仙的方式:简陋的祭所、仪式和尽可能丰盛的供品。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俗世中的人还是显露出其自信,即通过得到某种平等的与胡仙谈判的权力,并充分利用胡仙的权力来服务于他们自己个人的目的。
这种与现实生活相关联的性政治颇类似于流心在《自我的他性》中阐释、辨析的当下都市社会中“处长、小姐和老板之间的三角关系”。在当今中国普遍存在的这种畸形关系似乎仅仅是传统中国“人狐”类商业关系的整体性位移。老板类似于父系权威体系中需求多多的男性——父亲或丈夫,俗世的小姐同时也扮演了被狐狸附身的妖媚,漂亮、勾人魂魄的狐女,而处长则类似于有着诸多法宝并有着超凡能力,能激发也能满足人诸多欲望的男狐。当然,在这个当代的三角关系中,同属于男性的老板和处长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人和仙的角色也会因应具体情境而易位。如同过去一样,在酒吧、ok厅、甲鱼宴这样被悬置的“零点空间”,今天都市文明中存在的这种类商业的“人狐关系”是脆弱的,会因任何一方的退出而终止。
第五章《胡仙与地方敬拜》是对和胡仙有着关联的西王母、碧霞元君与王奶奶这些不同女神生发、升迁过程、相互关系和内在意蕴的梳理。《百里志》、《述异记》、《子不语》、《凉棚夜话》、《燕山丛录》、《醒世姻缘》、《狐媚丛谈》、《阅微草堂笔记》、《印雪轩随笔》、《庸盦笔记》、《清稗类钞》等等都是作者随手拈来的解读对象。
以《子不语》中的故事为例,作者解读出村民在敬拜有祛除狐魔能量的天神的同时,对恶迹斑斑却能满足个人需求的胡仙的宽容。在对《凉棚夜话》中记载的前殿供奉女神——胡仙,后殿才供奉土地神的“土神庙”的分析中,康笑菲指出这实际上是睿智的村民使用官方的象征和性别的等级来驯服胡仙的恶习,并为自己的最大利益来提升胡仙的权力的政治策略。同样是在文献的解读之中,康笑菲浓墨重彩也绵密地辨析了在信仰实践中胡仙与女性神祇之间的复杂关系。
汉代之后,西王母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高高在上。宋代以来,碧霞元君在北中国几乎完全取代了汉时的西王母,形象可亲可近,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联日紧。对碧霞元君的敬拜和对胡仙的敬拜盛行在大致相同的时期与地域。在庙宇中都穿着三寸金莲的胡仙和碧霞元君有相似的身份,拥有非正统的权力,灵验而危险。二者日常的敬拜群体都是社会地位低下但又有着重要社会功能的边缘性群体。产婆、媒人、太监、差役、少妇、儿媳等都敬拜碧霞元君,妓女、小妾和艺妓等则敬拜胡仙更甚。只有在碧霞元君和胡仙互动时,人们才认为这二者是独立的,且将胡仙置于碧霞元君之下,认为碧霞元君是胡仙的上级。碧霞元君在控制胡仙危险性的同时,其在泰山的住地也是一个拯救之地,在这里可以将狐狸从兽形变为人形。这样,对碧霞元君和胡仙的相互借用使得人们既能驯服狐狸的邪性,又能暗地里提升碧霞元君和胡仙的颠覆权力结构的能力,超越于天界神灵的制度性控制。
在19、20世纪之交,与人们对碧霞元君的敬拜并行不悖,一个被称之为王奶奶的女神出现在了京津地区。在保持女性神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的同时,在很短的时间内,民众自由地使用官方的语言和符号提升王奶奶的神格。在康笑菲看来,西王母、碧霞元君与王奶奶这三个女神的官方属性和个体特征不但代表了历时性升迁等级的不同阶段,而且也是同一种敬拜共时性兼有的不同面相。也即,一种有名的敬拜,即使有了官方的认同、敕封,也有公共庆典,仍然包含有其亚神或者说其低下阶段时有的个性化的、地方性的和实用的因素。包括胡仙在寺庙与天神毗邻而居这种中国乡土宗教的混融性、涵盖性打破了公与私、官方意识形态和非官方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化界限。这种有着对立的分野是变化的、动态的。为此,康笑菲总结说:
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脱胎于萨满和灵媒的地方文化的西王母、泰山奶奶、王奶奶对女性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同时,她们与狐狸精的共同关系又暗示了这些女神有潜在的危险。但是,由于敬拜者使用公共符号和官方象征提升她们的权力,在其发展历程中,这三种敬拜也都按等级地前进。当一种敬拜发生了从地方到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扩展并得到公众甚或官方的承认,一种新的、小的和地方性的次生敬拜就会出现。胡仙信仰本身也是这样升迁的一个例证。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北中国和满洲的狐狸常常被作为五种(或四种)神圣动物之一而得到敬拜。这五种动物包括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在这五种神圣动物中,狐狸处于最上层,许多它的恶习都“滑”向了黄鼠狼这种与之相似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价值的动物。
在题为《胡仙与官方》的第六章,作者清晰地勾画出了作为情妇、妓女和艺人的胡仙,作为流浪者、不法者和守印大仙的胡仙等诸相,并将“作为第三只眼的胡仙”与诸相并列,指明在帝国晚期亦正亦邪的胡仙的两可性、模糊性。
在帝国晚期,胡仙利用神圣的洞察力,常常发挥着“第三只眼”的功能,监督官员的道德行为并限制其滥用权力。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当帝国失去了它象征性和真实的对社会的控制后,胡仙敬拜在衙门内外更加盛行。此时,在民众的知识与想象中,一度因偷窃而声名狼藉的狐狸精不时被描绘成为窃贼的克星和官方利益的保护者。当国家力抗击外来的侵略时,胡仙还成为拯救帝国宫殿、使国家免遭侵略者进一步羞辱的官方辅助力量。
但是,康著不仅仅停留在文献的耙梳,阐释。除前文提及的与日本稻荷神敬拜的比较,康著还有在陕北波罗镇田野调查的记述与分析。在如今的波罗镇,从外而来并附带灵力的胡仙试图定居当地,可胡仙的能力却被认为是从属于石佛。官方对佛陀的承认,使佛陀通过文本、庙庆、戏剧、高大显赫的塑像、石碑等得以再现,但佛陀却是一般人法亲近的。形也灵验的胡仙只能通过口头和小的旌旗传播,是弱势的、边缘的,属于“生活失衡”并力有效解决的底边人群。这样,从现存的胡仙敬拜实践,作者发现了与文献记述中的胡仙敬拜共同之处:边缘性。
在结论中,作者强调胡仙是中国文化一种多重的象征,强调必须将胡仙放在多面的中国神灵及其在中国宗教中潜在的地位这个情境中来理解,以此对“官方-帝国的隐喻”这一陈说提出批评:
在中国,胡仙敬拜的历史说明,民众敬拜的恶魔起源已经极大地吸引了所有社会背景的人,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从官方的权力和道德世界中自由追求超道德的、个人的和地方利益的机会。人们利用胡仙的边缘权力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和精神的疾病、经济困难、家庭失序、性紧张、道德窘境和政治压力,并紧扣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文化的差异未能整合不同的社会群体,政府、宗教人士和精英也不可能对胡仙进行一致的解释。而且,多面、模糊和经常矛盾的形象在不同的个体和社会群体中引发了复杂的和情境性的关联。精英、官员、宗教专家和普通人敬拜、祛除、讲述和记述胡仙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实践繁荣了胡仙敬拜。荒谬的崇敬和憎恨,中国文化中的狐狸精体现了的布迪厄界定的“官方(正式)”秩序和“非官方(非正式)”实践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多层面的、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的文化情境中。在中国人将狐狸灵力最佳化也控制其邪恶的时候,人们根据他们多样的需要,建构并颠覆了官方的秩序和公共道德。
这样,胡仙成了康笑菲把握、理解繁杂多样的中国乡土宗教心灵的绳子。千百年来的中国民众的宗教实践也就沦为一个她可以书写、组织与言说的对象。如同一个语言学家,康笑菲不残酷地一步步揭穿了中国乡土宗教的障眼法,剥去了中国乡土宗教的遮羞布,将中国乡土宗教的语法和修辞裸露出来。如同一个深通医理戴着老花眼镜的老中医,康笑菲似乎在给中国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宗教实践把脉,并触及到深藏的静脉。如同一个不怕脏累、鞠躬尽瘁的下水道工人,在汗牛充栋的文献宝库中爬梳、历尽艰辛的康笑菲似乎找到了中国乡土宗教流淌了千年、纵横交错、时断时续的暗沟,发现了它的起承转合与节点。
于是,博学、精通中英两种语言并熟稔东西两种思维方式的康笑菲就带着高低胖瘦不同、动机目的兴趣眼光各异的各色人等在中国乡土宗教的历史长河中漫游,时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时而迷雾蒙蒙、荆棘丛生,徜徉、迷醉在官与民、男与女、阳与阴、本族与异族、我与非我、妻与妾、上与下、生者与死者、古与今、公与私、书面与口头、正与邪、主与次以及文明与野蛮等在家庭、地区以至国家等大小、层级不同的竞技场的政治斗争与妥协的权力共谋之中。
因此,在康著中,狐狸不仅仅是狐狸,胡仙更不仅仅是胡仙,而是变化多端、四通八达、上天入地的精灵,由此能认知中国乡土宗教甚至中国文化的内核以及全部。也因为对胡仙敬拜流动性和暧昧性的强调,康豹因此认为康著能够促进对“中国文化潜在标准化的传统智慧”与“官员和精英们自上而下施加文化整合能力”的重新思考。
三、三寸金莲:边缘化胡仙的边缘
如果康著所引用、分析的文字记述传达的确实是她所言的信息、意义,那么在敬拜实践中,敬拜主体难道没有一点纯粹精神上的追求与关照?换言之,“权力”架构下的话语分析是否能够完全清楚地解读出国人千百年来胡仙敬拜的所有内涵?权力争夺中的冲突与妥协难道是胡仙敬拜这些被霸权话语称为“淫祀”和“迷信”的乡土宗教不绝如缕传承的唯一动因?承袭结构人类学的阴阳、男女、上下、官民、偏正、正邪等二元结构分析是否多少有些机械地割裂行动者身心合一的敬拜实践?形中强化了敬拜主体的“身”和研究者的“心”?
从权力-话语的视角而言,作者基于波罗镇田野调查的分析也是事实。但是,正如康笑菲的田野描述本身展示的那样,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常常处于失衡的民众而言,外在形式上边缘的胡仙反而可能才是中国乡村的庙庆与宗教实践的本质和核心。如果没有灵验的胡仙或者当地人认可的灵验的其他超自然力,一个被官方认可、扶持的村庙的香火会很快地衰败而成为仅具观赏价值的景观或表示方位的地标。
理性的选择、信仰的法则之类当下在国内宗教研究中热门的理论其实是将中国经验西方化后的误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言传的就是中国乡土宗教的情感性特征。中华文明迥异于以基督信仰为核心、主导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排他性的、攻击性与侵略性的,总要为自己的扩张以及暴行寻求逻辑上的理由,首重理性。与之不同,中华文明则是包容性的,晓之以理时也以动之以情为基础,首推情感。同样,在中国的普通信众那里,理性的选择不是没有,但那是以情感性的选择为基础和前提。信众情感化的表达常常是神、仙灵验与否和庙会香火红火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完全忽视这种情感取向的宗教市场理论以及明显带有东、西意识形态之间争斗色彩的中国当代宗教市场的色素分析以及短缺经济学的论断同样机械地、片面地解读着中国复杂多样的宗教实践,主观、随意而任性。
诸如胡仙敬拜这样的乡土宗教的“边缘”特性仅仅只是官方抑或居上位的精英的他者的主观定性,是局外人的认同和霸权话语的产物。对边缘性群体而言,他者的“边缘”反而是其“中心”。为了自己的“中心”,民众表面上也会迎合、迁就甚至套用、利用官方的话语、形式,以退为进,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也正因为如此,当拥有横暴权力和话语霸权的精英将民众信仰的神灵镇压、消灭或者收编、提升而边缘化后,各地的民众会我行我素地再生产出自己当地信仰的人性化的、实用的,并且是可亲近的和支配的神祇与“中心”来。
同时,当把中国的传奇、笔记、小说、野史等休闲文字完全当作正史或史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情来解读时,这些原本博人一笑,供人茶余饭后闲谈、娱乐开心的文字也就变得面目可憎、索然寡味。这或者是可以视为典范的西方人读中国书的方法与权力-话语分析之类的西方理论预设的陷阱。从移植来的那一天开始,如何摆脱“东方主义”的阴影,既不失语也不流于夜郎自大的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仍然是始终在寻求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基本窘境。
“神、鬼、祖先”是西人观察中国乡土宗教后建构的一种认知范式,影响深远。显然,康著描述、阐释的胡仙敬拜对这一认知范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遗憾的是,康著的叙述架构却完全依赖该模式,一一对照地解析胡仙信仰中神、鬼、祖先的三面。这样,对其反复强调的流动的、易变的、一体的胡仙反而进行了机械的割裂,从而在相当意义上限制了胡仙敬拜这个案例本身可能有的认知意义。显然,尽管胡仙时而像神,时而像鬼,时而又像祖先,但它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更非祖先。对于中国人而言,胡仙就是胡仙,而非别的。
已经有学者指明,康著涉及的狐与巫觋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事实上,康著所讨论的灵媒多数来自文献,就是她作为重点分析的波罗镇的胡仙-雷武在她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时也已经过世。这种研究者与现实生活中活态的灵媒的“间离”或者是造成她上述不足更为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康著断言复杂的王奶奶信仰明显缘于胡仙信仰也需要进一步斟酌。该论断的证据主要是零星的文献资料和顾颉刚等人早年调查资料中提到王三奶奶穿着三寸金莲。在正式出版的专著中,康笑菲在列举了周振鹤、顾颉刚、李慰祖、坦布鲁克以及殷兆海、吕衡等人的记述后,论述道:
尽管资料之间存在差异,显然王奶奶的崇拜源自于民众关于胡仙的信仰,并且王奶奶本人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女性灵媒和其他边缘化女性的代表,这些女性灵媒和边缘化女性在当地社区生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对妇女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其实,在过去以及当下的田野事实中,自从汉族妇女普遍裹足以来,三寸金莲是许多女性神灵都要穿的。2006年,在山西洪洞羊獬“迎姑姑”的仪式现场,传说中的娥皇女英仍然穿着醒目的三寸金莲。而且,作者反复引用的李慰祖的研究也曾明确指出丫髻山王奶奶和妙峰山王奶奶的区别,云:
王奶奶不是一个,有东山(丫髻山)“王奶奶”,有西山(天台山)“王奶奶”,我是东山“王奶奶”,原本是京东香河县后屯村的人,娘家姓汪,西山“王奶奶”,跟我是同村的人,娘家姓李,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天津称“王奶奶”作“王三奶奶”,现住妙峰山,那又是另外一个人,她并没有弟子,也并不降神瞧香。
在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指导下,当然也差不多完全忽略王三奶奶胡仙性质的吴效群以及王晓莉对妙峰山进行了详尽的民俗志研究。如果作为华人且熟悉北京的康笑菲能够注意到国内这些学者基于田野的新的研究成果,那么妙峰山的王奶奶就是胡仙这个论断可能会更谨慎。当然,重古文献而相对忽视近期国内有的用汉语写作的同类研究应该是英语写作者的一种基本取态、惯习与策略。
总之,时髦的权力、话语分析为康著增彩、增色。但是,因为完全将文献作为事实而忽视了文献的文学性、审美性与娱乐性,即文学的情感性,同时也忽视乡土宗教的情感取向,康著分析、阐释的信度也就打了不少折扣。当然,正如历史学家陈学霖研究八臂哪吒城传说时完全忽视口头文学“止增笑耳”、“闲坐说玄宗”式的生活意义之不足一样,这种用西方理论来读解中国经验,表述的吊诡或者是中国学者与海外汉学家们研究中国时共有的困境。
四、千年之狐与百变之狼
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
千年修行千年孤独
夜深人静时可有人听见我在哭
灯火阑珊处可有人看见我跳舞
我是一只等待千年的狐
千年等待千年孤独
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
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
我爱你时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
离开你时你正金榜题名洞房花烛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
你看衣袂飘飘衣袂飘飘
海誓山盟都化做虚
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
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
你看衣袂飘飘衣袂飘飘
天长地久都化做虚
2006年,自小生长在黔东南丹寨县的玉镯儿(孙红莺)经过近十年的磨砺,终于将上面这首歌词定名为《白狐》。同年,歌手陈瑞的首唱使这首歌不但迅速红遍网络,还成为电视剧《聊斋2》的片尾曲,大江南北传唱声不绝如缕。竞相传唱者潜意识里视自己就是那只情深意重,善良,执着,美丽而哀怨的白狐。在很快因为创作权的问题惹下纠纷后,这首歌更是出现了多个版本。这个直白心声,吐露心迹,快意恩仇的流行文化现象很有意味。它表达的已经不是《封神演义》有的对媚人、惑主、祸国的九尾狐的诅咒,而是诉说着当下国人对“狐狸精”的喜爱、痴迷,肯定的是“千年修炼”的坚持、“千年不变”的操守和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理解、温存与浓浓的绵绵爱意。同样一只狐狸,经过千年的修炼,不但楚楚动人,还凝聚美德一身,洁白瑕。
在欧美,俚语“她遇见野狼了”说的是一个女孩儿失去了贞操。这句口头禅源自如今世人皆知的“小红帽”故事,是这则故事近三百年来因应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在传承传播过程中次生的文化现象。凯瑟琳?奥兰丝汀指出,因应18、19世纪浪漫主义、民族主义,20世纪女权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语境的变化,这个原本诞生于法国太阳王时期宫廷贵族之间的色情故事不断被改变、伪装。故事中的小红帽也因此先后经历了向谨慎但仍需男人拯救的小女孩,展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女性新貌的好莱坞的脱衣舞娘,及至向狼宣战并驯服狼,潇洒自如的“与狼共舞”的现代女性的转变。与之相应,原本凶狠、自由、为所欲为的狼则发生了被驯服、击杀,主动向小红帽讨好、献媚,甚至需要小红帽的引领、保护等根本性的逆转。不仅如此,今天西方的护狼人一度直接将狼这种野生动物的骤减归结为小红帽这则故事的缪传。
同样是与人类相处的犬科动物,西方的狼和东方的狐狸都与相应地域的人群发生了紧密的关联。狐媚、狐臭、狐狸精、骚狐狸、野狐禅、狐狸尾巴、狐假虎威、兔死狐悲、狐群狗党等这些耳熟能详,老幼皆知的语汇都表征着中国人、中国文化与狐狸之间的紧密关系。论是憎恶还是欢喜、爱怜,中国人更愿意与狐狸发生关系,交往,并且还希望它千年不变。甚至在科技文明已经昌明的当下,依依呀呀地将自己幻化为狐,幽怨地也是急切地期待狐狸精显身,期待喜爱狐狸精的人浪漫,温情,义反顾的大胆!与此大相径庭,在西方,人们则随意、任性地将狼在自己的手中捏来捏去,玩弄于股掌之间,不时地转化着狼的属性。这难道是源远流长的胡仙信仰的罪孽?是女娲娘娘震怒之下派送的九尾红狐——妲己——的阴魂不散与强劲?
显然,这是一个东、西方之间待解的文化之谜。或者,它也是永远都法解开的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