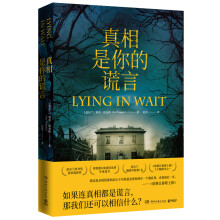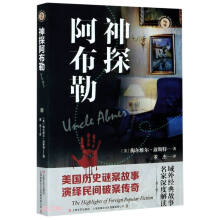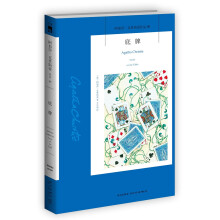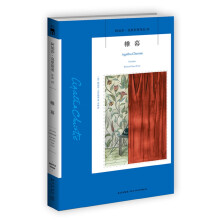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与10余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相比,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增订。
首先对“订”的部分做一番说明。
首先,此次之“订”视旧作之冗字冗词冗句若仇雠,一律删而去之。论述逻辑上的漏洞也尽可能弥补。另外更重要的还在观念的调整,即求“事理”之“真”。所以此次所“订”着力较多者还在观念方面。
其次,旧作曾对理学的“形上之思”与“形下之用”作过两分的区别,并且指出:理学的形上之思主要袭取自佛老“二氏”,其形下之用则来自“自家”的传统文化——主要来自儒学。《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强化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如若不将理学作“形上”、“形下”的区分,对于明代理学向清代考据学的转轨便终难免雾里看花未着堂奥。明白了这一理数,则理学清算运动为何以“辟二氏”为津筏便可了然;清代“汉宋之争”中“道问学”、“尊德性”的确切内涵也就可以看得真切。
再次,此次所“订”,对“春秋重义不重事”尤其是对刘逢禄的“实予而文不予”及其妄解《左传》的批判着墨较多,希望以此为剖析魏源、康有为乃至于后起的“古史辨”疑古史学作一先发性的铺垫。
此外,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以西学对中土的影响而言,无有可与严复版的线性进化论相比肩者。线性进化论同样也是五四以后“古史辨”疑古史学治史方法论的基石,疑古史学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如过分“证伪”以及时人所批评的“默证法”等,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线性进化论的理论踪影。以此,批判地剖析线性进化论,尤其着眼于其对于历史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就成为此次所“订”的重要内容。
另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成了此次“增”的部分。
首先,清初学者戴名世原并不为学界所重视。这或许是因为戴氏早遭《南山集》文字狱迫害而罹难,其著述因此大部飘零散佚而使然。戴氏是清代最早重视老子研究的学者,开清代诸子学研究之先河。是故此次“增订”,将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5期的《戴名世学论》补入。
“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不仅深刻影响着明清学风的转轨,是理解理学向考据学推身移步之枢机所在。承袭清初“弃虚蹈实”之风,清儒根本否认宋明儒之“尊德性”也是一门“学”,且其“学”之绵密精致宏阔,连戴震、凌廷堪这样一些不满足于斤斤考订,乐于作“哲理性思辨”的学者却仍然蔑视宋明儒的“形上之思”。此种学理上显现的悖论最可见出“汉宋之争”蔚然成风后的影响。且此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初的“科玄之争”。即使到了现今也不能说此种影响已经踪影全无。戴震、凌廷堪种下的思想胎苗到了五四以后终于“弄假成真”,“礼教吃人”竟然发酵为一种社会思潮,并且与广义的“疑古”产生了息息相关的联系。缘此,此次“增订” 新增了第二章。其中的《“尊德性”还是“道问学”?――以学术本体为视角》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4期;《“道问学”世风激荡下的戴学与凌廷堪》原以《戴学与凌廷堪》为题发表于《史林》2008年第3期,此次作了部分文字上的修改。
在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运动中,诸子学研究的诸多课题都曾是学界争论的热点。大批一流学者参与到这一场大讨论中,大大促进了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探讨这一诸子学研究的“转型”过程实质也就是在探讨“哲学史”这一门学科如何在中国“落户”成型的问题。在诸子学问题的大讨论中胡适、章太炎、梁启超恰处在“新老交替”的关节点上。缘此,此次“增订”将原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的《“新”“老”之争与诸子学研究的现代转型》置于第六章中的一节。
蒙文通同样是一位处于“新老交替”节点上的学人。他能够既取今文经学重“义”之长以补古文经学枯涩之短;又能取后者重“事”亦即重“史”之长而纠正今文家“春秋重义不重事”方法论的大缺陷。蒙氏身处古史辨疑古思潮世风的激荡之下,疑古学在蒙氏治学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厘清蒙氏之学既是“现代疑古思潮研究”的应有之义,对于客观公允地评价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疑古运动也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据此,此次将发表于《齐鲁学刊》2010年3期的《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增补为第六章中的另一节。
钱穆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不仅是今天进行诸子学研究的必读经典,此书根本就是20世纪30年代诸子学大讨论的直接成果。50年代,因郭沫若《十批判书》涉及“抄袭”钱穆《系年》而引发了余英时先生揭露郭沫若的一场学术公案。无论是钱穆的《系年》还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都可视为疑古运动的产物。考虑到《系年》与《十批判书》本身即与“疑古思潮”相关联,且对如何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问题的讨论,其于端正当下学界的不正之风亦意义重大。故此次的“增订”,将《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发表的《(互校记)与(先秦诸子系年)之史源发覆》作为“附录”收入。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