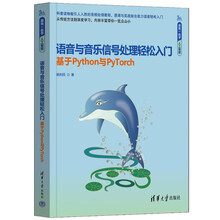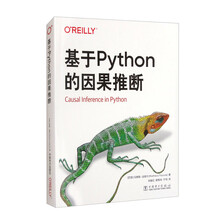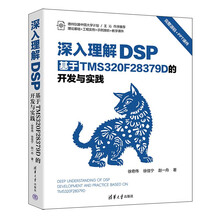当然,余英时在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他的导师杨联陞。余英时在《从(反智论)谈起》一文中写道:“我到美国后,中国史的业师是哈佛大学的杨联陞先生。杨先生既渊博又严谨,我每立一说,杨先生必能从四面八方来攻我的隙漏,使我受益无穷。”⑧他在《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中回忆了杨联隍对他的影响。余英时认为:“继钱宾四师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平生最敬爱的老师。和钱先生一样,杨先生是塑造了我个人的学术生命的另一位宗匠。”④余英时这样说有充分理由。早在1956年1月,余英时写成《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土族大姓关系》的再稿之后,就送呈杨联陞指正,杨联隍的批评第一次把余英时带进了日本和西方汉学的园地。从1956年秋到1961年冬,余英时做了杨联陞五年半学生后,后来又和杨联陞一起教了九年的中国通史和中国制度史(1966~1977年,中间包括两年在香港任职)。在《胡适杨莲生往来书札》序言中,余英时写到:“我从来没有见过适之先生,但是我在学术专业上受惠于莲生师的则远比他得之于适之先生的既深且多。”⑤
1962年,余英时的博士论文《东汉生死观》发表。此书在写作方法和观念上,明显受到杨联陞的影响。比如余英时重视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杨联隍也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官员、民众的日常安排的论文,后收录在《国史探微》一书中,题目是《帝国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就是运用的这一方法。余英时在《汉代贸易与扩张》自序中写到:“我要特别感谢哈佛大学的杨联隍教授,他不仅指导了本书每一阶段的写作,而且亲自作序为本书增色不少。”余英时在离开哈佛去香港中文大学任副校长时,1973年5月10日,杨联隍写诗勉励道:“少年分袂易前期,壮岁扬鞭莫复时。沩仰清风濡沫侣,摘茶拨火总相思。(作者注:用百丈及沩山仰山事)”①5月12日,余英时的和诗则是希望能早日回到老师的身边:“未行先自讨归期,怕向名场竟入时。岭外梅花任开前,康桥风雪最相思。”表达了对老师的深切思念。1976年1月,余英时40岁生日时,杨联陞将自己与胡适的长年往来的书信复印本送给他做礼物,扉页即是上面提到的诗句:“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当时余英时刚从香港返回,何俊认为:“大概正是体会到弟子的心情而示以老师的宽慰、提示与勉励吧”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