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8 年,大清帝国相当平静。消息灵通一点的人士听说中俄关系一直不太顺利,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崛起,打得喀尔喀蒙古人往长城一带逃难。但都好遥远啊!长江中游的武汉虽有军队因遭解甲而闹叛变,但也很快平息下来。
上了年纪的人,记得的却是很不一样的情景。50 年前,大股的农民军活动在华北平原上,至于在后追剿的明军,也同样有些不受控制。嗜血的乱军在攫掌大权之前,曾在富庶的四川盆地停留过短短一阵子。盛产稻米的江南,则因时政隳败不堪,北方义军南下,激起佃农、农奴群起暴动。至于南部沿海地区,握在沿海掌握海军大权的督抚的手里,是否支持明室,多半要看是否于己有利。明朝帝国的东北边疆,有一支民族“”女真“”,本是明朝的藩属,此时也已重整旗鼓,改叫自己为“”满洲“”,正逐步占据汉人的城市。
1644 年,北部的义军攻下北京,但不过 10 个星期便又遭清军逐出。清军声称入关是为了平乱,也要替殉国的崇祯报仇,但后来却宣布建立他们自己的“”大清“”。清兵入关的动荡,蔓延极广但时间不长,到了 1650 年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牢牢握在清廷手里。17 世纪 70 年代,几位先前变节投靠清廷的汉人将领作乱(三藩之乱),又陷中国数省于动荡,但最后终究败亡。明朝遗民最后一位反清的大将,盘踞台湾的延平郡王郑成功之子郑克塽,也于 1683 年投降。
儒家一般认为孔子之道,夷狄可教,只有几位像王夫之这样的人除外。他们知道中国周边有小国如高丽、越南、琉球,同样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们也知道日本以前就是这样,如今,他们对 17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虽然所知不多,但掌权的幕府将军爱读《易经》,一心要在掌统治大权的武士阶级里注入文雅一点的规矩,他们绝对见怪不怪。满洲继承的则是中亚的治术,和蒙古人、奥斯曼的传统没多少不同。但他们在1644 年前,就已标榜自己具有中国政治传统的嫡传身份——虽然未必服人。
1688 年,当朝的清帝已经迈入年号康熙的第二十七年。“”康熙“”虽只是“”年号“”,当作朝代系年之用,但中国一般皆以年号称呼皇帝,我们自然随俗。满文是康熙皇帝的母语,但他接受过很好的汉文化教育,也学得很认真。他和臣子在朝中日日商讨朝政,都有详细的记载(《起居注》)。而康熙朝的记载里会出现“”有治人、无治法“”这类儒家常见的古训,自不为奇。所以,我们知道康熙和臣子常花许多时间商讨各官位的人选,比较各人的优缺点,想用什么办法把脱序的官员拉回正轨,但又不至于毁了他的前途。
从公元 11 世纪以来,科举考试便一直是中国的社会精英将活力和野心注入朝廷中枢、服务社稷的首要管道。1688 年 4 月,从全国各地来的数百名士子,齐集京师参加“”会试“”。这些人都有幸挤过科考最难过的窄门。通过地方的考试(童试,院试)后,就有“”生员“”(秀才)的封号,小有社会地位,也可以减免税赋,但还没有做官的资格,也不是就此一劳永逸。秀才此后还是必须苦读不辍,定期参加复试。下一步则是最困难的:每三年就有数百名士子齐聚省会(参加乡试),关在贡院一长列的小考试间(号房)里,几天几夜埋首回答纵贯经史子籍暨治国之术的题目。这么多士子齐聚省城,可是难得的盛事。赴试的人忙着交换学问、政事的意见。没事的人忙着看榜,打赌谁会上榜。每一回科考的录取率可能低到百中只取二三人。在乡试里考中“”举人“”,就可以出任低阶官员,或到京城参加“”会试“”。士子未必个个是富家子弟,清寒子弟进京赶考的路费往往还得靠人济助;而济助的人,一来是敬佩他的学问,二来是巴望他哪天直上青云,会记得当年的贵人。
会试是在京师里的孔庙里举行,就在紫禁城东(顺天贡院)。考会试还是一样,士子一概关在贡院的小号房里写一篇又一篇的八股文。考过的人获颁“”进士“”头衔。最后一关叫做“”殿试“”,从命题到评选,皇帝都亲身参与,决定上榜的名次。高中前几名者,立即名扬名下,可能获派出任京师学术机构(翰林院)的要职,各方皆寄予前程似锦的厚望。
1688 年 4 月 28 日,读卷官将该年 176 名录取的进士以及前十名的名单,进呈予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心里早就有数,除了一一垂询排名前几名的考生人品如何,还点名同乡的大臣回答。有一份考卷还没拆封,康熙皇帝就认出来是查嗣韩的考卷,他说他先前看过查嗣韩的墨卷。查嗣韩出身中国东南部的浙江望族。查家曾参与反清复明的运动,备受地方敬重。康熙皇帝看了几份考卷,和大臣讨论优劣,便将查嗣韩从第四名拉到第二名。但这样一来,前三名就全是浙江人了,他觉得不太好,就再琢磨了一下。第二天,新科进士由人引进太和殿,向皇帝行磕头礼(三跪九叩的大礼),皇帝高坐在龙椅之上,在殿内的阴影里几乎看不见身影。
虽然儒家古有明训,但治国可不仅是知人善任、尊儒向善就好。苍生住在大地之上,以大地为生。君主还需要征收徭役,以应维持社会秩序之需。君主也要剿匪平乱,保护人民的身家财产。君主要视可教者,给予受教之机会,充实仓廪以备荒年。维持运河畅通,注意灌溉、防洪。徭役的负担既不得过重,又得兼顾损益平衡。中国政治家讨论到这些问题时,自然会去援引中国君主从公元前 200 年的汉朝即已试过的各种做法,论其优劣。
清廷当时有一项政策的挑战,历史就更久远了。早在公元前 2000年,古代的大政治家大禹就曾治水,开渠疏浚,引水入海,救溺于天下。之后,大禹因之获继任为帝,任内分九州,“”任土作贡“”,调查各地的土质、田地、贡赋、产物等。1688 年,有位大学士在当廷论政时提到《禹贡》一书,皇帝反驳这是“”不知黄河之性,故有是言“”。不过,传说里大禹号令众人、疏洪治水、百折不挠的干才和毅力,于当时苦思黄河、大运河治水难题的官员而言,却另有深意。
黄河流经的高原满布黄土。由于水性不驯,不时改道,泄出河水挟带的大量黄泥沉积在华北平原。孔子时代之前的统治者,曾先以筑堤防洪的方式排干部分平原的水,开发农地,然后才疏导黄河流向。结果,淤泥大部分沉积在河道里,终至河床高过周边平原。明清时期,情况又因大运河的运输重要,而益显复杂。江南盛产稻米,盈余即由大运河北运京城。而大运河、黄河、往南一点的淮河,以及洪泛平原区的连串浅滩湖泊,都有复杂的水流互动。因此,整区的水系都得时作监测,集中管理。但到了明朝末年,这方面的工作愈益荒废。淮河的入海口因之淤积日高。下游的水道又未见疏浚,河床和水道愈积愈高,洪泛也因之而日益频繁。1677 年,清廷决定治水,封靳辅为河道总督,负责疏浚筑堤的工程。但水患不去,以致靳辅的做法颇遭非议。
也因此,1688 年 4 月 8 日、9 日,康熙皇帝决心直指问题的核心,召集与闻黄河治水的几位官员,齐集御前。众臣当中,以京师巡抚于成龙批评靳辅最力。他指责靳辅没有疏通主要河口,任令洪泛肆虐淮河、长江之间的富庶地带。劳役也过重。靳辅还把官府征税丈量多出来的无主民田,没收作军方屯田之用;屯田的钱粮本作军用,目前转作治水。于成龙说,如今江南之人对靳辅只想“”食伊之肉“”。靳辅则回答,这是为了打击地主滥权占地。御前的这场诘难辩论,全在康熙掌握之中。他追究细节,点出大臣无知之处,提醒大臣他这位皇帝可是曾在南巡期间亲自走过几处主堰的。康熙一再点明臣子应该顾全大局,不能只是顺应地方舆情,因为地方居民才不管洪水改道是否淹没邻县。大臣有错遭皇帝指正,就马上跪地磕头谢罪。最后,看来是靳辅应该为推行屯田政策、不得民心,未将主要河口疏通,负最大责任而革职,但皇帝暂缓发落。康熙说,等继任的人做了六七年,看他治水的成绩再来定靳辅的罪吧。
康熙 1689 年第二次南巡时,再度巡查了江南的水系,在看了靳辅做出的成效,工程又极艰巨后,便将靳辅复职。靳辅河道总督一职,一直当到他 1692 年去世为止。靳辅在 1688 年时地位不稳,是因为他和大学士明珠有牵连。明珠那时刚失势。康熙当然知道政治风向的影响,但他也看重人才和事实,碰上难缠的水患更是如此。现代世界早期的君主,都知道藉仪式示惠或施威、彰显王者的威仪有多重要。康熙在这上面,和同时代的奥朗则布、路易十四不相上下。但在中国,因儒家重礼法的思想,而使仪典多加了一层审慎、自觉的色彩。康熙自幼浸染汉满两方的礼教,展现出来的便是礼遇良臣的英主和孝感动天的孙子。1688 年 8 月 9 日,康熙皇帝召见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靖海侯施琅。施琅在 1683 年率军攻克台湾,平定中国最后一处反清复明的组织势力。康熙将他自己颈项上的有里蟒披领一件,脱下来挂在施琅脖子上。8 月 10 日,康熙再召施琅至乾清门。乾清门是一座游廊状的建筑,一般用作非正式御门听政使用,位于紫禁城外朝的大殿后面。康熙皇帝还从他自己的盘子里,挑了些东西赐给施琅吃。
这是极大的优遇,写《起居注》的人仔细记下。皇帝只要一有机会,一定不忘要大臣知道,他对替他好好做事的大臣有多好,他自己对人的判断、对情势的掌握又比他们强多少。君主知人善任之明,是儒家治国之术的准则之一。但康熙喜翻自己的记忆库自夸一番,却是这位皇帝独有的性格特征。他老爱提醒大臣他知道谁的缺点,记得谁做的错事,但还是准他留任官位。也因此,皇帝的缰绳拉得不紧,大臣最好时刻感念于心,却又要随时提高警觉以备考核、监督——这便是康熙朝中臣子或将军的命。康熙皇帝再次召见施琅时,就特别赐这位老将进入他就寝的内廷乾清宫。这里除了皇帝、后妃、太监,一般不准外人进入。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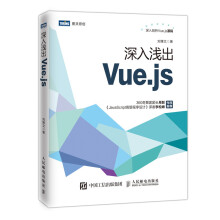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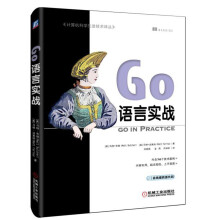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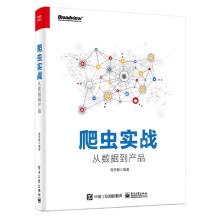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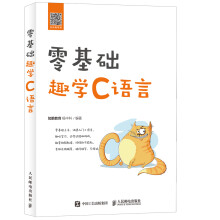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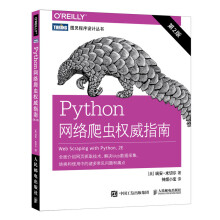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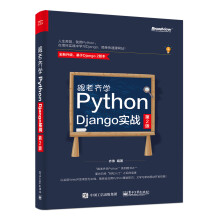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景迁
威尔斯在风平浪静的历史表面之下,看到了各国之间人口广泛而深入地交融、交流的真相。这让我们知道,在三百年前,全球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启动。
——《华盛顿邮报》
小约翰·威尔斯在这本书中,对这个世界的描述采取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写作视角。由于他对于所有国家的情况都很了解——从中国到秘鲁——所以能够站在全球范围的高度用鲜活的小品文去描述熙熙攘攘的城市、奢华的庭院、腐败的政体、商业的天敌、权力的滥用以及艺术的辉煌。
——《泰晤士报》
作品生动地呈现给我们1688年的生活图景,其中充满了令人惊骇的暴力,但同时也洋溢着让人感到亲切舒适的人间温情。
——《出版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