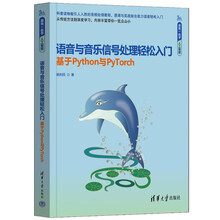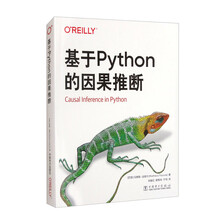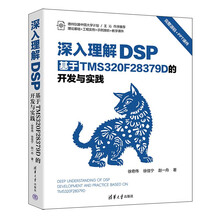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戏曲研究(第九十一辑)》:
五
葛藤梳理至此而毕。若摒弃一些非艺术性的短期效用因素,拾级以寻“内化”的山阴道,则以“红腔”为镜以观察“芳腔”,未必不能有一些意外之得。笔者尝试归纳为下面几项:
1.月阙之曲
依笔者所见,《芳腔新唱》中的曲目,可一言以蔽之,就是“阙”之歌,不圆满之歌。不圆满,可呼天抢地,恨天地,打鬼神,红线女回国之后所唱之《打神》一曲即是(王魁与焦桂英的故事,见《红线女:云雀奖金曲会萃》)。此曲无论曲辞及其处理腔线的刚劲手法均近乎西方的阳刚美,借用华裔法国艺术家程抱一的说法,“也就是男性、力量、对物质的征服”。但是,反观同样含冤莫白的《窦娥冤》(《芳腔新唱》),却偏偏绝少激烈的唱段。一句叫头白:“飞霜,飞霜!”只闻得若有似无的嗟叹而已。
美原是可以在不同层面展开的。李煜去国归降,愁如一江春水,但吴冠中在水墨画《朱颜未改》等作品中,却把李煜词的悲怆提炼成完全不同色温的视觉符号。他说:“李煜哀痛地思念他失去的豪华宫殿:只是朱颜改。流水留不住落花,落花留不住红,谁也留不住红。我浓抹重彩,一味显示朱颜未改,或朱颜不改。”①好一个华丽的转身!但这不是李后主,毋宁是吴冠中本人对生命流逝这一永恒悲怆的回答。“红腔”同例,红线女以阳刚奔放抒悲,除了个人声音条件,亦与其美学和人生取向有关。她在其上述唱片集中便自言:“林黛玉看到落花就难过……其实落英缤纷之日,也正是枝头挂果之时。园丁是不会闻风落泪,对月伤心的。”“我喜欢朝霞,也喜欢晚霞。黄山的日出和日落,都是出奇的绚丽、壮观。”经历过失败的婚姻和其后轰动一时而终归寂灭的爱情生活,她在其自传中仍顽强地说:喜欢话剧《原野》中和所爱的人冲破礼教樊篱、远走高飞的人物金子。这便是红线女在命运叩门时的回答:一个声音的吴冠中。
以高昂饱满的意态追梦园梦并不坏,但愈纯净的自觉意志,亦有使主人公的形象单薄甚至变形的危险。中国传统乐论有所谓“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史记·乐书》),以为不填满的“阙”才可以让人有更多的回思、联想,这确是前人的智慧。节,要求含蓄、收敛、矜持。中国人是非常敏感的,有关个人内心生活的一切,最好是间接地、暗示地表现出来。例如木兰远征归来,弟弟不是来一个拥抱,而是把欢欣转化为“磨刀霍霍向猪羊”;由于向内,“敏感”的心便留有不少供回想、重塑的空间。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曾调侃说:“致力于高标准散文的书,永远会因为没有给予读者足够的信息而遭到指摘。”①芳艳芬的“高标准”便是从不让声音塞满你的耳朵,你的“耳室”永远有足够的空间留下“客人”。粤曲票友有所谓“歌场散罢语喃喃”者,就是启动起自己的所有感官,循着曲中指引的点滴星光去追寻那未尽的余音。芳腔总没有听完。都给了,还“喃喃”什么!
阙,不只有一个“不圆满”的实义,更不会只剩下一个“限”的方向。芳腔唱段绝少咬牙切齿之声,即有,我们往往更多地被其中“只怕见得痴人心不安,不见痴人心又想,想起当年韵事岂能忘”(《洛水恨·南音》)的柔情所化。学者刘小枫在颂许波兰导演基思洛夫斯基名作《红·白·蓝》时说:是的,人生就是不圆美,在给种种偶然性击得遍体鳞伤的人生中,掇拾、珍惜、抚摸那爱的碎片,抱慰在爱中挣扎得遍体鳞伤的个体,颂唱生存惊恐中的宁静、破碎中的无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