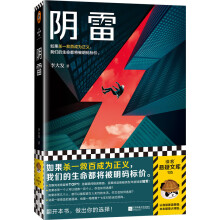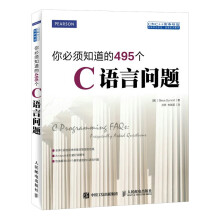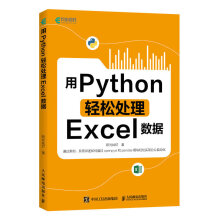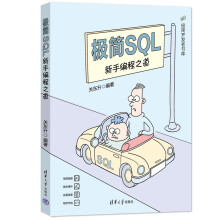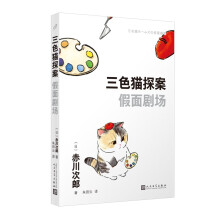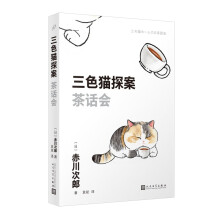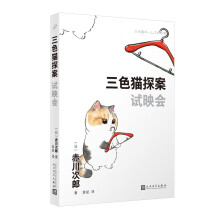五公子的悲怨痛悔之心,激荡于轮唱之间,在当场自悼悼人,比起巫觋悼亡之悲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相比关于父亲的那些堂皇颂歌来,其深切程度更是相去难以道里计。②
商代巫风卜卦极为流行。《尚书·伊训》云:“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现在所见的甲骨卜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和周易的卦辞,多是殷代的产物。从这些文献看,神灵意志高于一切,举凡大小事,都得先请巫史占吉凶。巫史卜卦,是未行事而先问神,具备前晓先知、弭灾趋福的安慰,显示了人的部分主动性,所以能取巫舞权威而代之。而原本在野外求神娱鬼的巫歌觋舞,此时则常常退居于宫室之中,成为歌颂武功文治,享受声色之乐的娱人乐舞。《墨子·三辩》云:“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日《护》;又修《九招》。”则已从夏禹作乐的“以昭其功”,开始转为娱乐性乐舞了。商代乐舞从夸功到娱人的变化,是歌舞艺术渐次获得以展示人体美、乐声美为主的艺术品位的过程,也是巫风与乐舞相为交融的过程。这种交融的后果,使得殷末的歌舞,每以声色感官刺激为事,“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史记·殷本纪》),这便是周武王斥之为变乱正声的“淫声”,是后来所谓亡国之音论的起点,也是唐孙綮作《北里志》,使“北里”成为妓院代称的远源。
周承商制,由司巫掌管群巫,分管舞雩、祭祀和丧事。按性别分来,其中的“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噗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③。这些严肃和悲哀意味的祭祀和卜卦活动,实际上令巫者并不轻松。因为年终还要总结,估算其祭祀预测的准确度如何。
较为宽松而充满艺术意味的活动是周代乐舞,这是敬神、祭祖和歌功的综合呈现。乐分雅、颂,舞有大舞、象等目,《诗经》便是这样一些乐舞的文学底本。所以《左传》称季札观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而“见舞”《大武》、《韶、凄》。以娱悦感官为主要目的的殷末靡靡之声,则被以周武王为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一概废止。理论界中,从季札到孔子,都把乐舞的情感表现,仅仅限制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类准则内,对艺术精神的自由发展,对悲情喜意的充分表现,对宗教气氛的神秘弥漫,都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毂梁传》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述过孔子对国君悦伎乐的不满,乃至在外交场合颊谷之会中杀戮齐国优人优施的事实。①
战国时期,中原巫风已经大抵消融在或规整化为仪式或审美化为歌舞的种种分野中。事实上,巫觋史占等传统神职人员尽管充当着神意下传、人意上传的角色,有着令人尊敬的位置,但也有失灵招祸、自败其身的时候。《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旭。”②《杜注》云:“巫埏,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或以为桎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谓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这位最早留下诨名的求雨女巫,竞因法力不至,雨神不降,被怀疑为仰鼻致旱的罪魁,险些落得个焚身以惩的悲惨结局。
充满悲剧精神和浪漫情调的巫舞觋歌,本时期在巫的故乡楚国一地继续蔚为大观。屈原的《离骚》便充满了“巫咸将夕降兮”、“欲从灵氛之吉占兮”的巫风精神。他的神游太空,也可看成是降神状态下的奇瑰想象。而《九歌》则更是刻意所作的巫舞之曲。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