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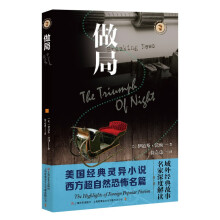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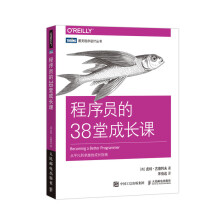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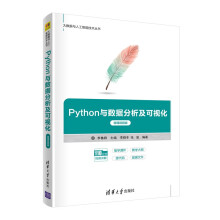



在网络社交极其发达的今天,我们失去可独处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孤独是强大资源。它能激发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的创造力蓬勃发展,并改善了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并出乎意料地与他人建立了关系。孤独的力量是我们正在失去的一种力量。适当的选择独处,享受孤独可以让自己更好的融入社会。
1. 此刻不再迷失
无论我在写什么,我的爱人肯尼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他“漫不经心”是因为他明白事理,不会在餐桌上激励一个作家。)但当我告诉他博恩医生的故事,并且说我想写点儿有关独处的文字时,他放下手中的啤酒,看着我说:“你尝过独处的滋味吗?怎么说好呢,你独处过一天以上吗?我是指真正的独处。”
他刚说完,我也放下了我的啤酒杯。我皱了皱眉头,凝神望着前方。“我一定尝过……”当然,我并没有,没有真正意义上尝过独处的滋味。他用令人羞怒的理智暗示我:我可能想要体验一番。
我反复玩味这段对话,但无法忽视我已被挑衅了这个事实。我眯起了眼睛。下周肯尼就离开了,我默默发誓,我会用一整天的时间体验独处——不与人交流,也不与他们的电子头像打任何交道。
但当这天到来时,我于早晨九点收到了一条信息,就像遵守某个巴甫洛夫定律一样,我查看了它。原来是一群身处郊外的朋友邀我到公园喝上一杯。不妙!
我作弊了。随后我又一次作弊。我去了次咖啡馆。我接了我妈打给我的一个电话。我外出慢跑,停下来抚弄了一条小狗。晚上睡觉时,我数了下,自己一共与人交流了十几次。我甚至无法独处一天。
我可能会偶尔将电话落在家里,或稍稍克制自己不算严重的贪吃习惯。但完全摆脱社会需求会怎样呢?我勉强记得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孩提时代,我会带着宝丽来照相机在森林里徒步,会整整好几个小时忘记其他人的存在。
我变了——只是长大了些,我就像钻进了将成年人一个个捆绑在一起的铁丝网里。有一天醒来时,我发现那些空白早已被忐忑不安所填满。我担心起朋友孩子的成长情况,担心起远房亲戚们是否快乐,担心起经济拮据的同伴是否安全,以及更为自私地担心起我个人的名誉(我粗糙的“品牌”)——一句残忍的网络留言,或一句含沙射影的闲谈,都会随时将它挫伤。简而言之,我已陷入困扰。
还有,可能改变的是这个世界吧。可能它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允许人们独处。又或者,更贴切地说,两股力量在融合——我自身在不停地成长,而这个世界也一直在自缚手脚。里里外外都变了,于是乎,在社会焦虑的薄雾中,我每天清晨醒来都会想:“我错过了什么?”我每天上床前都会想:“我说过什么?”
人间尘嚣,那如同自助餐般永久的纠缠,反倒引起了我对独处的饥渴。实则,我发现自己已如此饥渴了很多年,但这份饥渴如今开始驱动我了。几页书纸——和博恩医生这样的英雄——将这种饥渴转变成一种使命。我想再次与静寂的夜晚相守,再次体验那些我曾有过的无辜的白日梦,再次拥抱我所逃避的赤诚的自我(我逃离自我多久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何如此惧怕我那个安静的同伴?这本书最接近我心中的答案。
我要澄清一点:你接下来看到的可不是我对梭罗式林间茅舍的期盼。我不想逃离世界——我想在这个世界重新找到自我。我想知道,假如我们再次在夜以继日的喧闹中,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饮上独处的药酒,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向外迈开一步,执念于一次独处的漫游,也强迫自己去观察他人的社交生活。一对孤苦的少年情侣在岔道旁缠绵细语,在晨曦中挥手作别;离他们俩不远的草坪上,一位母亲正在和她笑颜永驻的婴孩玩躲猫猫;一位犹太教教士边打电话,边坐上他的奥迪车;一名女子从一辆咖啡贩卖车的窗户里探出身子,将一杯玛琪雅朵咖啡递给她的顾客,嘴里欢快地念着:“漂亮的女士才配得上一杯好咖啡。”在世界各地,在每个角落,我们将一份友谊献给彼此。着实,正是凭借这些柔软、持久的给予,我们的文化、我们身为人的物种,才得以生存。
我们已确知,要想在大的种群中生存,动物的大脑——尤其是大脑新皮质——就必须十分发达。事实上,灵长类动物的社会复杂性的一切标志——种群的大小、为同伴理毛的派系、交配战术、骗术、社会娱乐——与该灵长类动物大脑新皮质体积的相对大小密切相关。大脑新皮质体积越大,该灵长类动物就越擅长社交;它们越擅长社交,它们所生存的种群规模就越大,它们就越不容易出现种群内部的暴动和捣乱行为。
此处有数据为证。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他的“社交大脑”理论时,发现类人猿大脑新皮质体积的相对大小与它们种群之后发展规模的大小直接相关。例如,夜猴和绢毛猴有着与它们大脑尺寸相适应的较小的大脑新皮质,它们成群外出时数量少于10只;黑猩猩和狒狒有着相对较大的大脑新皮质,它们的种群成员一般有50来只。纵观我们的历史,绝大部分时间,人类的社交圈子里都约有150个人——我们同样也(毫无悬念地)有着灵长类动物里最大比例的大脑新皮质。邓巴的结论是,我们庞大的大脑或许真的帮助我们学会了使用工具,但它真正的优势在于,我们借此得以扩大我们的社群规模。你有更多的同伴意味着你更有安全感,更有力量,传承智慧的可能性越大,最终,你活下去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邓巴还发现,灵长类动物的社群越大,社群成员花在社交性理毛上的时间就越多。所有的爱恋、沮丧和挑衅都需要动物们一直去监视和把控。在一大群灵长类动物中生存可是项浩繁的工作。根据社群成员的多少,灵长类动物为彼此理毛的时间最多可达一天内20%的时间。鉴于我们庞大的社会部落,当下的人类该是被迫每天花上一大段时间为他人“理毛”,这个事实让邓巴着实吃惊。那我们如何规避邓巴发现的法则呢?我们又该如何在让自身社交种群扩大的同时,不至于无奈地将所有的时间用于为彼此的毛发抓取所谓的虱子?
答案是横空出世的语言,这是仅仅有十万年历史的博弈改变者。为了替朋友或敌人抓虱子,没法说话的灵长类动物必须将手放在对方身上。事实上,一个能说话,不只是会发声,而是能说出复杂的社会意见的灵长类动物可以为他的社会部落的几名成员同时“理毛”。这可是技能上的一大飞跃。并且,一只会讲话的猿猴可不会傻傻地蹲在草丛里替别的猴子“理毛”;它会边外出散步或寻找野果,边替人“理毛”。这是强大的一心多用。语言的诞生令“理毛”更高效,也令“理毛”行为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凭借语言,我们的祖先能将复杂的想法从一个大脑传递到另一个大脑,合理地安排狩猎、觅食及最终的耕作等活动。依靠语言,我们得以让越来越大的社会部落维持稳定(也因此享受稳定带来的硕果)。
我们并不止步于此,继续开拓了新的方式,以扩大和强调我们的社交性“理毛”行为。于是,人类这种动物(携带着庞大的大脑新皮质)得以在结构和安全性算得上表面无损的情况下,在越来越大的种群中生存。由此判断,每种通信技术的出现——从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到印刷术,再到品趣志(Pinterest)社交应用——都在操控我们思维中一块最为基本的部分。反过来,这些技术夸大了我们为彼此“理毛”的能力,使我们得以造出巨大的城市,最终创造出“地球村”。而对于地球另一端的人——我们甚至从未与之谋面的那些难民和恐怖分子,我们则或同情,或厌恶。我写下这句话的此刻,地球上约有7,401,858,841人生存着,而每个人都潜在地与其他所有人关联着,于是,可能的联系就有27,393,757,147,344,002,220条。于是,我坐在这里,一个人在我小小的办公室——我的小房间——外面的世界可能闪现着超过270亿亿次的问候。
当然,这一改变还没在全球平均分布。正如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所言:“未来早已摆在我们面前,只是它还没有平均分布罢了。”是的,当得知世界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时,苹果手机爱好者是十分吃惊的。尽管如此,这一改变来势迅猛,无论是贫穷还是封闭,都不会让人们长时间地与网络隔离:2006年,世界上18%的人口在使用互联网;2009年,25%的人在使用互联网;而到2014年,这一比例上升到41%。这样的增长速度是现象级的。回忆一下即时通信系统——它支配了全新的现实,又最直接代表了我们在线“理毛”行为——是如何快速繁衍的:瓦次普(WhatsApp),即时通信平台中的王牌,2016年的用户数量达到了10亿。而这一壮举是瓦次普在两年内达成的。
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定义为社交性的动物,他的概括一针见血。我们总是希望他人对自己有较好的印象,这也是我们身为人的基本动力之一。而当我们不再面对面地交流,转而在基于电子屏幕的社交媒体上问候彼此时,我们就更能胸有成竹地呈现自我了。例如,看到脸书上有人说自己找到了新工作,我可爱但又焦虑的朋友乔斯琳会花上好几分钟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撰写她的评语,最终写下西米粒大的毫无冒犯之心的“真为你高兴!!!”(而在近乎疯狂时,乔斯琳可能会加一个马提尼酒杯图片作为表情)。当然,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大约15亿脸书用户中,使用脸书最频繁的是那些存在社交恐惧的人——尤其是那些急需获得社会认同的人。技术于是成了一剂药膏,成了一种让我们无须再为适应环境或归属而担忧的方法。并且,我们用网络问候彼此的冲动早已以惊人的速度成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一部分:2005年,美国只有8%的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站;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一跃上升到73%。与此同时,接近一半的美国人如今睡觉时都会将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把它们当成哄自己入睡的泰迪熊。身为人意味着要会社交,而身为一个在电子显示屏时代的人意味着要学会频繁社交。
问题来了。许多人不得不采用健康的饮食方案,因为我们置身于一个充斥着高盐、高糖、高脂食物的世界——我们不得不囤聚食物,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如此强迫自己履行社交仪式,已到了必须从类似吞食快餐食物的社交中将自己解放出来的时候。社交媒体已让我们变得过度社交了吗?正如饮食方面,我们不停地在吞咽同他人的维系,但这种维系从来没有得到恰当的滋养。
大脑新皮质——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开启我们的城市、政治、宗教和艺术的物质—— 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劫持了吗?
网络社交的冲动是何时变得真正令人害怕的?关注这类事件很像玩室内游戏,但2004年7月14日上午9:49却有所不同。那一刻,一个伙计在论坛上发了一个新帖子,他写了这几个字:“我很孤独,有人愿意跟我聊天吗?”十年后,沙龙网站(Salon)给这一连串回帖冠以“网络世界最忧伤的回帖”的名号。即便是在首个回帖发布的几天后,任何人在谷歌搜索引擎内键入“我很孤独”,都会被带到那里;人们在那里留言,诉说自己心碎的孤独感,同时也博得了一些微小的同情。事实上,很多人,在夜晚独自喝上几杯设拉子(Shiraz)葡萄酒后,会发现自己正朝着网络这一水域扔“我很孤独”这几个字。他们期待得到怎样的回复呢?“我们都是没用的人,都需要生活。”一个访问者敲下了这几个字。“仿佛不再有人是真实的了。”另一个人这么写道。没人去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和药物治疗,也没人去寻找男朋友或不抽烟的女佣。这反而只是一声数码层面的号叫。
感到孤独时,就诉诸互联网,这种做法并不罕见。我已习惯在谷歌搜索中键入无助的问题。我可能会输入“现在是巴黎时间几点”或者“一升有多少盎司”这些被称作“神谕似的搜索”(如同“求问神谕”中“神谕”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一样)。随后滑动一下,向搜索引擎提交更为情绪化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没人爱我?”
2004年7月14日上午9:49。那是个无聊的周三早上。可能就在那一刻,上网社交的冲动失控了。一个无名小卒——就让我们称他为埃迪——落单了,于是他想着可以上网找个伴。这可是件容易的事,“神谕”也那么吸引人。“我很孤独,有人愿意跟我聊天吗?”埃迪想要瞬间挣脱落单的局面,这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算得上新鲜的是那份从容,那份技术给他的温柔保证——他再也无须感到孤单。如果说互联网已俨然成为独处的破坏者,那么这个破坏者也是人们招来的。对它微小的入侵和狡黠的不公,我们早已习惯了心存感激。
截至2020年,大约300亿到500亿物件——如汽车、烤面包机、洗发水瓶将会同互联网相连;网上可获得物件的数量是我2016年写作本书时的3倍。从前,你的卧室里、地方公园内、飞机厕所里那些愚钝的物件将会焕然一新,将会令我们的上一代赞不绝口。(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一些成员早已开始将这些物件称为“着了魔的东西”——这使人想起了英国科幻作家阿瑟·C. 克拉克的话:“任何足够先进的技术都与魔法密不可分。”)这一萌芽状态的“万物互联”将会依赖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联系行为和反馈行为—— 一次永恒的社会共鸣,而此时断连将会成为一种罪孽。换句话说,我们生存的环境中将会有越来越少的砖和塑料,而有更多以云端为基础的设施。这些数字环境对断连望而生畏,将它看成孕育故障的温床;其结果是,人们的思维生态系统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万物互联早已开始。我们给停车收费器、电力网、货币、汽车、文件、食品储藏柜、衣物和饰品添加网络信息,从而建立了万物互联,这在二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与此同时,谷歌即刻(Google Now)用无穷无尽欢快而定位具体的建议给予我提示。采用声控技术的亚马逊智能音箱回音(Echo)可以像个云计算仆人一样干诸如记录订单、撰写购物清单和阅读食谱这样的家务。亚马逊盛年天空(Prime Air)也在竭力通过无人机运送包裹。有自我学习功能的家用电器追踪人们的活动,通过同步人们的行为,使自身的功能性越来越隐蔽。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在这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所处的位置,但我们每天都在证明(假如我们去搜寻的话)我们已将时间更多地花在纠葛而非独处上。
此种半人半机器的成就不仅在人类的栖息地展露,我们还想依葫芦画瓢地改造动物王国。例如,瑞士一些奶牛的脖子上携带着传感器和SIM卡,借此,它们可向农夫们发信息。这些设备可以告诉人们这头奶牛何时发情,而发出的信息差不多就是:“我已准备好受孕了。”羡慕吧,伙计。
我无法为奶牛们代言,但人类确实容易偏爱将所有物件和所有人都联系起来。正如邓巴的研究所清晰阐述的那样,这种欲望是根植于我们最本质的天性中的。当然,我们可不是唯一热衷于联系的生物,许多物种都是社会型的,但人类是为数不多的符合真社会性的物种之一(“真社会性”在英文中是eusocial,“eu”的意思是“真实”)。“真社会性”也是伟大的昆虫学家E. O. 威尔逊用来描述具备自我牺牲精神、能够多代生存的动物的术语。同威尔逊所研究的蚂蚁一样,我们人类也是高度配合的动物,我们生来就会不断地迎合集体的需求。我们当然也有自私的一面,但是,有多少次,我们会将利己的冲动搁置一旁,奉献自我,臣服于他人军事性的征服之下?又有多少次,我们像合唱团里谦卑的小学生,或威风凛凛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发明者,在集体项目的祭坛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在威尔逊看来,真社会性文化的演变,是“生命历史中的重大革新之一”(同鸟类翅膀的出现和花朵的出现一样重大)。
于是,这些强韧的社会纽带遮掩了其他的存在方式:我们人类现在一有机会就将独处驱逐出去。2013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约7500名美国智能手机用户中,80%的人在醒来15分钟内就会使用手机。在18~24岁年龄段,这一比例上升到了89%(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一睁眼就立刻伸手去够手机)。事实上,每4名受访者中就有1名在一天中时刻离不开手机。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这就是真社会性的献身。我们向庞大的社交网络扩展,但这种蔓延已远远超出了实用性;它完全是强制性的,是我们必须去做的,它是一条幻影般的脐带。在谷歌搜索中输入“恐惧”,搜索项会自动补全成“恐惧独处”。
与此同时,你若是输入“害怕没有”,那搜索项会自动补全成“害怕没有手机”。许多人强烈谴责“社交控”(FOMO)——害怕被遗漏(fear of missing out)的出现,但对我而言,这个词并没有捕捉到焦虑的气息。我外出散步,有一两个小时没带手机时,并不担心遗漏了什么新闻,让我担忧的是迷失了自我。如同恋爱中的人只能在爱人注意力的光亮中看到自身,我要是少了他人的注意,似乎就总处于消亡的边缘。
通过手机履行的社交礼节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激活我们的快乐/奖励系统,但这依然于事无补。当我和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沃特曼聊天时,她告诉我:“我们就是这么根深蒂固地想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状态。”沃特曼专攻人类的种种成瘾癖好。我们分享得越多,感觉就越好——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的:“我们自身的信息与许多人共享时,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变得活跃起来,这在只与少数人共享信息时是不会出现的。”当灵长类动物与整个群落打交道时,它的胸腔是扩张的。谁没在推特网上体验过当一个“看似信手拈来”但精心策划的言论被转发数千次后,那激涌的多巴胺带给我们的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