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块一张CD 所谓“发烧片”、“发烧音响”,说的是音质特 别讲究的音乐软硬件。殷殷追求这种讲究的玩家,自 然就是“发烧友”了。
在我等经济实力与时间精力均远不足以支应的乐 迷眼中,“发烧世界”是幽深奥秘的异次元宇宙,充 满了只可意会而近乎于禅的词句:“低频Q软而不松 ”、“中频紧实而不生硬”之类既无标准亦无法测量 的玄奥说法,都是常态。“发烧圈”最经典的套语, 大概是顶尖扬声器应当能听出弦乐的“松香味”—— 这以嗅觉形容听觉的妙喻,常被“非烧友”引来调侃 。此外,音响广告常有“听出耳油”一类形容,大抵 是旧时从香港传来的夸饰法。我有时也会想:到底什 么样的音乐,值得你我为它流一汪“耳油”呢? 少年时,曾到一位长辈家中作客。他是望重四方 的名医,墙上挂了不少博物馆等级的真迹。地下室辟 做试听间,摆了一对比人还高、像两堵墙竖着的静电 喇叭。线材皆粗壮黝黑,如蟒蛇横卧于地。前后级扩 大机、黑胶唱盘、CD机,无一不庞大沉重,面目阴鸷 。即使真有贼人闯空门,大概也是搬不动的。那天长 辈招待我们听了几张唱片,印象最深的是一张发烧“ 测试片”,里面收录了校准音响部件所需的各种声效 。他特别选播其中一曲,很短,内容简单扼要:一只 玻璃杯“哗锵”摔碎在地上。他反复播了好几次,并 且得意地问我们:可曾听出这玻璃杯摔碎的方位,在 右前方三公尺处?可曾听到一块碎片由右往左弹跳的 脆响? 我倒不至于轻薄地以为长辈花费相当于一队进口 车的资本打造这套发烧系统,只是为了原音重现摔碎 玻璃杯的实况——若是那样,未免也太不划算,还不 如买几百只玻璃杯,每天现摔现听。但我也暗自狐疑 :一旦“发烧”到一定的份儿上,“音乐”与“音响 ”究竟孰轻孰重? 《音乐与音响》杂志创办人张继高先生虽有名言 “音响只是手段,音乐才是目的”,他也曾形容暗夜 中看着“真空管顶上那点点橘红灯丝……温婉有光, 直觉上它散发出来的音乐,都是一种温存、一种美、 一种风韵、一种感激。”——你看,恋物、发烧,也 是需要教养的。
几年前,我接到音响展览活动的讲演邀约。我的 讲题是“我的摇滚发烧片”——任何门派的乐迷,都 有属于自己的“发烧”定义,我虽没有玩“发烧音响 ”的资本,却很可以聊聊某些唱片在录音、编曲、音 场处理各方面的巧思。当然,定这个题目另有私心, 便是期待主办单位能借地利之便,借一组我死也不可 能供在家里的超级“发烧”音响,放放我那些听熟了 的唱片,让我好好过把瘾。
可惜事与愿违,那次讲演的音响器材,几乎是我 这些年走江湖所见规格最阳春的一组——连那到底算 不算“音响”都十分可疑——一只摆在地上的手提式 扩音喇叭,补习班常见的那种。那喇叭功率稍弱,音 量略略扭大,便会窜出哔哔剥剥的噪声和回授啸声。
我的CD透过那只喇叭播放出来,高中低频或许都还在 ,只是通通黏成一气,糊烂难解——总之,我得在全 台湾“发烧音响”最密集的展览现场,用一只补习班 扩音喇叭讲两小时的“摇滚发烧片”。
我只能急中生智,改变策略,反向切入:话说五 六十年代,我们的长辈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用晶体管 收音机和手提唱机听着那些古早的音乐,何尝在乎过 “发烧”与否?那些歌的创意和才气,即使用最最阳 春简陋的器材播放,仍足以撼动人心。
“大神级”资深制作人李寿全曾经跟我说:他制 作完一张唱片,在后制录音室完成混音和母带后期处 理,会先用录音室里专业级的监听喇叭仔细听一遍, 再把母带录成卡带,拿到楼下电器行找一台最便宜的 手提录放音机放一遍。若是这么听起来也不错,才算 过关。毕竟流行歌曲从不单单为了发烧音响而存在, 它将在计程车上、在便利商店、在面馆的电视机前被 听见。真正厉害的“发烧片”,得要做到“随遇而安 ”、“遇强则强”,才算得上“雅俗共赏”。
李老师的故事给了我灵感。那天我请大家把那只 补习班喇叭想象成“四十年前的晶体管短波收音机” ,果真奏效,听众并没有被它吓跑。
讲演结束,活动承办人上来作结,这位混“发烧 圈”多年的前辈阐述了一段“发烧友应有的观念”, 令我大开眼界。他说:发烧友常常花太多钱玩音响硬 件,却吝于投资软件。所以他们努力提倡一个观念: 器材成本与唱片收藏,应该至少保持“一比一”的比 例。也就是每花一万块钱买器材,就应当至少买一片 CD。
易言之,若你拥有一套百万音响,你起码应该要 有一百张CD。我暗暗换算了一下:若从架上的唱片数 量逆推,我应当要拥有一套价格相当于两三栋房子的 音响系统,才对得起这个公式。
然而我也很清楚,有太多年轻人的硬盘里塞满了 十百倍于我毕生搜购唱片总和的MP3文件,连续放上 几个月都听不完,然而他们往往连一副像样的耳机都 没有,听音乐最常用的接口是电脑喇叭和手机。他们 得之于音乐的快乐,是否质量必然不如遵行“一比一 ”公式的“发烧友”呢? 所谓聆听的教养,所谓“发烧”的真谛,我想了 很久,依旧没有答案。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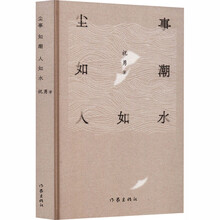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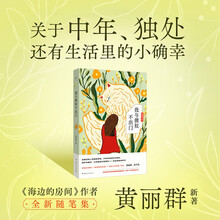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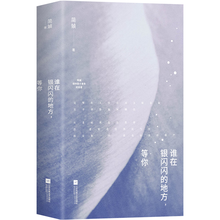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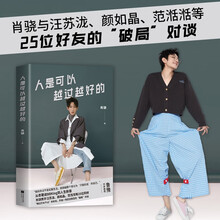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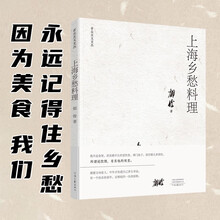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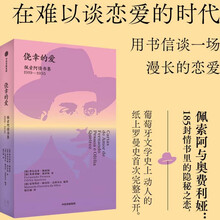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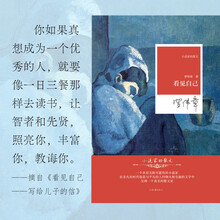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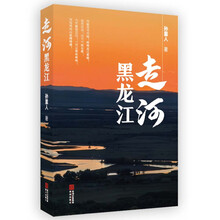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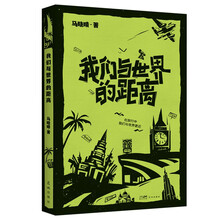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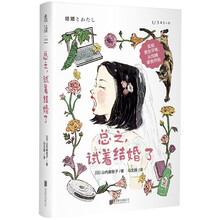
★这片岛屿刚刚历经七○年代的一连串颠簸,正摇摇晃晃迎向一波波更为激烈的大浪。许多人殷切等待足以描述、解释这一切的全新语言,于是一首歌也可以是启蒙的神谕,一张唱片也可以是一桩文化事件。一个音乐人不但可以是艺术家,更可以是革命家、思想家。
——马世芳
★马世芳这样用心的听者,让华语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与付出,有了价值和尊严。
——李宗盛
★关于过去四十年两岸三地的原创歌曲,很少人比世芳听得多,听得仔细。
把耳朵借给马世芳吧,听他放一首歌,认识写歌的人和那个年代的故事。
——侯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