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蒂玛在我快满七岁的那年夏天,住进了我们家。她来的时候,亚诺荒原的美丽正在我眼前展现,河流唱着潺潺的歌,伴随翻滚的大地的低吟。童年的神奇时光静止不动,大地鲜活的脉动让我感受到它的奥秘而血液沸腾。她握起我的手,而她拥有的安静神奇力量,将美丽赐予原始的太阳炙烤下的亚诺荒原、翠绿的河谷和白花花的太阳栖居的蓝色大碗。我赤裸的双脚感觉到大地的颤动,我的身体也因兴奋而颤抖。时间静止不动,与我分享这片土地的过去与即将来临的未来……
让我从头开始。我不是指在我许多梦里出现的开头和它们对我低语的,关于我的出生、父亲与母亲的家族,还有三个哥哥的故事,而是随着乌蒂玛而来的开头。
我们家的阁楼被隔成两间小房间。我的姐姐,黛柏拉跟德瑞莎睡在其中一间,而我睡在门旁的那个小隔间里。嘎吱作响的木头楼梯向下接到一条狭小的走廊,通往厨房。我可以从楼梯顶端的制高点看到我们家的心脏,我妈妈的厨房。从那里,我将看到查维兹带来警长被杀的恐怖消息时惊恐的脸;我将看到哥哥们对父亲的违抗;还有许多次在深夜时,我将看到乌蒂玛从亚诺荒原归来。她是去采摘只能在满月月光下由巫医小心翼翼的双手收获的药草。
那天晚上我非常安静地躺在自己床上,听到父亲跟母亲讲到乌蒂玛。
“她自己一个人,”父亲说,“而且草原村已经剩下没多少人了。”
他用西班牙语说,而他提到的村子是他的家乡。父亲做了一辈子的牛仔。这是个古老的行业,跟西班牙人来到新墨西哥州的年代一样久远。即使在开农场的人跟随得州人到来、在美丽的亚诺荒原围起栅栏后,他,还有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仍继续在这里工作,我猜是因为只有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和天空下,他们才能感受到灵魂需要的自由吧。
我听到母亲叹息,而她想到乌蒂玛独自生活在孤独的广阔亚诺荒原上,想必也微微颤抖吧。母亲不是亚诺的女人,她是农家的女儿。她看不出亚诺的美丽,也不了解半生都在马背上度过的粗野男人。我在草原村出生后,她说服了我父亲离开亚诺,带着她的家人来到瓜达卢佩城,她说我们在这里才会有机会,也才能受教育。这次迁徙降低了父亲在他伙伴——那些仍顽强抓着原本生活方式与自由的亚诺的牛仔们——心中的地位。城里没有空间畜养牲畜,所以父亲不得不卖掉他的一小群牲口,但是他不愿意卖掉他的马,所以他送给了一个好朋友,贝尼托?康柏斯。但是康柏斯无法将这动物关在围栏里,因为不知为何,这匹马的灵魂很贴近它原本的主人。于是它被允许自由驰骋,而全亚诺荒原没有一个牛仔会往这匹马的头上套项圈。就像有人过世了,他们便转开目光,不愿去看仍行走在世间的灵魂。
这损伤了父亲的自尊。他越来越少与老朋友来往。他去做铺设公路的工作,而到周六,拿到工资后,他就跟他的组员去长角酒吧喝酒,但是他从不曾与城里的人亲近过。有时候到了周末,亚诺的人会来城里买补给品,而像柏尼,或康柏斯,或巩萨雷斯兄弟,会过来家里坐坐。这时父亲就会眼睛发光,跟他们一起喝酒,谈着过去的时光,说着古老的故事。但是当西沉的太阳将云朵染上橘色跟金色,牛仔们坐进货车踏上归途时,便只剩下父亲一人在漫漫长夜中喝酒。礼拜天早上他起床时就会脾气暴躁,抱怨要去早上的弥撒。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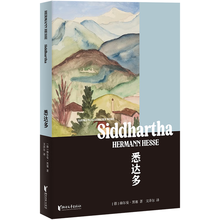









——《洛杉矶时报书评》
★安纳亚的第一部小说《河流,黑暗的灵》深入挖掘青春记忆中的丰富宝藏,可能是当代最知名也最受重视的墨西哥裔美国文化小说。
——《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