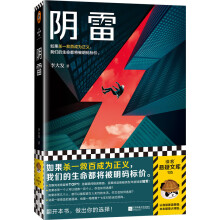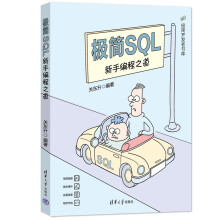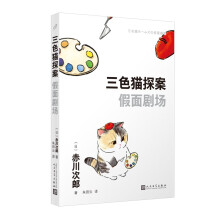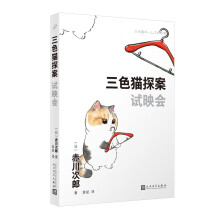走向诗学试论胡适白话诗的散文化倾向
众所周知,胡适是中国白话新诗的始作俑者,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他的新诗创作几乎都收在该集里。胡适的白话诗较之他以前的文言诗的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学者评价道:胡适“比他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突破旧诗藩篱,大胆创建新体。(2)破坏旧诗格律,探索新诗的音韵。(3)在探索中,重视了形象思维,创造性地运用了具体描写的艺术手法。(4)采用明白晓畅、接近口语的语言创作新诗。”祝宽:《中国现代诗歌史》,青海民族学院出版社,1982年,第277-284页。我认为这些评论都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这里,暂不谈胡适白话诗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试从诗自身的角度来量度《尝试集》,以探讨初期白话诗的散文化趋向及其成因。
1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一部诗集亦不例外。在《尝试集》出版已达80年的今天,如果用客观的纯诗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的白话新诗写得相当不错,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但更多的诗则平白质朴,缺乏浓厚的诗情诗意,带有明显的散文化特征。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诗的结构看,胡适白话诗缺乏跳跃性。诗作为文学创作中最早成熟的文体,它与散文的区别,曾多次被古今中外的诗论者指出。我国古人就把诗比为米酿的酒,把散文比为米煮的饭;西方人把诗比为用脚跳舞,把散文比为用腿走路。这一“酿”字、“跳”字,活化了诗鲜明的特质,表明了散文可以是平铺直叙的,而诗则必循着艺术思维的驰骋而跳跃。这种跳跃可以是时间上的古今沟通,也可以是空间上的东西跨越,还可以从主观的情感跳向客观的事物。并且从诗人的思维转换角度看,诗的跳跃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时间与空间、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互逆变幻,诗中思维跳跃的表达可以是关联的、发散的,也可以是对比的、平行的。但胡适的白话诗中时间、空间的转移并不是诗本身结构的跳跃。如《赠朱经农》中叙述现在、未来和过去:“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这在诗的结构上,是连续铺展的,而不是垂直增高的或平行跳跃的。试比较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中有关时间变幻的句子:“——躺在时间的河流上/苦难的浪涛/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流浪与监禁/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最可贵的日子”。同样写自己的经历,前者是散文的写法,后者是诗的写法。
其二,从言语表达看,《尝试集》中的诗缺少凝炼性。诗是用最简洁的言语表达最丰富的情感的文体,前苏联诗人维诺库罗夫说:“诗人——这是指善于把多得不能再多的东西,也可以说,把整个自己都放进一个形容词,一行诗里去的人。他能把如此之多的内心激情和力量放进一道短小的抒情诗里,假若让一个散文家去写的话,势必写成整整一本小说。”转引自张孝评:《中国当代诗学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1页。诗要求精选最恰当的语词来形容最深刻的情感体验。绝大多数的诗人都运用象征、比喻、典故、省略等手段来尽量达到诗的这一要求,因为这些手法最符合诗的构成原则,胡适的白话诗却几乎不用这些诗法。胡适之所以摒弃这些诗法,与他的文学革命理论不无关系,他提倡的“八不主义”《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60页。就对我国古典诗歌的一些优良传统如对仗、用典等予以否定。否定它们,就等于放弃了精粹隽永而言近旨远的诗语。而且他的白话诗大都不用形容词,更不用象征,却采用散文的叙述言语。这样,只能写出具有诗的外在形式(分行、押韵)而不具诗美的韵文。
其三,从诗对音乐美的强调看,胡适颇注重押韵,这从他《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可见一斑。但从押韵、停顿而形成的节奏的作用看,他追求的节奏很少能促进诗的情感的抒发和意境的创造。胡适较满意《尝试集》中押韵的诗句有:“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我望遍天边,寻不见一点半点光明/回转头来/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这些诗句都是“胡适之体”。《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新诗,多写情感体验的过程,而没有真正表现他的情感状况。因此,在诗的外围徘徊,而未登堂入室,即使再三斟酌韵律,也不可能成为驾驭诗的情感的主体,这样的诗,自然少了音乐美。还有,胡适白话诗中有关景物的描写也缺乏情感的浸透,形成景是景,人是人,没能逾越情与景之间的沟壑。因而,《尝试集》中的诗缺少情景交融的意境,更没有虚实相生的意境;缺少诗的韵味,便增多了散文的意味。
2
胡适白话诗以上这些缺少诗意诗味的特性,使得他的新诗明显地具有了散文化倾向。不论从创作主体角度,还是从创作方法角度,我们都不难找到胡适白话诗散文化的原因。
其一,理性思维大于形象思维。诗的本性在于美。诗是创作主体的强烈情感冲动的产物。这就要求诗人首先具有丰富充沛的情感储备,然后在触发主体情感爆发的客观对应物的刺激下,诗才能得以产生。而作为学者的胡适,其思维整体结构中的理性思维压抑了情感思维即形象思维。他在美国留学时,接受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这一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胡适养成了精密的理性思维,对任何事物都要进行周密的思考和详切的条分缕析。这并不是说胡适没有情感思维,或诗性感情,但当理性思维的发展强大到超过情感思维时,必然导致情感思维呈现压抑乃至萎缩的状态。在这样强烈的求证思维模式的操纵下,为了从实践上证明其白话可以入诗的理论观点,胡适也就为作诗而作诗了。也就是说,胡适的诗是理性的产品,而非感情的流泻。这势必诗情不浓,诗味寡淡。正如闻一多当时所指出的:早期白话诗的感情大多“是用理智底方法强迫的,所以是第二流的情感”。《闻一多全集》(2),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9页。这一痛切的针砭,自然包括胡适的白话诗在内。再从创作的角度看,《尝试集》中诗缺乏“动情”的环节。我国古代诗论就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讲的“情”,我认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指诗人充沛的情感,因为主体的情感是诗产生的首要条件;第二层是指诗人在主体之外找到了情感对应物,即诗人将情感附诸客观形象。而这一过程是凭借形象思维来完成的。胡适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形象思维,其结果是情感与情感对应物之间的剥离。艾青也说过,“散文化的诗的最大特征,是创作过程中排除了形象思维”。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5页。
其二,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胡适在《谈新诗》一文中说:“诗须要用具体的作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凡是好诗,都是具体的;越偏向具体的,越有诗意诗味。凡是好诗,都能使我们从脑子里发生一种或许多种明显逼人的影像。这便是诗的具体性。”《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他在新诗中确实实践了“用具体的写法”写诗,想达到“以引起鲜明扑人的影像”的目的。胡适这里所说的“影像”,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意象”。但是在实际上,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常常失衡,这就造成意象(影像)难以实现的矛盾。例如《蝴蝶》一诗: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的具体写法过于平实,很少甚至缺乏使读者引起视觉、听觉或全身心感受的意象。这就造成胡适白话诗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之间不小的距离。他的理论是从古人作诗的成败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但他在作诗中却不知道诗的意象的最终目的在于:诗的语言功能的发挥及其言外之意的生发。诗之所以为诗,被称为文学中的文学或最高的语言艺术,其原因就在于此。言外之意是由具体灵动的语言生发出来,而意象一旦形成,则反过来挣脱具体语言的束缚,以进入自由想象的境界。诗人说出来的尽可能地少,读者间接想到的就尽可能地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反比例的关系。古诗论上所谓言少意足、言有尽而意无穷,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以少胜多”正是一切艺术的通则;而诗艺,对它的要求更高一些。但胡适所倡导的意象与他新诗中缺乏言外之意的矛盾,正是早期白话诗“断奶”现象的表现。文言能创造的意象,白话肯定也能创造,这一点胡适坚信不疑。只是初用白话,其语言的功能还不可能一下子就发挥得很好。这正是胡适与朋友们论争的焦点——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辩。胡适之所以遭遇“孤单怪可怜”的尴尬境地,正是由于他的白话诗重在白话,而不重诗,这就死死地捆绑住了他作为诗人的翅膀。
其三,用作文的方法去作诗。胡适曾经强调“要须作诗如作文”。从艺术手法的角度看,胡适写作新诗实际上更多地运用了小说的描写、叙述的方法。在《尝试集·自序》中,胡适“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认为“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胡适:《尝试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让自然的生活不加选择地入诗,让自然的生活内容不加诗化地表现在诗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的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的文学可能性”。胡适:《尝试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这样,对不经情感过滤的客观事物,用诗、文通用的文字,借助小说的白描手法作出来的诗,其结果更像散文,而不像诗。如《江上》: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作者叙述夏日阵雨的来去过程,是用小说的描写、叙述方法,是再现对象的审美特征,而不是表现诗人主体的审美意识。这是小说写作中常用的回避情感的客观化的铺写。在这里,胡适的诗笔拘于外在的表象的真实,缺乏情感的渗透与激发,缺乏画面的灵动感,更没有必要的艺术张力与审美情韵。其不足以动人,是不消说的。再如《鸽子》:“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这首诗平实明白,摄下了瞬间美丽的画面,但毕竟拘泥于具象,滞留于事实,缺乏对生活内容的净化和升华,平直叙述和随意白描,造成了意随言尽、没有隽永余味的单薄与浅近的后果。现代著名诗人艾青曾经依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凭想象可以写出好诗?为什么根据事实反而写不出好诗来?我认为,据实叙述,只能是散文式的写实;发挥想象,则必然会有诗意的升华。艾青的成功与失败,不恰恰从正负两面说明了诗与散文的区别吗?正因为胡适的新诗创作过于注重写实的叙述和白描,遂导致了他对于艺术想象的放逐;而放逐了艺术想象,则无异于驱逐了诗的精灵,如此一来,怎能产生深邃、开阔、丰腴的诗境呢?
综上所述,胡适白话诗的散文化,是早期新诗的重要现象,又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等前期诗人在新诗发展道路上所起的开创和铺垫作用,才使得现代新诗创作在此后一步步皈依缪斯的怀抱。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