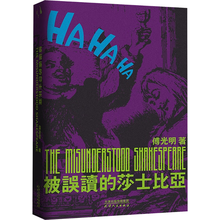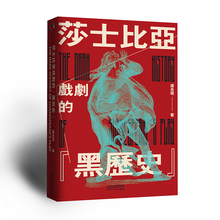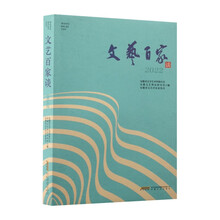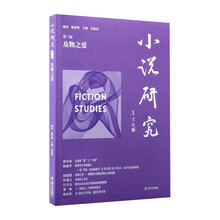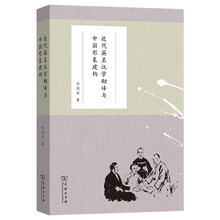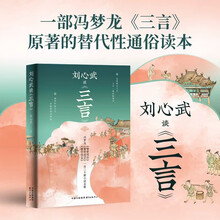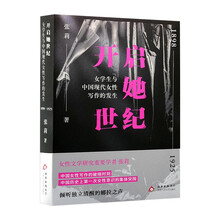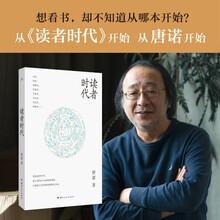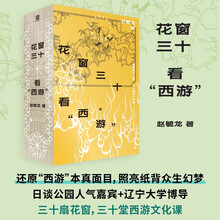《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
因此,文学批评和历史叙述的这种回归意识,或许同样存在于对历史情境和文化结构的各种“对话”意识和阐释观念之中,但是其根本目的更多的是对历史叙述和文化生产的各种“厚描”经验和建构实践。这种关注历史观念和文化经验的所谓“祛魅”工作,目的就是要在传统宏大叙述的各种时空断层来回溯和阐释历史情境和文化精神,从逸闻轶事的历史形式转向对历史诗意和主体意识的各种个体叙事的厚度描写实践。借用格氏本人的话来说,文化诗学的历史批评“应该探讨各种集体性的信仰和经验如何得到塑型,如何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外一种,如何集中到可以掌控的美学形式提供给消费过程。我们可以考察如何区分艺术形式和其他同类言说方式之间的各种文化实践;我们探讨清楚这些特别划定的区域如何可以赋予快感、激发兴趣或者产生焦虑的能力;这种观念不是要排除和摒弃美学自主性的魅力印象,而是要拷问这种魅力的各种形成条件,以及探索这些社会流动的多种踪迹如何被消除”总而言之,对于宏大叙述的经典正史也好,对于逸闻轶事的江湖野史也罢,文化诗学的这种历史诗性观念,不仅直接呈现为面向历史语境和文化传播的多元时空结构,而且明显蕴含着关注主体塑型和阐释经验的多样诗性意识。
3.3 文化诗学的文化诗性观念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英美学界的全面崛起有效地促进了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历史转向,然而这种情境主义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以历史语境和文化结构为关注对象的诗学空间。文化诗学的理论观念,显然是在文化与诗学两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对话和彼此渗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