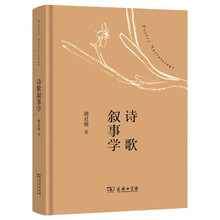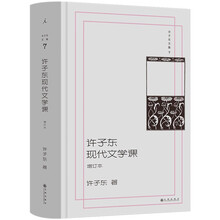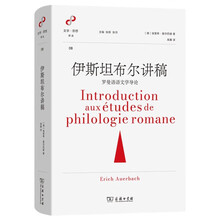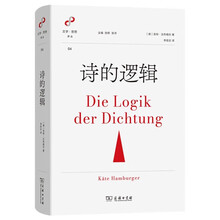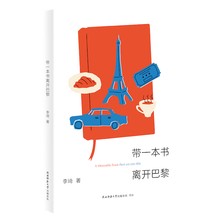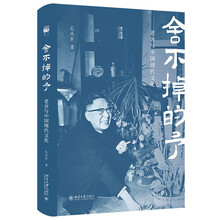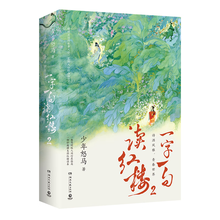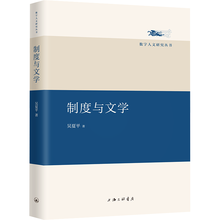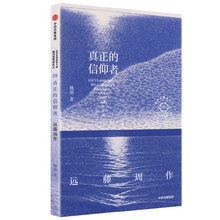《解放区前期诗歌研究(1936-1942)》:
对文艺社会功能的过分强调,不自觉地培养了延安作家的“革命”意识。所以,所谓“自由”,不是讨论与创作的无限制、无禁区,而是在文艺服务于“抗战建国”的根本原则之下的自由讨论与创作。因此,《讲话》之前延安的文学理论争论很多,而有深度、有建设性价值的理论成果则不多。
文艺家的各种不同的学术理念和不同的创作风格,都有其共同的出发点:即文艺如何更好地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服务。所以,延安文学的丰富与复杂,也是在这一个共同前提和根本原则之下的丰富和复杂。文学上“民族形式”的讨论即是在此前提下进行的,其对民族性的诉求和对未来新中国新文学的建构意识就是不言而喻的。
可以说,“民族形式”问题包含了两个相关性的话题: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文学的现实功利性与艺术性关系。
在延安对“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萧三等人因为重视文学抗战宣传的“当下效应”而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民间文化与旧形式,而何其芳等人因为更富有面向新中国文学未来的心态,而属意于以五四文学为基础的新文学,并试图建构一种兼有民族性与现代形态的文学形式。
延安时期的作家心怀未来新中国的乌托邦理想,在新文化的建构上显示了极大的创造性意识,但其所参照的理论资深却排除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一脉,而专心于在中国民间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武库中寻求其理论生长点。
这一种向“后”向“下”而不是向“前”向“上”的参照意识,与抗战的现实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西方先进国家给这个民族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羞辱和侵略,取法于西方的五四新文学无法为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欣赏;抗战的宣传需要文艺进行社会动员工作,要求文艺成为大多数民众的精神食粮。所以,民族自强的意志与大众的欣赏水平,限制了新文化建构中对参照资源的选取。在如何建立新诗的“民族形式”问题上,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对这两个资源的不同认识而展开的。这两个资源恰好代表了“民族形式”论争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即“民族性”与“现代性”——民间文化与旧形式显示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根基,五四新文化显示了文学的现代性方向。
而就抗战时期延安具体的政治而言,“民族形式”的讨论也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紧紧地抓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砝码,也是出于抗战大局的需要。联合蒋介石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大业,是全国的民意所在和人心所趋。
1938年10月,日本先后占领武汉和广州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速战速决的侵华战略政策宣布破产。国内资源的有限和战线过长等原因,促使日本政府想迅速结束战争。所以,在侵略政策上也有所调整:他们改变了以往单纯的军事进攻原则,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辅之以军事进攻。蒋介石也因此在抗日这件事上处于动摇状态:“即动摇于亲英反共降日与亲苏联共抗日之间。”
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发起了抗战以后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围攻八路军和进攻我敌后根据地的方式撕毁了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日本为了加强蒋介石降日的决心,不仅大力扫荡八路军,同时大举进攻陕北地区。②日本与蒋介石的和谈条件中有一条就是消灭共产党。这些情况,促使共产党更加努力于抗日动员工作。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就是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因此,1939-1941年延安的“民族形式”讨论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恰好形成了某种同构关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