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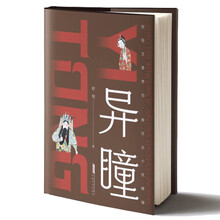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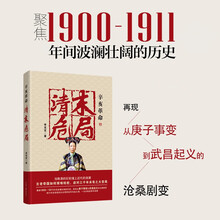
1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明明是无雨的天色,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由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棚屋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蒙蒙。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棚屋,透着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能看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理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闪过,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照射着,如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汽笛声,列车迎面驶来。火车司机对助理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迎面驶来,从开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旁边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理打了个手势,示意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绝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好像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一样。”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老头儿有些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就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聊天、争论、唱歌。
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牢房里,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命运,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按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类的犯人:红布条的是政治犯,黑布条的是怠工者,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撬门贼。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让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嗒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橘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觉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热衷于吹牛。
他们吹牛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在战前,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同朋友谈话时批评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说了一个带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战争期间,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关押战俘,也是法西斯当局的一项新措施。这里关押着在德国领土上被击落的英国和美国飞行员,以及盖世太保感兴趣的苏联红军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法西斯分子要求他们提供情报,同他们合作,提供咨询,逼迫他们在各式各样的声明上签字。
这座集中营还关押着一些怠工者。这些人故意旷工,企图擅自放弃在军事工厂和军事工地的工作。把不好好工作的工人关进集中营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新发明。
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一些衣服上缝着淡紫色布条的人,他们是从法西斯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这也是法西斯当局采取的一项新措施。离开德国的人,不管他在国外表现得如何忠诚,自然也成了政治敌人。
那些衣服上缝着绿布条的人,即小偷和撬门贼,在这座政治犯集中营里享受着特殊优待。警备队依靠他们监视政治犯。利用刑事犯来控制政治犯,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发明。
这座集中营里还有一些犯人由于命运与众不同,以至于当局设计不出与他们的身份相符的布条颜色。他们中有一个耍蛇的印度人,一个从德黑兰来的研究德国绘画的波斯人,一个学物理的中国大学生。然而国家社会主义在集中营的简易床上为他们留好了位置,为他们准备了盛菜汤的饭盒,每天让他们在工地上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军用列车昼夜不停地开往死亡集中营。
空气中充斥着车轮的轰隆声、机车的咆哮声和数十万衣服上缝着五位数蓝色号码的囚犯们上工时的脚步声。这些集中营成了新欧洲的城市。它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它们有自己的设计方案,有自己的街巷、广场和医院,有自己的集市、旧货市场、火葬场和体育场。
与这些集中营相比,与焚尸炉上方令人触目惊心的深红色反光相比,那些局促地坐落在城郊的古老监狱显得多么幼稚,甚至带点温和而淳朴的味道。
表面看来,管理这样一大批囚犯似乎需要一支上百万人的庞大监视者大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穿党卫军制服的人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在囚犯的牢房里露一次面。在这些集中营里,囚犯们自己担负着警察和警卫职责。
他们自己维护集中营里的内部秩序,自己监视自己的厨房,他们只能吃霉烂的冻土豆,而把那些又大又好的土豆挑选出来,送到军队的食品供应站去。
囚犯们担任集中营医院和实验室的医生和细菌学家,担任清扫集中营人行道的清洁工,他们还担任向集中营供电、供暖和供应汽车零件的工程师。
集中营警察严厉而凶残,十分猖獗。警察左胳膊上系着宽宽的黄色袖标,此外,集中营的区段和班组还设有各自的头目。他们自上而下地把集中营的生活控制得严严实实,从整个集中营的动态到夜间囚犯们在床上的举动,全都处在他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一些囚犯可以参与这座庞大集中营的秘密事务,甚至可以参与制订培育良种人员名单,可以参与审理被关押在暗室——混凝土禁闭室里的正在受审的囚犯的案件。看来,假如长官走开,囚犯们并不会中断铁丝网中的高压电流,不会四处逃散,而是会继续干活。
这些巡警和区段警为警备队长效劳,但却时常叹息,有时甚至为那些被送往焚尸炉的人流泪……不过这种二重性是无法坚持到底的,他们从不把自己的名字列入良种人员名单。在莫斯托夫斯科伊看来,最令人不安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并没有以那种戴着单眼镜装腔作势、傲气十足、与人民格格不入的面目来到集中营。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集中营里,他们没有脱离普通人民,他们用人民的方式开玩笑,他们的玩笑也逗得人们哈哈大笑。他们就是平民百姓,他们举止随便、平易近人。对于那些失去自由的人的语言、心态和智慧,他们再熟悉不过。
3
八月的一天夜里,莫斯托夫斯科伊在斯大林格勒城郊被德国人俘虏。同时被俘的有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女军医莱温托恩和司机谢苗诺夫。他们被俘后立即被送往德军步兵师司令部。
阿格里平娜·彼得罗夫娜在审讯之后获释。根据战地宪兵队一名工作人员的指示,翻译发给她一个豌豆面大面包和两张红色的30卢布钞票。谢苗诺夫被编入俘虏行列送往韦尔佳契村地区的非军人集中营。莫斯托夫斯科伊和索菲娅·奥西波夫娜·莱温托恩被送往德军集团军群司令部。
在那里,莫斯托夫斯科伊最后一次见到索菲娅·奥西波夫娜。当时她站在落满尘土的院子中央,没有戴军帽,领章被揪掉了,她那阴郁而凶狠的眼神和表情令莫斯托夫斯科伊大为赞叹。
第三次审讯之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徒步押往火车站。一列运载粮食的军用列车正在装货,拨出十节车厢运送被迫去德国做工的男女青年。军用列车开动时,莫斯托夫斯科伊听见女人的喊叫声。他被关在一节硬席车厢的狭小的公务包厢里,押解他的一名士兵待人并不粗暴。但是当莫斯托夫斯科伊向他提问时,他脸上却露出聋哑人的表情。这时莫斯托夫斯科伊才意识到,士兵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他就像动物园里有经验的职员,经常全神贯注地默默监视着乘火车外出旅行的野兽在箱子里的动静。列车驶经波兰领土时,包厢里出现一个新乘客——一个波兰主教,他头发花白,高个子,很漂亮,有一双悲剧演员的眼睛和年轻人的丰满嘴唇。他立刻向莫斯托夫斯科伊谈起希特勒对波兰宗教界的镇压。他的俄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莫斯托夫斯科伊严厉批评了天主教和教皇之后,他便沉默起来,对莫斯托夫斯科伊提出的问题,他用波兰语做了简短的回答。几个小时之后,他在波兹南下了车。
途经柏林,然后莫斯托夫斯科伊被送进这座集中营……他仿佛已在这个管辖区里生活多年,这里关押着盖世太保特别感兴趣的囚犯。这个管辖区里的生活比劳改营里好一些,但这是类似供实验用的动物的轻松生活。有时值班员把一个犯人叫到门口,原来是一个朋友要以优惠价拿一份烟叶换一份口粮,那犯人微笑着满意地走回自己的床铺。有时他们又叫了另一个犯人。犯人中止谈话,向门口走去,同他谈话的人再没有听到他说完自己的话。一天后,一个警察走到床前,吩咐值班员把那个犯人的破烂东西收拾好。这时有人讨好地问棚屋的头目凯泽:能否占用这张空床?在这里,各种谈话奇怪地混在一起,人们已习以为常。囚犯们谈论选择良种,焚化尸体,集中营的足球队:最好的是“沼泽地上的士兵队”,“管辖区队”阵容强大,“厨房队”前锋勇猛,波兰“普拉采菲克斯队”没有后卫。在这里,经常流传着几十种甚至几百种关于新式武器、纳粹头目发生内讧的传闻。这些传闻美好而虚假,是集中营囚犯们的精神鸦片。
天快亮的时候下了一场雪,地上的雪一直到中午才开始融化。此时,俄国囚犯们悲喜交集。这是来自俄罗斯的气息,这雪就像祖国母亲把洁白的头巾抛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集中营棚屋的屋顶一片银白,从远处望去,仿佛家乡的村舍。
然而,转瞬即逝的喜悦夹带着忧伤,最终被忧伤淹没。
……
译者序 / 严永兴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罗伯特·钱德勒(Robert Chandler,俄语文学翻译家)
《生存与命运》遮蔽了当今西方世界几乎所有能被认真对待的小说。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人文主义文学评论大师)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存与命运》让人压抑沉重,它无所畏惧,真实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果,以及我们在厄难中所能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一部文学的杰作,一部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写出的著作!
——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美国学者》资深编辑)
瓦西里·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无论它是随性而为的,是平淡无奇的,还是英勇坚决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泯灭。
——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英国作家)
对于不仅已从我们所经历的恐惧里走出,并且也已从我们关于那恐惧的记忆中走出的今天与明天的广大读者来说,《生存与命运》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格罗斯曼留下了一部将为人类长久记忆的书。
——列夫·安宁斯基(Lev Anninsky,俄罗斯文学评论家)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小说将长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并不只是因为它鸿篇巨制的体量,它对极权体制的深刻沉思,它对战争令人赞叹不已的叙述;更因为,这是一部让我哭泣的小说。在蒙彼利埃机场,我读它,不是只落下几滴眼泪,而是长久的失声痛哭……在集中营,格罗斯曼失去了他的母亲。在《生存与命运》中,他笔墨温存而痛楚,这是只有在极权体制下幸免于难的人才有的人生经历。确实是经典之作。
——吉莉安·斯洛沃(Gillian Slovo,英国作家、英国笔会主席)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存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
——梁文道(知名作家、媒体人)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20世纪伟大的文学杰作。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世纪优秀的俄语小说之一。
——《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
格罗斯曼对苏联生活的叙述是百科全书式的,洞若观火……令人赞叹不已。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格罗斯曼是一致公认的20世纪杰出的作家之一,《生存与命运》是历史长河为人类留下的宝贵遗产。
——《卫报》(Guardian)
阅读这本书,并为20世纪诞生了一位思想深邃高远的文学人文主义者而欣喜。在当代文学中,这些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的探寻,是对人类心灵令人不安却又令人振奋不已的拷问与反思。
——《华盛顿邮报·书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生存与命运》是一部勇气而智慧的著作,笔墨有着契诃夫式的质朴精妙。
——《展望杂志》(Prospect Magazine)
《生存与命运》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罕有其匹……不得不承认,《生存与命运》中的格罗斯曼是苏联的个自由之声。
——《评论杂志》(Commentary)
人性,就像历史,是无法给出确切结论的。人既能作恶,亦能为善……格罗斯曼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试图探求苏联社会的历史结构和未来可能。
——《国家》(The Nation)
围绕斯大林格勒战役展开的鸿篇巨制,以托尔斯泰式的格局,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且深入到了人类社会“腹地中的腹地”——集中营和古拉格……正如格罗斯曼坚信的,只要善还存在,人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费加罗报》(Le Fig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