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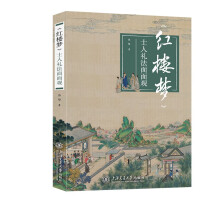
对于民主的描述往往是很深沉的文字,仿佛没有劫难没有涅槃就没有民主。《民主的进程:影响美国法律的十宗最》却通过另外一种趣味的方式——排行榜——写尽美国法律的尊荣与诟病。那些曾占据美国法律制高点的联邦**法院大法官,用个人的智慧推动美国的民主进程;扭转历史的十大判决在法律合宪性、公共利益及军事权力与平民权利等方面改变了美国式民主;还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庸才,在其位却迟滞着美国法律的进步……历数美国法治的光荣与梦想,揭开*不为人知的司法记忆,美国民主的进程跃然纸上。
了解美国最高法院是读懂美国民主发展进程的重要部分,《民主的进程:影响美国法律的"十宗最"》中开立了数个有关最高法院的榜单,以便“远近高低各不同”地领略“庐山真面目”:十位最伟大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十位最糟糕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历史上十个最佳判决;最高法院最受诟病的十个判决;十佳联邦最高法院异议意见;联邦最高法院史上十大逆转六个榜单。此外还可以读到联邦最高法院以外的伟大法官、最高法院之外的十项最伟大判决和最受诟病的十个判决三个榜单,作者除了围绕美国司法系统进行重点阐述外,还尽可能全方位展现美国法律史的内涵理路:塑造美国法的十部法律书籍;最伟大的十位律师;最重要的十场审判;最具影响力的十部法律电影排行榜。针对每个榜单,作者附以精妙绝伦的点评,而这种点评也不是普通的介绍性文字,视野之广阔与深邃,无论是普通爱好者,抑或法学专业研究者,读罢皆会有所得,整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发展内在逻辑跃然纸上。
第一部分
谁曾占据美国法律的制高点?
——十位最伟大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十位最伟大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1.约翰·马歇尔(1755~1835)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801~1835
2.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02~1932
3.厄尔·沃伦(1891~1974)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53~1969
4.约瑟夫·斯托里(1779~1845)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811~1845
5.小威廉·布伦南(1906~)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56~1990
6.路易斯·登比茨·布兰代斯(1856~1941)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16~1939
7.查理斯·埃文斯·休斯(1862~1948)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10~1916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930~1941
8.雨果·拉斐特·布莱克(1886~1971)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937~1971
9.史蒂芬·J.菲尔德(1816~1899)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1863~1897
10.罗杰·布鲁克·坦尼(1777~1864)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1836~1864
小引
谁能登上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伟大法官的宝座?他们又凭借什么在法律世界的制高点占据一席之地?
老实讲,这世上所有的排名都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都会或多或少受排名人自己主观价值的影响。毕竟,正如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大法官所说:“尚且没有这样一个公认的标尺,来评判一个人在法律世界的地位,甚至,连评判时需要衡量的各方要素都不能明确。”所以,法律不像棒球,在棒球的世界,至少还有一个平均击球数来确定泰·科布(Ty Cob)们或特德·威廉斯(Ted williamses)[ Ty Cob和Ted Williamses两人都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著名运动员。——译者注
]们遥遥领先的地位,而在法律界,我们甚至没有一个完全“客观的”标准来比较大法官们的优劣。
或许,我们能套用一下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关于色情出版物的精妙断语:“是的,我可能永远无法准确定义何谓色情出版物。但只要我看过之后自然就会成竹在胸。”同样,恐怕谁也无法给“伟大的大法官”一个确切定义,但是,我们读罢此书,自然能判断他们是否当得起“伟大”的名号。
以下即是依我的判断所列出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十位大法官,并陈述他们获此殊荣的理由。另外有些大法官登上了我总结的其他一些最佳名单,遗憾的是我却没能将他们纳入本人的“十佳”之列,其具体原因我也会一一道来。本章结尾,我会为我的名单作一个总结,阐明是哪些因素决定了某位法官能否登入这座先贤祠。
1.约翰·马歇尔
在所有美国最高法院最伟大法官的列举中,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1755~1835)的榜首地位都无可动摇。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是如此描述他的:“如果选出一个人来代表美国法律,无论是他的忠实拥趸,还是怀疑者,恐怕都不会质疑约翰·马歇尔的当选。惟此一人,别无他选。”而且,这位首席大法官在文献中被提及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任何大法官。他不仅是宪法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其撰写者和创造者。美国总统詹姆斯·A.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曾说过“马歇尔不仅造就了宪法的文本,也赋予了宪法的权威;他不仅搭建了宪政的框架,而且还给了其血肉和灵魂。”
对马歇尔而言,宪法实施切忌形式主义,而应根据建国先贤们的首要初衷来实行,即建立一个政府享有必要权力的国家。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三个判决保证了联邦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力:“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 v. Madison,1803),确定了宪法至上和司法权对法律合宪性的审查权;“麦卡洛克诉马里兰州案”(McCulloch v. Maryland,1819),确定了联邦权力并不限制于宪法的列举范围;“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1824),为联邦管理商业的权力作出了宽泛解释。
我们可以从他的一句影响深远的法律意见中领略到马歇尔法哲学观念的关键所在:“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我们所解读的是一部宪法。”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如此评价马歇尔的这句话:“这是有关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一句话。”马歇尔的这句名言奠定了宪法解释的基调,用法兰克福特的话来说,宪法就是应该被解读为“一个小型的保险条款,面向难以预测不可限量的未来而仅对政府的框架作出规定”。
马歇尔认定宪法应当为国家和政府的高效运行奠定法律基础。与同时代其他法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歇尔视法律为获致他所偏好的政治和经济境界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美国法形成发展的时代,马歇尔无疑是奉行结果导向原则的法官典范。
毫无疑问,马歇尔是最伟大的法律推理者之一。其永远的第一原则是:一旦接受了某一观点,则可经严密逻辑之推演,最终指向其所偏好的结论。正如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所说:“观察那些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会发现这个过程相当缜密客观而不带个人的想法。令人感喟那确是不加感情因素的必然性的过程。”
这种假象甚至迷惑了马歇尔最强大的攻击者们。一位批评者气急败坏地评论道:“错了,彻头彻尾都是错的,但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为什么错了或者错在哪儿。”同时代的作家如斯说:“马歇尔即是用逻辑原理统御世界者。”马歇尔的司法观点反映出他逻辑家的本质,在那个三段论大行其道的年代,他用宏大的笔触建立了一个如此完备的逻辑体系使同时代的批评家都哑口无言。然而,对于马歇尔来说,逻辑或者法律,都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确实,这位首席大法官的司法观点可说是霍姆斯那句著名格言的绝佳写照:“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比之其他任何法官,马歇尔更善于依照霍姆斯所谓的“时代的需求”来锻造他的法律裁判。与宪法一样,法律是一个整体,是马歇尔的工具;公法也好,私法也罢,都可以被马歇尔用来浇铸至未来国家主义新国度政治和经济的理论基础之中。
与托马斯·杰斐逊相比,虽然马歇尔的愿景算是相对保守的,但是他们对美国政体却有着不同的见解。马歇尔入木三分地概括杰斐逊式的作风具有一种横扫一切的架势。在1815年的一封信中,马歇尔如此写道:“世人公认民主是政治智慧的最完美杰作而平等则是民主制度运转的支点。”随着年龄的增长,马歇尔愈加认同平等价值并为其传播而斗争,其中最著名的成就当属1829年和1830年的《维吉尼亚公约》(Virginia Convention)。在同一封信中,他写道:“平等者,要求人在物有富余之时,能分与其急需之同胞。”
不过,如果说马歇尔反对杰斐逊式和杰克逊式民主的斗争注定要失败的话,那么他那更具广泛意义的抗争——对自己法律理念的维护,则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即使是对美国法律只有粗浅认识的人也知道,马歇尔的宪法理念曾经主导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法理观。另外,马歇尔的法庭判决使普通法与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开辟了在实业前景之下的私法重塑之路。个人的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成为了法律的最终目的,恰如其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一样。法律成为征服这片新大陆的首要工具,也成为经济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首要手段。本段的总结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马歇尔可能曾经是杰斐逊或杰克逊式民主的反对者,但同时,他的法律观念为法律制度奠定了宪政的基石,从而以此在社会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平等。
2.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
历史上最高法院所有联席大法官当中,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前面谈论马歇尔的时候,我已经引用过了霍姆斯的一句话,“如果选出一个人来代表美国法律,那么此人只能是约翰·马歇尔。”其实,如果要选出代表美国法律的二号人物的话,大多数人会同意霍姆斯获此殊荣,因为正是他订立了现代法学的诸项议程。霍姆斯不仅在法律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同时他本身也成为了一个传奇:在他的时代和他之后的岁月里,这位“来自奥林匹亚的北方佬”[ 即Yankee from Olympus,一部在美国长久畅销的关于霍姆斯的传记,作者Catherine Drinker Bowen。同名电影入选本书“十部最伟大的法律电影”名单。——译者注
],这位波士顿的贵族,产生的影响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毫不夸张地讲,二十世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运用的理论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得自霍姆斯的真传。
霍姆斯在宪法领域内的两个伟大贡献是司法克制理论和广义的言论自由观点。司法克制理论是霍姆斯的核心法律理念之一。霍姆斯一再强调,作为一个大法官,他并不关注那些受质疑的立法议案的明智与否,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解决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法案,需要人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决定,而非由法官来越俎代庖。
然而,在处理言论自由相关案件的时候,霍姆斯表达出的法律理念却与其“司法克制”理念相矛盾。一战之后,霍姆斯创立了“清晰且现实的危险”的判定标准;在这个概念下,除非某些言论真的具有某种威胁性,即存在着清晰的且现实的危险——该言论将导致立法机关有权防止的罪恶时,言论自由才能受到限制。
其实,霍姆斯的贡献,远不止这些法律理念。如同我前面所说,在引领美国司法走向全新时代的道路上,霍姆斯较之其他同仁贡献最巨。霍姆斯认为,制定法律时,应当有意地使其服务于那些最有利于社会的政策。本质上来讲,霍姆斯认为,法律应当主动适应社会的需求,而不能是以往教条的逻辑演绎。霍姆斯的司法体系中,法律是实用的工具,是使社会需求得到满足的工具。
霍姆斯早已经为法律思维设想了未来的道路,早在他的著作《普通法》(The Common Law,1881)一书中,霍姆斯就已声明:“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吹响了二十世纪法学前进的号角。如果法律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求”的话,那么,法律就应当由这些需求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理论教条决定。然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大多数法官和律师并不遵行这一观点,甚至在霍姆斯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职务期间,其同僚中的多数也不认同。值得庆幸的是,霍姆斯的理论在其离世之后,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如果说,形式主义的法学理论统治了十九世纪的法律界,那么二十世纪最终成为了大法官霍姆斯的时代。
3.厄尔·沃伦
厄尔·沃伦,(Earl Warren,1891
~1974)担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期间,正是美国法律史上法律性格形成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法律也同样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正是沃伦在此一时期社会进化的背景下领导了重构美国法的运动。谈到对美国法律的创新性深刻影响,只有约翰·马歇尔任期能够与沃伦时代相匹敌。
沃伦凭借其出色的领导才能和娴熟的政治家技巧,成为马歇尔之后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与沃伦共事的其他大法官们无不对其出色的领导能力赞赏有加,特别是他主持案件讨论会时井井有条的风度教人记忆犹新。正如《华盛顿邮报》当时描写的:“沃伦从会议一开始就能依照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来驾驭案件要点的讨论。”
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1954)的第一次案情探讨会上,沃伦提出了与种族劣等观念相关的问题。他告诉大法官们,只有从黑人心中彻底清除种族劣等的阴影,才能解决种族隔离问题;因为种族隔离之所以能够维持,正是有这类种族劣等观念做基础。深沉如法兰克福特大法官这样的学者,绝对不会如此表述问题,但沃伦就是如此直接,他直奔人的价值这一终极性的讨论。在沃伦这种路径面前,法律界的那些雕虫小技无论怎么看都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每个法律体系都内含一对矛盾冲突:法律必须保持稳定性,但又不能僵化。而平衡这两者的任务,就落到了法官肩上。首席大法官沃伦坚定地主张法律当变,他致力于变革法律以使其适应社会变化。沃伦反对司法克制,因为他认为,司法克制阻挠了最高法院充分发挥其宪政作用。
在沃伦看来,法院的功能是保障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其他政府分支未能做到的时候。如果由于政府失职而导致宪法无法实施,那法院必须对此有所作为;否则的话,宪法就是连根本条款都得不到执行的一纸空文。“布朗案”中有关废除种族隔离的决定,就是行政过程无力保障种族平等而引发的一个直接后果。在“布朗案”之前,政府的失职已经使得宪法中关于保障非洲裔美国公民平等的条文变成了鸡肋般的摆设。对于沃伦来说,由于多年来立法机关的不作为,法院的干预势在必行,否则的话,那就是对公然亵渎宪法和人类根本价值暴行的袖手旁观。
公正和平等是沃伦大部分判决的基础。对于这位首席大法官来说,涉宪案件相关的技术性议题,往往最终演变为有关公正的宏大主题讨论。辩论过程中他经常会问到一句话“但这公平吗?”其对于公正的关注,从中可见一斑。如果沃伦得出某人被不公正对待的结论,那么此时他绝不会让法规或者先例成为他为蒙屈者打抱不平的拦路虎。除了公正以外,平等的观念对沃伦来说意义更甚。如果说有哪个重要主题反复出现在沃伦的判决之中,那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种族的平等、公民之间的平等、贫富之间的平等、公诉人与被告的地位平等。他如此强烈地追求平等,其结果反而有点尴尬,因为有人说这是“法官们的革命”。然而,沃伦法院的一系列判决对平等权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影响,如果没有他的努力,当今美国社会种种追求平等权的运动或许根本无由开始。
作为一个法官,或许沃伦永远没有机会与那些经历几代时间参与塑造盎格鲁-美利坚法律结构的先辈们平起平坐。但沃伦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普通法传统的发言人。他是“结果导向型”法官的代表人物,他灵活运用手中权力来追求自己认定为正确的结果。他将司法权威发挥到了极致,在将公正和平等的理念播种到法律之土的过程中,对自己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未犹豫过。
沃伦认为,原则比先例更具约束力。沃伦在任期间最高法院的几项主要判决推翻了先前几届最高法院的裁决。往届最高法院的那些先例,将施行宪政权利的任务交给行政分支,而事实上,这些部门往往执行不力。在沃伦看来,情势是在逼迫法庭作一个抉择:要么遵循先例,要么维护正义。面临选择,首席大法官沃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认定正确的后者。
综上所述,沃伦的地位不在于他的理念,而在于他的决断。谈及对美国法律的影响,最高法院法官席上,能出沃伦之右者实在寥寥。然而,业界也不乏对沃伦的批评,相较于他作为马歇尔之后美国第二次伟大法律变革的杰出领袖功绩,其在学术和司法技艺方面,就显得不那么从容了。
4.约瑟夫·斯托里
32岁那年,约瑟芬·斯托里(Joseph Story,1779~1845)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法官,同时也是最高法院历届法官中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不仅如此,他还是一名业余诗人。他作过一首长诗《孤单的力量》(The Power of Solitude)并在一封信中称此诗的创作是“闲暇时光中最甜蜜的劳动”。后来,斯托里对这首诗作了一些添改,与其他诗作一并发表出版。不过,如果你读过斯托里儿子的传记摘录的话,你就会因为斯托里的弃文从法感到庆幸,而不会替文学界感到惋惜。显然斯托里后来也感觉到自己在文学方面的天赋有限,不然,他应该不会将他所能找到的自己诗作的复本全都付之一炬。
在马歇尔的法院里,斯托里拥有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所不具备的法学知识。事实上,斯托里之学养确实深厚。马歇尔曾说:“在这里,斯托里兄弟……能详述从《十二铜表法》(Twelve Tables)[ 古代罗马成文法的开端,大约公元前449年公布。——译者注
]到最新报告的法律案例。”斯托里痴迷于法理研究,他的长篇观点陈述总是很博学,频频引用先判和之前学者的著作。
不特如此,斯托里本身也是法官和律师们所看重的重要作家。在他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时,他共出版了九部专著(计十三卷次),讨论话题从宪法到商法,十分广泛。这些学术成果证明了普通法在美国的成功,并给法院提供了权威的指导。
斯托里最著名的作品,当属三卷本的《美国宪法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833),书中文字重述了马歇尔的宪政原则。斯托里在卷中通过逐条逐款的分析,证明马歇尔的法律理论是“正确的”宪法学说。正是斯托里的这三卷本著作树立了美国政府权力的国家主义形象,并为现在法律与新兴经济力量的调和打下基础。
在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斯托里大法官是马歇尔宪法学说的主要支持者,但绝对不是马歇尔的代言人或模仿者。如果说马歇尔是早期美国公法的主要设计师,那么在私法领域中占据相应席位的当属马歇尔法院中的斯托里。我们的商法和海事法律规则,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斯托里的判决留下的先例。斯托里用他的主要法律理念,将信托法与英国发展起来的基本的公司法相结合,催生了现代企业法人制度,使公司企业处理事务时有据可循。在斯托里时代,法人企业已经开始“快速发展,其扩展速度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引自詹姆斯·肯特)。毫无疑问,斯托里法律观念在上述发展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斯托里允许公司如同个人那样自由行动,这使公司能更好地适应不断扩张的经济的需求。
斯托里认为,经济进步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商法,使商业人士可以依赖。斯托里的一些重要思想促进了这样一部法律的创建。根据公认的商业习惯和便宜原则,由联邦法官们在无陪审团(斯托里认为商人“厌恶陪审团”)干涉下制定的统一商法,体现了商业社会的需求。
斯托里是共和党(杰弗逊派系)人,但他一般被看作是保守派法官的典范。不过,他的私法路径——尤其是关系商业发展的法律——却具有变革性质。斯托里曾撰文写道:“显然,法律必须主动适应需求,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就是斯托里,而非任何其他的大法官,致力于奠定我们私法的普通法基础,并使之适应新国家的形势。而且,在斯托里的努力之下,法律才可如此清晰地表达出来,以使法庭有能力将新规则运用到实际个案
……
★伯纳德施瓦茨教授在业界享有盛誉,我本人以及最高法院的其他大法官们都十分钦佩他在宪法学上的杰出造诣。鲜有法学教授的作品能与施瓦茨教授的媲美……他作品的质量堪称经典。
——美国最高法院布伦南大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