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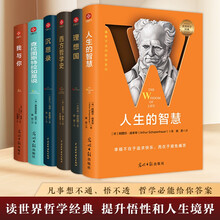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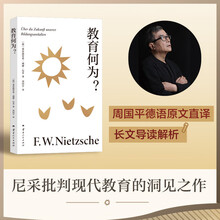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一个处在多彩生活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年代,一个一战刚刚结束、纳粹主义正在酝酿的年代,一个德国哲学的黄金年代。
马丁·海德格尔的事业平步青云,并邂逅了与汉娜·阿伦特的爱情。跌跌撞撞的瓦尔特·本雅明在卡普里岛疯狂迷恋上了一个来自拉脱维亚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正是这段爱恋使他自己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天才维特根斯坦是亿万富翁之子,他在剑桥被誉为哲学的上帝,而这样的天之骄子却来到了上奥地利州偏远地区担任乡村小学教师,过着完全赤贫的生活。最后还有恩斯特·卡西尔,他在迁居到汉堡中产阶级区的几年前,亲身经历了正在抬头的反犹主义。
本书除梳理了海德格尔、本雅明、维特根斯坦和卡西尔在1919-1929年间的各异的日常生活、情感经历和思想状况,还力求将四位哲人的思想予以对观,展现了他们在面临时代根本问题时各自的回答和应对方式。借助作者出色的叙述,我们在这四位卓越哲学家的生活道路和革命性思想中,看到了当今世界的根源。回望20世纪20年代,既是感悟又是警醒。
新的自我意识
实际上,本雅明论述的说服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人们对浪漫派那两个基本思路的看法。那两个基本思路涉及到的是普遍存在的所有事物与自身和与他者的关联,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这两个思路是合理的,就会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本雅明的观点。其实这两个基本思路也并不像第一眼看上去那么不合理。瓦尔特· 本雅明起码可以给他的父亲指出全人类身上存在的一个基本现象:人类具有自我意识。这个事实无可争议,每个人都能具体地感受到自我意识,根本无需对此存在任何理性怀疑。最终,每个人都拥有这么一种特殊的神奇能力。所谓自我意识,指的是通过自己的思考能力来思考自己的想法。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独立地“思考”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认知过程,在这个认知过程中,不但批评的客体(也就是我们思考的对象——我们自己的想法),而且批评的主体(正在进行思考的思维)都可以感受到一种变化,并感受到批评的客体和主体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正是自我意识能够进行自省的这种基本状况,成为了批评活动与他者产生关联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例子对于每种形式的关联都适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例子,它可以用来说明,当“一个存在物被另一存在物所认识,并与被认识者的自我认识叠合” 时,发生了什么。
事实上,处于变化中的这种事物的自我关联在持续产生着奇迹。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本雅明能够给一个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包括他的父亲解释清楚自己的想法。当一个人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联基础、自己与世界的关联基础时,这种奇迹就以一种特别明显和有效的方式发生了。伟大的艺术作品事实上就是这么一种自省过程的结果。因此,伟大的艺术作品在自我关联和与他者关联方面,内容特别丰富多元,并且具有启发性和自身特色,因此也可以促进人们的认知:
批评就如同在一个艺术作品身上进行实验,通过实验,艺术作品的反思被唤醒了,艺术作品被带入了意识领域,以及对其自身的认识。只要批评是对艺术作品的一种认识,那么批评便也是艺术作品的一种自我认识;只要批评指的是评价一个艺术作品,那么这种评价也是在艺术作品的自我评价中进行的。
对于本雅明来说,艺术批评概念的哲学核心存在于浪漫主义之中,就算浪漫主义者自己也有可能对此理解得不够清楚。要清楚理解这个哲学核心,需要观察一个持续较长的时间维度(整整150 年),还得进行尖锐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进行批评。本雅明正是想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批评这个任务当中。尤其是因为,批评活动也会对他以及在他自身内部产生作用,他批评的“作品”会不断发生变化,他也会由此认知自我。事实上,每个可以对自己的思维进行思考的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件作品。每个人都可以练习以批评的眼光检验自己和认知自我。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以批评的方式成长和塑造自我。每个人都能成为真正的那个自己。这种成长方式,就是一种批评。或者也可以简单说成:从事哲学。(P44-46)
变形
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家里留给他的遗产,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他有没有跟哥哥姐姐们商量过这个事儿?要不要最好再深思熟虑一下?不,他不打算再考虑了。“这下好了,”维特根斯坦家的公证人叹息道,“您真是下定了决心要在金钱上自杀。”确是如此。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不会动摇。他还是身着白色少尉制服,没有丝毫犹豫,几次打断公证人的问话,强调自己的决定不会改变,哪怕他今后再无经济方面的避难所,哪怕条约中没有任何特殊的附加条款,哪怕他再无退路不可反悔,哪怕他签字之后真的要永远和绝对放弃他所有财产,无可挽回。金钱上的自杀,说得好。
维特根斯坦刚回到维也纳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是从意大利战俘营归来的最后一批军官。此刻,1919 年8 月31 日, 他坐在维也纳一家气派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的全部财产——转让给他的姐姐赫尔梅娜、海伦娜和哥哥保罗。维也纳,这个曾经骄傲的帝国首都,如今只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破产迷你共和国的首都。在一战后的第一个夏天,维也纳最终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战后灾难,大多数奥地利国民主张与同样陷入瓦解状态的德国结盟,但是遭到了战胜国的禁止。96% 的奥地利儿童在1919 年夏天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爆炸式地飞涨,货币处于一种自由落体状态——城市风气也是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旧等级秩序完全崩溃,而新秩序也仍未全部运作起来。一切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变形了。当时30 岁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经过几年的战争岁月也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1914 年夏天,一战爆发仅仅几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根本改变生活的希望自愿报名入伍,成为一名下士。他出身维也纳最上流的社会,欧洲最富有的工业家庭之一,剑桥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哲学界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老师伯特兰· 罗素和戈特洛布· 弗雷格都期待着他完成“下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观察得没错,那么其实战争已经完全实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个人愿望: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他在加利西亚、俄国和意大利的前线地带多次目睹了生死,他开枪杀人,他通过阅读列夫· 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找到了基督信仰。尤其是他在前线漫长的暗夜等待中完成了哲学著作。他自己坚信,这本著作不光是哲学中的下一个巨大进步,甚至也是最后和终结性的进步。
但是,这本著作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什么都没有达到。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是达不到什么目的的,这种无意义性每天都在折磨着他。1918 年夏天,他最后一次上前线前回到家里度假,期间他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了最后润色。正如他在著作的前言部分中写道的:
因此,我认为,本质上来说,我已经最终解决了诸问题。如果我在此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价值就在于:它表明了,当这些问题获得解决时,我们由此所完成的事情是何其的少。
换句话说,在构成人类生活条件、给予人类生活意义、价值和日常希望方面,哲学没什么可以说的,也没什么可以争论的。为什么基本上会是如此——为什么没有逻辑方面的结论、论据,也没有站得住脚的意义理论能够涉及生活实质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著作正好永久展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P47-49)
对本有的忠诚
1919 年,年轻的哲学家们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人们可以这么来理解此种特殊挑战:有一种生活方式,它已经超越了“命运与性格”的决定性“框架”,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现在正需要人们为自己和为自己那代人给出理由。放到具体的人生经历上,这首先意味着要敢于冒着失败的危险,从迄今为止具有引领作用的结构(家庭、宗教、民族和资本主义)中突围出来。第二,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找到一种存在模式,这种存在模式可以对战争经历带来的紧张力进行加工,将其转化到思考和日常此在的领域中。
本雅明想通过浪漫的手段——通过对所有一切进行批评从而推进一切——来实现生活方式的更新。维特根斯坦则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他在面临最强烈死亡恐惧的时候感受到了全然神秘的平静和与世界的和解,他希望能够把这些短暂的感受延长到日常生活中去。海德格尔在1919 年的自我境遇中给自己提出了一个任务,人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任务:海德格尔目前已经存在的自我形象是一个“狂野思想家”,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在寻找一种方式,可以将战争经历带来的紧张感和平凡的日常进行和解,使两者可以和平共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战争带来的紧张感和思考的紧张感具有基本相似性。一方面是一种处在思考风暴中的生活,另一方面是日常生活,所谓和解指的是这两种生活之间的和解。而早在1919 年,海德格尔的任务就对(紧张和日常之间的)边界特点提出了所有要求:于是,海德格尔在1919 年5 月1 日写给伊丽莎白· 布洛赫曼(她是海德格尔夫人长年最好的朋友)信中这么写道:
我们得对有意义生活的高度紧张感做好心理准备——而且我们必须在这种紧张感中持续生活——我们并非要尽情享受这种紧张感,而是更多地要把它构造成生活的一部分——在生活的推进中带着这种紧张感一起生活,并将其纳入未来生活的律动中去。
一个有稳定恋爱对象的男士如果用更为哲学的方式,就很少会这么解释:恋爱关系之外的桃色事件只限于少数几次拥有“高度紧张感”的碰面。但是,海德格尔如同迷恋于情欲一样迷恋着思考:他要给自己留有机会,让自己拥有伟大的瞬间,让自己可以真正体验到洞察的发生,以所谓忠诚于伟大的本有的方式来度过此在的余生。对于这种忠诚来说——在他此在中唯一令他感兴趣的忠诚——他想要必须做到一点:自由。在思考中、在行为中、在恋爱中,都得自由。1919 年春天,他终于开始从锁链中挣脱出来:从天主教义体系、从父母家、从他的婚姻,以及——如果人们仔细观察的话——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挣脱出来。(P66-67)
不被喜欢的人
1919 年冬天,还看不到德国文化向学者卡西尔显示出特别慷慨仁慈的一面。这年是卡西尔在柏林大学担任教师的第十三年,虽说此时他已经是受到国际认可的学者,可他依旧还只是所谓的“编外教授”,没有被正式录用为公职人员,没有给学生进行考试的权利,哲学家只是第二职业。在柏林的电话本中,他登记的信息还是实事求是的“私人讲师”。一次又一次,每当出现评选教授的机会时,卡西尔总是被忽视,他也习惯于这么给他的妻子解释:“我总不能强迫他们喜欢我吧,事实上他们就是不喜欢我啊”。在过去几年中,卡西尔已经写出了好几本高水准的著作,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1911 年出版);在卡西尔的哲学老师和支持者赫尔曼· 柯亨逝世后,1916 年卡西尔就成为了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毫无争议的领军人物,而且他就算不是当时最具引领作用的康德专家,那起码也是其中之一。在学术职业前景方面,战争岁月打下的烙印对于卡西尔来说自然更多地成了障碍,而不是好处。在民族主义的保守圈子里,以柯亨和卡西尔为核心的马尔堡学派学者越来越明显地遭到质疑。有人认为,他们作为“犹太学者”正在将康德真正的学说和影响与其“真正的”也就是说“德国的根源”疏远,并将后者清除。早在一战时期,民族主义讨论中的收缩倾向已经继续加重了国内的反犹太主义——例如1916 年在德国军队中进行的“清点犹太人”活动。这种反犹氛围随着美国参战变得更加浓厚,还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卡西尔”是一个来自富裕市民阶层的德国―犹太家族典型姓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柏林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占据着中心位置:工厂主、工业家、工程师、出版商、医生、艺术收藏家,以及哲学家。卡西尔家族是被“同化和吸收”入德国社会的典范,而正因为如此,出于德意志民族本质逻辑的特殊“内部原因”,卡西尔家族特别令人怀疑。(P70-72)
新的启蒙
对于卡西尔来说,以分析的形式揭示出上述背景,意味着以最吻合康德理念的方式推动了启蒙。也就是说,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成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不成熟状态首先指的是:概念的真正背景指引着我们进行思维活动和对世界做整体理解,而当我们面对这些概念背景时,却情愿保持着不清楚和未经省察的状态。
这种舒适感,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种漠不关心,也是海德格尔1922 年在其解释学情境的显示中斗争的对象。在论文中,海德格尔强调道,有必要对现存的、尤其是哲学的概念进行一次“解构”。与此相对,卡西尔的分析目标恰不是对现存基础概念进行解构——解构除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神话语言彻底全新的开始之外,还能通向哪里?——而是说,概念承载着一种彻底的启蒙动力,这种动力会让各个可能性和不可能性都形成自己的意识。不管是神话的、宗教的还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形式,每个概念形式都必然带来意识的形成。
每个现代文化在其任何一个发展时间段里都面临着主要危险。卡西尔认为首先有两种危险。第一,每个文化明显都具有倒退性,它的每个发展步伐都是可逆的。第二,正是在极端危机、极端紧张和极端迷茫的时代中——例如在1922年和1923年——文化会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文化以减负的形式倒退到一个最大程度上黑白分明的解释模板中,例如尤其由神话思维提供的那种解释模板。(P116-117)
坏邻居
……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住在汉堡阿尔斯特河支流另一侧的一户人家的花园与卡西尔家相邻,邻居先生名叫哈赫曼。夏日里的一天,卡西尔夫人非常有礼貌地询问哈赫曼先生,哈赫曼家7 岁的儿子在他自家花园里玩耍时能否声音小一些,或者去别的地方玩耍。因为卡西尔夫人此时正在她的花园里面阅读,她的父亲也来到汉堡,待在女儿这里,而哈赫曼家孩子极具穿透性的吵嚷声很是要命,这让父女俩觉得深受打扰。听到卡西尔夫人的询问,哈赫曼先生怒火中烧,他对着卡西尔夫人叫嚷:“您觉得您就没有打扰到我们吗?您那纯种的外貌就已经是在打扰我们了——你们所有人肯定全都是巴勒斯坦来的。”
卡西尔的夫人托妮· 卡西尔在流亡美国时回忆到这次栅栏边上的争吵,感到这是一件令人记忆深刻的大事儿:“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与德国的分离。”对这件事儿起决定作用的,不光是哈赫曼肆无忌惮直接表达出来的仇恨,托妮还明确感受到,在魏玛共和国这段早期的危机岁月中,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犹主义爆炸似地混合在一起,共同发酵。这种混合在最高的教育圈子里都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也获得了公众的支持。
……(P155-158)
知觉在回忆
在这里我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从文章开头和文章提交方式来看,本雅明的论文无论是在标准上还是在要求上都与一篇以学术为目的的论文相去甚远。难怪论文鉴定者们深感震惊和惊讶。他们有充分理由要求和期待看到一篇质量上乘的论文,但拿到的却是一篇哲学誓言。而且这篇誓言并不是要表现作者的思想贫瘠,而是哲学家所处时代全部哲学思考的贫瘠。本雅明的《认识论批判序言》本身想要成为一个事件——还要成为一种起源,能够吞噬所有、打开所有的起源,由着这个起源开始了一种新思维,以便能够克服现代哲学。确确实实,太厚颜无耻了。
首先人们清楚地看到,本雅明给现代哲学推荐了怎样一种具有彻底反动色彩的起源选择。最终如本雅明所说,只有上帝——一种神圣的本有才能保证真正的救赎。语言现象本
身也是那样一种神圣的东西。就如语言——它是了解这个充满意义的世界的基础——对于本雅明来说并不是人类起源,那么觉察真理(真理存在于“纯语言”中)的神圣本有也不可能是起源,这种神圣本有令人震惊。和维特根斯坦完全一样,本雅明也一再坚持不能用一门语言来解释这门语言本身的奇迹。充其量最多只能通过特别的语言表达方式来显示语言和语言奇迹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
本雅明将如下行为命名为哲学:从事实上知觉不到的某个具体时间范围出发,给出对“知觉起源”真正原因的集中指示。而且是以回忆形式进行的:
理念在词的符号性质中可以认知自我,这种认知自我是与所有的向外传达行为相对立的。哲学家要做的事就是,通过阐述再次赋予词的符号性质以优先权。因为哲学不能妄称可以敞开地言说自我,所以只能通过一种回溯到未知觉状态的回忆来实现上述之事。
回忆行为的发生方式首先在于,要沉入为了回忆而创造出来的艺术思维图像中。确切来说在这点上,回忆所具有的是一种知觉的被动的特点,而不是那种积极主动的认知特点。关于这一点,本雅明谈到了一种“富有成果的怀疑”。他明确强调在这点上他关心的仅仅是洞悉一种不可能性。要落实这种怀疑,那么就要在所有可能的经验库中刻意使自己的感官对全部现象的明显特点变得敏锐,并要深思熟虑地重复进行这种敏锐化。这就有点儿像是佛教的曼陀罗13,搜寻着的精神主体在曼陀罗的花纹绘饰中必须进入沉静状态,内心澄明、抹去所有杂念图像。用本雅明的话来说:
这种怀疑可以比作思想的深度喘息。在这喘息之后,思想可以悠然忘我于最细微处,而毫无任何忧愁之迹。因为在观察深入艺术的作品与形式以探测其内涵时, 往往都是在谈论最细微处。以消耗他人财物的那种草率手法来对待艺术品,这种急切是因袭成法者固有的,与庸俗之辈的热情相差无几。而真正的冥思则与之相反,对于这种冥思,对演绎方法的拒斥则伴以一种不断扩充的,日益热切的对现象的回溯。 这些现象绝不会陷入始终是某种阴郁惊诧的对象这一困境,只要对这些现象的表现同时也就是对理念的表现,而且现象的个体也在表现中得到了拯救。
对本雅明的沉沦诊断具有决定作用的乃是这种洞见:一种天堂式的“回归到现象”、回归到“事物本身”的理念,是否无论如何都无法导向哪种评判形式呢——答案是,无法导向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评判。
所谓非常具有判断力的现代主体提出了无理要求,鉴于世界的需要,将自己提升成法官,对善恶进行评价,并宣传这样的观点:人类伦理学可以建立在现象学——语言现象本身——的基础上。这种无理要求对于本雅明来说意味着现时代真正严重的、扭曲了所有东西的原罪。根据他论文的主旨,他把这种原罪和德国的巴洛克悲苦剧起源连接在一起,将其作为一种衰落的典型,也就是说:
巴洛克所含有的这种可怕的、与艺术相悖的主观性在这一点上与神学的主观化实质相汇合。《圣经》以知识的概念引入了邪恶。蛇预言说,第一个人将会“认识善与恶”。但是上帝在创世之后说的是:“ 上帝看到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此,关于邪恶的知识根本是没有对象的。邪恶并不存在于世间……关于善和恶的知识因而也就是所有实际知识的对立面。在牵涉主观化的深度时,这知识基本上就只是关于邪恶的知识。按照克尔凯郭尔所理解的深刻词义,这知识就是“无稽之谈”。作为主观性的胜利和对实物的专制统治之肇始,这知识是所有寓言式观察的起源……因为善和恶是无法命名的,是无名者,是外在于命名语言的,而天堂中的人正是用这种语言来给实物命名的,在质疑的深渊中他离弃了这种语言。
主观性的胜利、本着内在固有精神而产生的对事物的独断统治、尤其是对符号之下自行物化的自然界的统治,这些最终也会导致人类无可救药的物化。一句话说,真正的现代悲剧正是在此之上建立起来,本雅明在他著作中讲的就是现代悲剧的不幸始源。特别是围绕着善和恶的知识事实上并“没有对象”,“不存在于世界间”的问题。用本雅明自己特有的命名存在论来说就是:善和恶的知识“外在于命名语言”。
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保持沉默。而现代主体在其彻底自我授权的意志中却不是这么做的,而是要去“胡扯闲聊”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并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深地陷入一种麻木的无知觉中。其最终效果就是悲伤,虽然悲伤的效果自然总是以隐晦的方式被觉察到的。
……(P260-264)
第一章 序言 魔术师
第二章 跳跃 1919
第三章 语言 1919-1920
第四章 形成 1922-1923
第五章 你 1923-1925
第六章 自由 1925-1927
第七章 拱廊街 1926-1928
第八章 时间 1929
结语
著作目录
参考文献摘选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