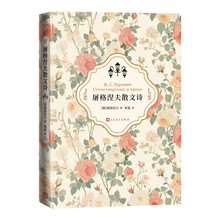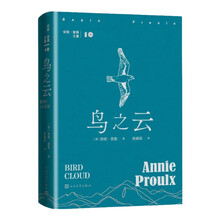千年译事话短长
董燕生
恐怕从第一批开口说话的智人出现在地球上,翻译活动就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从而促进了部族的融合,生产范围的扩大,社会组织的日益复杂,最终导致高级文明的产生。到了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译的重要性就更加彰显了,因为人类文化不仅需要在世代传承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也需要在横向交流中获取灵感以求丰富。任何一个部落和民族,只有向别人学习,才能不断地充实自己,逐渐攀升到文明发展的高峰。当今世界上绚丽多彩的多元文化正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为了更具体深切地看清翻译活动的重要社会功能,只要观察一下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两大文明群体的相关历史断面就够了。
先说西班牙。大家知道,智者国王阿封索十世,在十三世纪组织大批学者从希伯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翻译了大量古代典籍,其内容涵盖了文学、哲学、宗教、法律和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在被愚昧和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欧洲上空投出一道启蒙的光芒,为一个世纪后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吹响了号角。从那时候起,整个西欧开始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现代社会迈进。
再说中国。自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正式大量翻译佛经以来,外帮的、面貌迥异的宗教信仰,哲学体系和思想方法日渐融进了中国文化,打破了汉代确立的独尊儒术、一统天下的僵化局面,推动了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技诸方面的长足进步。这里仅仅举出一个与语音学和文学有关的例子:受梵文拼音文字的启发,汉语的音韵研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这期间的重大创造之一就是反切注音法。很显然,对汉语语音的深入了解,无疑为唐代诗歌的严谨格律奠定了自觉的语音学理论基础。此外,佛教的传入对中国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的深刻影响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果说佛经翻译构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那么,明末清初便在开始酝酿第二个高潮了。它的鼎盛时期从清末一直延伸到五四运动之后,对中国的近代社会产生了深刻又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翻译高潮的初始阶段,以介绍西方自然科学为先导,然后逐步扩展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而推动中国人的观念意识日渐向现代范畴转轨,一步步踏上汇入世界民族之林的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痛苦的历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三四百年里,一代又一代翻译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很难设想的;我们将首先面临理论工具领域的一片空白,因为我们的老祖先,无论是儒、道、释哪一家都没有传下创建现代国家的理论和方法。这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到外部世界去寻求有关的思想学说,以资借鉴。
然而翻译活动不仅限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语言演化的走向。西班牙语和汉语的发展历史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在现代西班牙语的形成初期,智者国王阿封索组织领导的典籍翻译起了决定性作用。在这之前,所谓罗曼斯语刚刚从民间拉丁语脱胎而出,尚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诸多变体之间摇摆不定。正是上述历史性的翻译活动在散文方面的典范作用,勾勒了西班牙语的明晰雏形。
汉语的丰富和发展也不止一次地得益于翻译活动。佛经翻译就为汉语注入了大量新概念和新语汇(佛、菩萨、塔、涅磐、刹那),赋予不少固有词汇以新的含义(众生、因缘、果报、影响、冤家),而且还不仅如此:在魏晋以后短短二三百年中,它还使汉语文献语言的词汇系统迅速双音化,显著改变了上古汉语单音词占主导地位的面貌。另一方面,出于普及佛教教义的需要,译文中大量采用口语,从而促进了文体的演变,同时在语法结构上也引入了新的形式。
近代的翻译活动在塑造现代汉语方面的作用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我们每天挂在嘴上的一大批常用词汇,都是经过一代代翻译工作者的创造、移植、锤炼才逐渐演化、成型并且普及开来的。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可以顺手拈来: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经营、自由、民主、专制、科学、法律、生物、物理、化学……在这类词汇中,有些是汉语固有的,但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些则是利用汉语词根新创的。更有意思的是一大批这类词汇是绕道日本,通过先出口(日本人根据中国典籍发掘或创制的)后内销的曲折途径引入的。它们的出现完全是历史的必然,是用来表达从域外输入的新事物、新观念和新思想的。还有些词汇本身就多少保留着外来痕迹:逻辑、卡车、保龄球、绷带、水泵、赋格、拖拉机、冰激凌……,还有不少外来色彩更浓一些:模特儿、摩托、苏打、白兰地、夹克、凡士林、福尔马林、沙发、雷达…...。除了词汇,现代汉语还从域外引入了相当数量的固定短语:武装到牙齿、鳄鱼的眼泪、火中取栗、特洛伊木马、泥足巨人、替罪羊、钉在耻辱柱上、天方夜谭……。
大家知道,语法结构在语言诸要素中是最为稳定的,短期内很难有什么显著变化。但是在从清末开始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也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面貌。不妨随意举几个例子:我可以帮你一下,尽管我很累;那咱们就这么做了,如果你同意的话,这样的倒装句不仅在文言文里找不到先例,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里也难觅踪迹,完全是从印欧语引入的。再比如:人称代词带很长的定语:受尽了折磨的她;使用频率很高的状语结构:原则上,本质上,基本上,实际上,理论上......;一些用于主题化的结构:关于......,就......而言,以及名词的动词化和不及物动词的及物化,等等。
简单追寻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就不难发现翻译活动的重要性,这也就意味着翻译工作者肩负重大而光荣的社会职责。
翻译工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难!不过这一点非得置身其间才能深切体会。难怪有人认为,只要案头放着一本双语词典,谁都能动手翻译东西;也难怪翻译的稿酬如此低廉,与创作相比,何止天壤之别!这种反差实在很不公平。我国近代大诗人、大学者闻一多先生说得好: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跳舞”。如此说来,创作显然是“放开手脚的跳舞”了。我无意断言翻译一定比创作需要更高的才能和技艺,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作家可以避开自己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而翻译家却必须面对那些自己从未经历过的外域事物,并且千方百计去理解它们,然后再将外语的表达方式转换成汉语。
那么,翻译工作者究竟要面对和解决哪些困难呢?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语言差别。这种差别造成的翻译上的困难,并非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靠一本双语词典就应刃而解了。大家知道,不同语言的词汇之间根本没有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尤其是那些抽象而多义的词汇。所以最完善的双语词典也只能尽量多地提供常用参考译文,绝无穷尽所有可能性的义务和能力。所以译者经常要以词典的解释为基础,根据具体语境,自己搜索枯肠地去寻找恰当的译文。这在任何两种语言的互译中都是司空见惯的,在汉语和印欧语的互译中尤其如此。比方,西班牙语地区的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形容词simpático,双语词典提供的参考译文是:给人以好感的,可亲的,可爱的;同情的;共鸣的,共振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