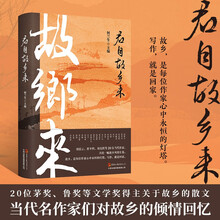致科学院的报告
可敬的科学院院士先生们:
承蒙诸位垂爱,邀请我向贵院呈交一份关于我过去所经历的人猿生涯的报告,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我深愧无法满足诸位的要求。自从我脱离人猿生涯,已近五年了。从历书上看,这段时间仿佛很短,事实上,尽管我的日子过得如同白驹过隙,时光流逝起来还是极其迟缓。诚然,我生活中有优秀教练的伴随,也不乏金玉良言的劝诫以及喝彩叫好声和乐队的管弦声,然而根本上我还是孤独的,因为我的那些监护人为了造成一种印象,总与我保持一个距离。如果我一直死抱住我的出身,执著于少年时代的记忆,我决不会取得目前的成绩。老实说,“不固执”就是我羁绊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第一戒;虽然我是只自由的人猿,但是我甘心接受这样的约束。其后果呢,当然是过去的影子越来越淡薄。倘若人类许可,我原本也可以经由一道长得足以跨越天地的桥梁,回复到原来的生活。可是我既然驱策自己在造化规定的事业上努力前进,我背后的那个入口也就逐渐缩小变窄;我觉得在人类的世界里更加舒服,格外舒畅,来自我的“过去”跟在我后面的那股强风开始变弱,到今天,它仅仅是一丝吹拂着我的脚跟的微风了;而远处的入口,也就是风所发出和我自己所来自的地方,已变得那么狭窄,即使我有足够的力量与意志想回去,在穿越入口时也非落个遍体鳞伤不可。一句话,用我喜欢的形象的语言来说,一句话:先生们,你们过去的人猿生涯——你们经历中的别的事情也一样——和你们现在之间的距离,不见得比我过去与目前之间的距离大多少。可是世上每一个生物都有搔脚跟的癖好,从小小的黑猩猩到伟大的阿契里斯阿契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童年时曾被母亲放在冥河中浸过,所以刀枪不入;只有脚跟捏在母亲手里,没有浸到,成为全身的弱点,也是后来致死的原因。阿契里斯并无搔脚跟的癖好。作者是在表示人猿一知半解,以己度人,乱用典故。莫不皆然。
然而如果把要求降低一些,我还可以满足诸位的愿望,为诸位效劳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握手,握手是表示诚恳的意思。既然这样,今天,当我达到事业的高峰时,我愿意在第一次握手所表示的诚恳之外再添上几句诚恳的话语。我在这儿要告诉贵院的事实上并没有任何新内容,当然不会符合诸位的要求,也不能表达我的好意于万一——然而,虽然如此,我的叙述还是应该能够表明:一只往昔的人猿需要遵循什么道路,才能进入人类的世界,并且取得安身立命之道。但是,倘若我不敢肯定自己正确,倘若我在文明世界所有大舞台上的行为不是全然无懈可击,我是不敢用下面琐碎的细节来烦渎诸位的倾听的。
我的原籍是黄金海岸。至于捕获到我的经过,那就得借助于旁人的证词了。海京伯公司派出的一个打猎探险队——顺便插一句,后来我与探险队的队长一起干掉过许多瓶上好的红酒——埋伏在海岸附近的一个丛林里,恰巧我和一伙人猿在傍晚时分下来喝水。他们向我们开枪,我是唯一被击中的人猿。我身上中了两枪。一处是在面颊上,是个轻伤,可是留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大红疤,使我得到了“红彼得”的诨号。这个称呼够可怕的,与我完全不相称,只有人猿才想得出这样的名字,仿佛我和那个耍把戏的人猿彼得——他不久前才去世,在地方上还有些小名气——唯一的不同就是我面上有个红疤似的。不过,此乃插话而已。
第二颗子弹打在我的大腿上。这伤势可不轻,直到今天我的腿还有点瘸。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那是一万个专拿我出气的空谈家中的一个写的,文章说我还没有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人猿本性,证据是每逢参观者来访问时,我总爱脱下裤子给他们看子弹是从何处穿过去的。写这篇文章的人的手指真该一个一个的给子弹打断。至于我,只要我愿意,当然可以在任何人面前脱下裤子,你们不会看到别的,除了梳理得很顺的毛和一个伤疤——请允许我为了特殊的用途挑选一个特殊的词儿,以免引起误会——一颗漫无目标的子弹所造成的伤疤。一切都是光明磊落的,什么都不用隐瞒,当痛苦的真实受到怀疑时,高明的人自然会摒弃华丽的装饰。不过倘若那篇文章的作者胆敢在来访者面前脱下裤子,那情形就大相径庭了,我敢担保他不会这样干。既然如此,我也请这位文雅的先生不必多管我这个粗坯的闲事!
在挨了这两枪之后,我恢复知觉时才发现自己来到了海京伯轮船中舱的一只笼子里——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逐渐有记忆的。这笼子并非四面都是铁棚的那种,而是钉在柜子上的,只有三面是铁栅,第四面就是柜子。笼子低得我站不直,而且又窄得我坐不下去。因此,我只得弯着膝盖蹲着,身子无时无刻不在颤抖;也许有个时期我谁也不愿见,只想呆在黑暗当中吧,我总是把脸朝向柜子,所以笼子的铁栅都嵌进了我背部的皮肉。在捉到野兽后的最初阶段,用这种方法囚禁野兽应该是有其优点的吧,我通过自身的经历也无法否认,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也的确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可是当时我并不作如是观。我生平第一次发觉自己没有了出路,至少是没有简捷的出路。紧贴在我面前的是那个柜子,一块块木板紧紧地接在一起。的确,木板间有一条缝,我刚发现的时候还天真得狂喜地大吼了一声呢,可是那条裂缝小得连尾巴都塞不进去,不论人猿有多少气力也休想把它撑大一些。
应该说,我发出的声音小得异乎寻常,这也是后来听别人告诉我的。人家从我的声音里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就是我很快就会死去,要么就是我能够度过第一个阶段,训练起来准定非常听话。我也真的度过了这个阶段。我绝望地啜泣,痛苦地捕捉跳蚤,悲惨地把一只椰子舐来舐去,不住用脑袋撞柜子,逢到有人走近就对他吐吐舌头——在新生活的第一个阶段里我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可是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只有一个感觉:没有出路。当然,我现在只能用人类的语言表达当初作为人猿时的感觉,所以表达得并不准确,可是虽然我无法恢复往昔人猿生涯的真实感受,我刚才所说的情况无疑还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这以前,我对什么都很有办法,可是现在却一筹莫展,我给拴住了。就算我给钉死在一个地方,我自由行动的权利也不至于比现在更小些。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搔搔足趾之间的嫩肉,我找不到答案。用背脊死命地顶铁条,直到自己险些给勒成两半,我还是得不到答案。我一无出路,但是我必须找到出路,否则我就活不下去。老是这样面对着柜子,我这条命非断送不可。可是在海京伯马戏团看来,柜子跟前恰恰是最配人猿呆的地方,既然如此,那我只得不当人猿了。这真是一个周密而清晰的结论啊,我准是用尽肚子的能耐构思出来的,因为人猿是用肚子思想的。
我担心人们不太了解我所说的“出路”指的究竟是什么,我是就最完整也是最通俗的意义上来用这个词的。我故意不用“自由”之类的字样,我指的并非任何方面都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感觉。也许因为我是人猿吧,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也见过渴望自由的人。可是就我来说,不论过去或是现在,我都不希望享受这种自由。请允许我顺便插一句:我甚至觉得,人类因“自由”两字而上当受骗是否已经太多了一些?正因为自由被视作最最崇高的感情之一,所以,相应的失望也算是崇高的了。好多次,在杂耍戏园子里,还没轮到我上场的时候,我常常看空中飞人怎样在屋顶高处的秋千上表演。他们摆动自己的身子,晃来晃去,向空中跳去,扑进对方的手里,这一个用牙齿咬住那一个的头发。我就想道:“这样的自我约束居然也算人类的自由。”这对神圣的大自然母亲该是多大的讽刺!要是让人猿看到这种表演,戏园子的墙壁不给他们笑塌才怪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