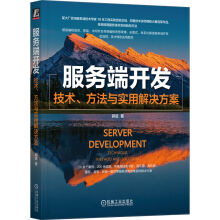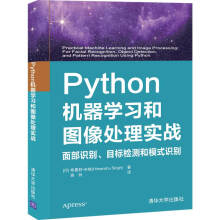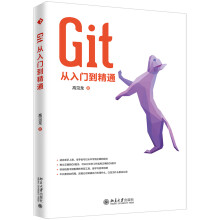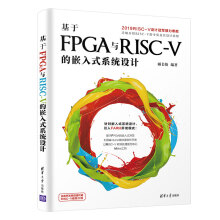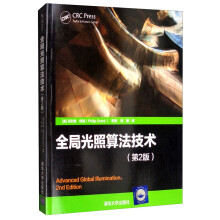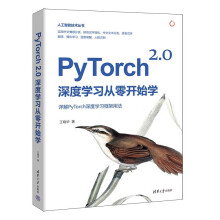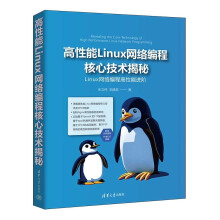王佑夫一再用民汉对比,是由其对中国文化构成二元观和文野相对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由两大系统构成的,即:以中原为中心、以汉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系统和以周边为圆圈、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系统”“汉族文化作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心凝聚”。“多元一体”在表述中被简化成“二元一体”①,“中心”与“周圈”的措辞中表现出一种中原中心与汉族中心的思维模式。接着他进一步指出:“先进的农业生产既带来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促进了理性思维的发展,于是,汉民族在发展诗歌创作的同时,散文兴盛起来;后来城市繁荣,小说、戏曲文学随之林立。相对落后的牧业或半牧业生活,使得相当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长期停留于诗歌创作。”②如果说“二元一体”表述还是一种隐晦的“文野相对”的思维,在此用“先进”来定位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和城市文化,用“相对落后”来定位游牧半游牧文化,便体现出明显的进化论思维模式。虽政治上一再强调平等,但将55等同于1的这种二元划分,还值得反思。
除理论的建构外,有研究者已将“二元对立”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如张胜冰在《西南少数民族原始诗学与汉语诗学的关系》一文中,便从“少数民族”中抽取出“西南”板块,与汉语诗学比较,认为西南少数民族的诗学是一种以口传文化为基础的“原始”的、缺乏理性的诗学,而后者则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理性化诗学。③“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可以随研究者研究兴趣和目的而随意割裂的对象,实质上恰好反映出“少数民族”本身是丰富多元的。
“文字中心”的倾向是目前非汉民族文论研究中存在的另一个缺陷。虽诸多学者承认非汉民族文论呈多样化的特点,但在具体的论述中,仍难以摆脱文字中心的羁绊,如王佑夫认为的“古代少数民族文论存在形态呈多样化的特点,其中之一是书面文论与口头文论并存,口头文论是一种集体创作,既无写作时间可考,又具有一定的变异性”。但在接下来论述文论产生时他又说:“少数民族文论的最初源头目前尚难寻觅,从现在发掘的资料及其考察看,它大约开始于南北朝时期。”④将文字文本的出现视为文论的起点,恰恰忽视了其口传性的存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