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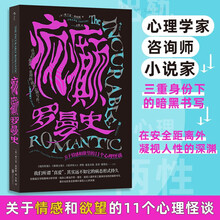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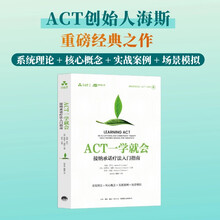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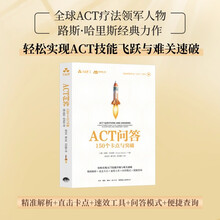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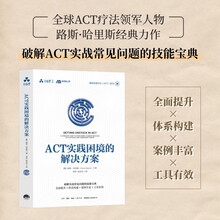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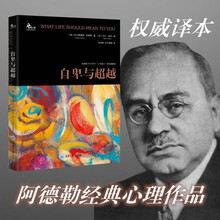
【一】 耶鲁大学“抑郁自救”课:怎样靠自己战胜抑郁症?
【二】你有抑郁症前兆吗?
在这个心理医生的自愈故事中,可以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三】当一个心理医生患上抑郁症,她会怎么做?
她是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员;
她是有着3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医生;
她是一个有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
她用自己的自愈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抑郁自救”课。
【四】陷入抑郁的人,该怎样放过自己?
内心抑郁的人,需要了解的5个问题:
ONE 为什么你比别人更容易抑郁?
TWO 抑郁症真的是病吗?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待抑郁症?
THREE 为什么那个平时爱笑、爱闹的人,会忽然抑郁了?
FOUR 生命中所遭遇的悲伤和抑郁,一定是坏事吗?
FIVE 靠自己能够走出抑郁症吗?
【五】一个心理医生战胜抑郁症的自愈故事,写给每个被抑郁夺去力气的现代人!
名人(媒体)推荐
《好吃的悲伤》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本书充满着伤痛、希望和自我疗愈的智慧。对于任何陷入抑郁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本必读之书。
——托马斯·H·斯蒂伦(Thomas H. Styron),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副教授
作为创伤心理学家和研究人员,我强烈推荐这本书。对于任何想了解自己的痛苦并寻求解脱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必读的。索耶博士出色地说明了抑郁症自我康复的可能性,尽管她内心的悲伤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消失,但她已经做到了“一边嚼着悲伤,一边战胜了抑郁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
——琼·M·库克(Joan M. Cook),博士、耶鲁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副教授
这本书展示了作者漫长而痛苦但最终取得成功的抑郁症康复之路。在精神病医院进出多年之后,她获得了博士学位,结婚生子,并开始了职业生涯……推荐给对抑郁症治疗感兴趣的心理从业者,更推荐给正在遭受抑郁折磨之苦的读者们。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在现代生活中,每个人都离抑郁症很近。
抑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懂它,还对它存有偏见。
悲伤是块巧克力,味道好极了。
这是一个关于悲伤、抑郁、坚持、改变和成功的故事。
心理医生安妮塔·佩雷斯·索耶,曾是一名内心充满黑暗和悲伤、有着自杀倾向的抑郁女孩。她曾被误诊为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期间遭受了89次电击治疗,病情急剧加重。为了搞清楚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了,她开始阅读心理学书籍,尝试自我的内在探索,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认知和行为。病情有所好转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心理学系教员和心理医生。
成功走出抑郁症的索耶,决定把这一切写下来,用自己的自愈故事,给所有人上了一堂“抑郁自救”课——悲伤和抑郁并不可怕,它是命运赐予我们的考验,是我们认识真实自我的途径。所有你曾经历的悲伤和抑郁,终将成为你生命的滋养,让你更好地活下去。
悲伤,是心灵成长的代价。
有一天你破碎重生,
所有的悲伤都将化为一份美味的食物,
滋养你仍在继续的生命。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正在长大或已经长大的孩子,
他们内心有伤,不善表达,不被理解;
献给所有积极关注病人的、灵魂有光的治疗者;
献给所有理解我、给予我帮助的家人和朋友;
献给所有相信我的人。
第一部分:被扭曲的悲伤
我觉得我没有疯,我只是一个对自己充满悲观,有着自杀倾向的女孩子。
但没有人能够看到这一点,他们都被我的自杀倾向吓坏了,所以他们才会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我。
然后,我就真的要疯了。
第一章 他们认定我疯了
1960年5月
涨潮的海水拍打在岸边冰冷的岩石上,浪花四溅散开。我们住的小屋就在这岸上。天空很晴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咸咸的味道。萨拉在纱门外催我快点出去。大家都想去游泳,可我完全没准备好。“你们先去吧,”我对她说,“一会儿我就去找你们,别担心。”
她皱起了眉。我不愿看到萨拉因我心烦的样子,但我仍然无法说服自己动身。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是在想该拿我怎么办。良久,她说“那好吧。”就跟其他人一起朝海滩跑去。“你也快点,别再磨蹭啦!”她边跑边喊。
那个周末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我们,或者说我高中的朋友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蒙托克角之行。虽说我们都是高中生,但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青少年,因为青少年应该是朝气蓬勃的,而我只有死气沉沉,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只是轻声附和。朋友们说话时,我脑中总会响起一个奇怪的声音,有点像铃声或高频的嗡嗡声,而朋友们似乎变得很遥远,就像一些我可以用手移动的玩具。
那个周末,我打算自杀。等朋友们都走后,我会在身上绑上沉重的石块,义无反顾地走向大海,直到海水漫过我的头顶,将我淹死。但我还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去做。
也许是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游泳,也许我还在琢磨一些实施计划的细节,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泳衣换好。当我终于打开纱门,萨拉、芙兰,以及其他人早已不见踪影。我一脚踏进了阳光里。
我紧紧地抓着浴巾,低头看着脚一步步踩进温暖的沙子里,将一串串深深的脚印留在身后。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我抬起头,向声源处望去,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褐色的雪佛兰,之前它并没停在那里。那好像是我父母的车。啊哦,我想。
我加快了脚步。一时间,闪闪发亮的沙子,哗哗的海浪声,与脑中的嗡嗡声掺杂在一起,让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像是被巨大的热气球送到了空中,感觉好像飞了起来。我摇摇头让自己回到现实,步子迈得更快了。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站在了那辆车旁,紧挨着萨拉。她站在那儿,跟我父母面对面地站着。啊哦。
“真的没什么好担心的。”萨拉跟他们说。她在维护我——她的确是我的朋友——但她看上去比她说得更担心。他们都跟她说了什么?
萨拉转向我。“你爸妈觉得你在这里不安全。”她用抱歉的语气说,“他们想让你离开,立刻。”芙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艾米丽和施特菲决定继续去游泳。萨拉向后退了几步。现在只有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我的父母。我,这个被通缉的罪犯,终于要被抓捕归案了——就差当着朋友的面给我铐上手铐了。
这个场景透着一股怪异,令我感觉似乎是在做梦。
车子从长岛的尽头离开,开始了漫漫的返程之路。父亲开着车,母亲阴郁地坐在他旁边。无尽的沉默。只有每当从烟盒里抽出一支又一支香烟时,才会偶尔传出玻璃纸和打火机的响声。随着每一次呼吸将烟雾连同这可怕又由衷的叹息,长长地吐出,淹没了整个车厢。
我静静地蜷缩在后座上,心里自责着:如果你动作快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努力集中精神,试图重塑现实,期望老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象着一幅画面:我走进了海里,被淹死了,电台发布了我的死讯。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计划的失败令我难以接受,我的灵魂仿佛从现实中抽离出来,进入了另一个平行空间。车里和车外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异常渺小,而我就坐在zui远的包厢里,观看着这出人间戏剧。慢慢地,纷杂的颜色消失了,时间也静止了。
“入院。”父亲嘴里叼着烟,对着门卫室吐出这两个字。一条正式到不能再正式的车道,从门卫室通往深深的某处。入院,听到这个词我不禁打了个冷战。父亲灰着一张脸,嘴里衔着香烟,听上去像个行将伏法的黑帮老大,我究竟做了什么?
车慢慢沿着山道往上爬行,几座建筑零星地分布在一大片庄园之上。zui终,车停在了一座大得令人喘不过气的精神病院门前。这里离我家住的市中心不远,以前我经常能远远地看见这些建筑。高而冰冷的铁栅栏将整片区域牢牢围住,正常人是进不去的。我不属于这里。
“我发誓我不是认真的。”我绝望地恳求着坐在我身旁的父母,但他们只是看着对面的医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跟我父母谈着入院的事情。“求你们!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我即将滑向宇宙的无底深渊,而我的父母是我与地球连接的绳索。他们如果撇下我离开,我就完了。
三个人盯着我。无动于衷。
“求求您,求求您,求求您,求您带我回家吧。”我伸出双手,苦苦哀求着母亲。
她表情僵硬,双唇紧闭,努力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反对声。以前她总能用她那双深色的眼睛,带着恳求的眼神说服我,不要违背父母——实际上就是我父亲——的意愿。她垂下的肩膀,她的叹息和绝望的神情都在提醒我,如果我不听从父亲的安排,就会给她造成程度的伤害。从幼时起,我就常常有这样的恐惧:如果我不听话或惹太多麻烦,就可能会伤害甚至杀死她。此时,她的眼睛里失去了zui后一丝神采,仿佛死去了一般,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喜怒哀乐。
“医生让你留在这儿。”她说,把脸别过去,“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我停止了恳求,看着他们。
身材瘦小,长着一张娃娃脸的父亲不停地抽着烟。他说话轻声细语——这不是他平时的风格。他并没有表示异议,而是顺从医生对我命运的决定。但从他反常的轻柔的声音和不安的手势上,我能看出,他也很害怕。
“爸爸,求您了,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努力做zui后一次尝试。他只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意识到,没有人会来维护我,替我说句话。巨大的恐慌不可抑制地从胸膛蔓延开来,涌向我的喉咙,从喉咙里咆哮而出。
那个男医生性格专横,瘦骨嶙峋,长着一头卷曲的红棕色头发和一张瘦长的猴脸,他身体前倾表达着他的看法。他警告我的父母,说我可能会自杀,所以不应该把我带回家去,只有他们医院的医生才有办法对我进行治疗。我的父母像是瘫痪了一般一语不发,没有表示异议。
然后我看到了使我留在这里的证据:我曾在日记里写下要淹死自己的计划,被我母亲看到了。如今我的秘密正攥在医生那双干巴、僵硬的大手里。他把日记打开,看了几页,手指在一些句子上划过。他时不时挑出一些词语,大声念出来——“危险的……坏的……肮脏的……”——曾经属于我的东西,如今却从他嘴里吐出来,这是玷污!然后他翻到zui后一页,念出我计划死亡的那部分。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再也听不到他说的任何东西。
“这真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听到自己在解释,“我没病,不需要待在精神病院。”
但他们谁都不听我的。我父母签了必要的文书,然后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