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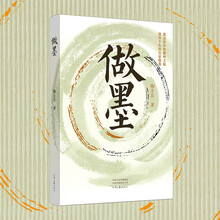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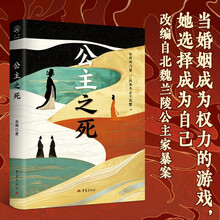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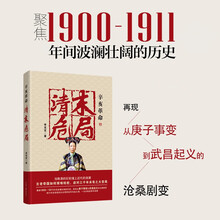





1.敦煌全景图。晚唐国势纷乱,执掌敦煌的张氏归义军外患频仍,与周边的吐蕃、回鹘、吐谷浑、龙家各族在这块土地上展开激烈争夺。从凉州、甘州、肃州到瓜州、沙州(敦煌),西北边陲的河西走廊裹挟着弥漫的沙尘,酝酿着新的变局。
2.政治阴谋史。张氏归义军首领张淮深,迎回了作为唐王朝人质的堂弟张淮鼎、张淮诠兄弟。淮鼎、淮诠的父亲张议潮是上一任的敦煌首领,兄弟二人重回故土后,张淮深隐隐感觉到自己在敦煌的统治地位将被动摇,家族团聚的表面温情背后,开始暗暗涌动着不为人知的政治阴谋。
3.中国版王子复仇记,强烈的莎翁悲剧基调。小说从始至终埋伏着一种“宿命”的悲剧感。作者将敦煌归义军历史与莎翁悲剧中与命运抗争的无力感和荒谬感巧妙融合,形成了小说的独特气质。在叙述结构上亦采用了高度凝炼的戏剧架构,有很强的细节密度感和戏剧张力。
4.中国新派历史小说的开拓之作。作品的内容融入了大量有关“敦煌学”、“归义军史”、“晚唐史”等诸多“敦煌学”的研究成果,作者花费四、五年的时间梳理史料,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展开了充沛的文学想象力。
5.人性探索的内核。不同于官场小说人物脸谱化的描述,作者的笔触探入了人物的深层心理,复活了这些历史人物的形象与心灵面貌,揭示出他们在政治漩涡中各自的真实面孔和应对方式。《降魔变》的人物各有自己的“心魔”,心魔的驱使,令他们无法看清全局,更无力挣脱宿命的纠缠。
6.敦煌题材本土文学创作的先行者。敦煌一直很热,但敦煌归义军时期的历史和人物,很少作为对象主体进入本土纯文学的创作视域。受日本作家井上靖《敦煌》的启发,作者把目光投向一千多年前的晚唐沙洲,秉承一个小说家的创作使命感,将归义军的故事带到了台前
唐末敦煌,归义军政权在大唐王廷和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夹击之中,风雨飘摇。敦煌统治者
张淮深迎回了久居长安的堂弟张淮鼎、张淮诠兄弟。当年为打消唐王朝对张氏政权的戒心,这两兄弟与父亲——上一任的敦煌首领张议潮举家入长安为王廷人质。此时父亲去世,兄弟二人回归故土,张淮深隐隐感觉到自己在敦煌的统治地位将被动摇。一场家人团聚的温情大戏背后,正暗暗涌动波云诡谲的政治阴谋……
"正午,沙碛道中,网鹰人程子迁骑着白额驴行路,后面跟了两个背箩担步行的家奴。
半里外,十来个马骑军将排开雁字队形按辔徐行,警戒着两侧和前方的敌情。前日早间,程子迁按约定与他们在肃州子城衙署前会合,便一同结伴发往甘州。军将们是去换防,他是要去甘峻山。初秋的暖阳下,原野平阔,南面,一带雪山连绵不见头尾。惟有沙砾间的丛丛棘草,被贴地吹来的微风拂动,标识了季候。近段时日,肃、甘二州都不平靖,听闻此去路途上常有回鹘人出没劫掠,一出肃州城,程子迁便在路头设酒食供祭,烧去了三张神像画纸,祈愿道途安泰。
正想着此行能否如愿返回沙州,身后传来骤急的蹄声。回头看去,一皂衣少年正打马加鞭而来。待追上他所乘的驴子,少年挺一挺身,单手收拢缰绳,调缓了行进速度,另只手轻拍青骢马的颈脖给予奖赏。从放足迅奔到缓步徐行,那匹坐骑鼻息安稳,丝毫不见疲态。
“好马骑,好身手!”程子迁不由赞道。
“出了肃州城,先去盐池河口给它洗澡,又向附近人户讨了草料喂足了。眼下这匹马精神得很,可以一口气跑去甘州!”
断然的神气超乎了年龄。一张少年人的脸,衬着随风摆动的青布裹头的巾脚,尚还显得稚嫩。
之前在沙州,刚从尚书厅堂里出来,少年就缠着他要跟去甘州看捕鹰,口中言称已请得族中长辈允准,还拉来了在使府任牙将的亲友作证。纵如此,也不能答应啊,曹家儿郎才满十三,站在马的身前,身量才刚及马耳;而且此行不知凶险如何,还是少个麻烦为好,程子迁当时便没有应承。从沙州到瓜州,一路安妥,原以为此事已了结,谁知到得肃州城里,在街市上竟又与少年照了面。彼时,少年正站在邸店门口与一群胡商叽里呱啦地谈说比划,那些是从西州和于阗来的驼商,货物刚卸下,驼儿已牵去草棚里喂料,众人正坐在场院里铺开的大毡上歇脚。少年不知说了什么笑话,又引得众胡商开怀大笑。他自己却不笑,眼光一斜溜,恰与路过的程子迁四目相对。两下并无言语,程子迁也不知该如何应付,径直就去投官家馆驿住了下来。昨日出了肃州城,路头未见少年踪影,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所以,此刻少年的出现并不让他惊讶,反而让他接受了事实。
于是没好气地怼了一句:“还是让军将们在前引路比较好。免得豺狼前来惊扰。”
“这个不怕,正好一并射杀了。”
少年拍了拍腰间那个装着雕鸰箭的胡禄箭囊。箭囊外缘镶了金丝线,泛着碎光。因为体格尚小,背在身后的那张画被弓显得尺寸奇大。
“我说的是豺狼样的人。”
少年眉宇锁起,一时不语,抬眼凝看前方半空里的一缕细云,半晌才问:“此番定要捉得青骹鹰幺?”
“是呢。尚书吩咐要捉得,便一定要捉得。”
“为何非得这鹰?别地出的鹞隼便不行?”
“河湟一带,只甘峻山的青骹鹰最是神俊有名,头圆如卵,胸阔颈长,筋粗胫短,翅厚羽劲。驯养得法的话,最宜做骑猎伴侣。昔日太保奉命归阙前,就曾将四联青骹鹰作为上品贡物送往长安。如今,尚书做了沙州使主,便也要送。”
“为求得旌节,尚书也是煞费苦心了。”
程子迁不接话头,转而嘱告少年道:“仁贵儿郎,到得甘州你便返程吧。”
“不,我要学你网鹰!”
语气很果决。
“好好学士郎不做,学网鹰做甚?再说,捕鹰哪是一两天就能做定的事,多半得在山里守上十天半月呢。”
“十天便是十天,半月就是半月,我若亲眼见识了,准定回返就是!”
言罢,少年两腿一夹,手下起鞭,那青骢马便纵身向前驱奔,蹄足一路打出烟尘,很快就与前面开路的众军将会合了一处。他正值茁壮年纪,志在驰逐,眼见一切都新鲜有趣,浑不知前路的凶险变数。
日昳未时,即将抵达建康军的屯台废墟,程子迁估算余下的里程,入晚应可到达甘州城了,只不知那边情形如何。前几日在使府,临出发时,正好听得几个内宅押衙议论甘州军务,尚书张淮深正打算分遣游弈使白永吉、押衙阴青儿出巡探查;而此前不久,原凉州都防御副使翁郜刚刚受王廷敕令,又兼任了甘州刺史。虽说只是遥领,并未分凉州天平军官兵进驻,但听说翁刺史这几日正在甘州督修雉堞、堡楼,沙州派驻的军将和各家部众都暗行抵制,双方彼此抵牾不断。
之前停宿官驿时,肃州防戍都营田使索汉君和县丞张胜君特意前来问候,询问了沙州使府情况后,两人正色告诫说,要捕鹰,眼下恐非适宜时节,近来甘州、凉州一带闹乱不休,回鹘游骑四处出没,若是出了肃州境,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思量来思量去,决定让十二名预定换防的军骑提早两天动身,正好一路护送到甘州。
这懵懂少年,哪知晓前程后路的这许多关节?
暑夏尾梢才过,日头高悬后,地表的热气渐渐蒸腾上来,令人头眼发昏,程子迁伏低头,禁不住打了会瞌睡。可是,他很快就被后方另一阵紧促的马蹄声给扰醒。回头看去,只见十数匹马骑正驱近前来,当首领骑的,正是发送他上路、兼管了使府鹰坊的押衙张文彻。
这又是什么情况?莫非尚书一转念,又派人要将我召回?
这拨人马抵近后并未放慢马行速度,张文彻经过身边时也没有勒停坐骑,只略提马鞭唤了他一声,程子迁刚要开口询问,却听他大声呼告:“你且前去甘峻山,我等另有公务,就此别过!”
跑出二十步以外,张文彻又回头喊:“给我看好曹家小儿,莫让他给野狼叼了去!”
程子迁不由提起手中小鞭,催驴起步。两个家奴见状也提上一口气,加快了脚步。
等赶到屯台,见曹家儿郎和换防军将正停在那里饮马歇息,并不见张文彻那班人。
“张押衙他们奔甘州去了?”
仁贵应答:“捕鹰博士,押衙不是去甘州,是直去邠州!”
张文彻一行倒是在这里停留了片刻,由是仁贵和军将们都得知了那个重大消息:之前尚书派往京城请节的宋输略使团七人,前月与西归的回鹘使结伴,自长安返回,路经邠州时,他们遇到了返回沙州途中的淮鼎、淮诠郎君、太保娘子、家累仆从、军将、常住奴客、入京僧等二十人。宋输略等被告知,两位郎君路上曾遭贼,被党项人劫去为人质,幸亏有随行军将逃脱,及时向邠州节度使求救;邠州使主因与故太保有交谊,不敢怠慢,连忙派人至党项部落将人赎了回来。目下郎君等人就暂停在邠州,准备随凉州嗢末使一同返程,只因之前衣箱什物丢失甚多,一时发赴不得。
“宋输略他们现在何处?”
“还在凉州,他们遣出了一匹快骑,昨日一早刚到使府报讯!”
程子迁不由咂舌,这确是个大事件:自两位郎君入京陪侍太保,到如今返沙州,前后已有十五年,当初的垂髫小儿,如今定已长成青年儿郎了。对沙州四境的民众来说,这与太保本人归乡同等,实在是让人喜不自胜;虽然人事可哀,归阙入质的太保张议潮十二年前已在长安去世,敕葬于京城素浐南原了。
屯台残壁外有一口泉井,程子迁令家奴汲水上来,和两名家奴各取一瓢饮尽,驴子栓在柽柳低枝上,很知趣地站定不动,只偶尔摇一摇尾巴。程子迁心疼这匹跟了他多年的老驴,也让它解了会渴。此时他心里多出一桩焦心事,觉得必须改变行程计划了。
“仁贵儿郎,这回定是要看捕鹰?”
“当然了。”
“那么,不随军将们走官路去甘州了,我们直截去甘峻山山口。若我所判无误,这个时节该能捕到名贵的青骹鹰!”
“好!”
少年爽快地响应。本来,四人去甘州城也只是暂歇过宿,现在听闻程子迁绕过这一节,直接带他去捕鹰现场,他有点兴奋难抑了。
决定已下,就开始点检装备。过夜露营的长行帐有了,干粮吃食已备足,生火的火镰有了,捕鹰的绳网在家中早就编织好,此行上路前尚书发给的关牒文书也在。所有东西一一齐备,就不知道老天爷有没有给他们预备足够的运气了。
军将们听说他们要绕过甘州往东北方向直行,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送了他们两把新开刃的短刀防身,入夜后的山地间多有野兽出没,还是小心为好。而他们乐得轻松上路,若一路急驱,入晚前能赶到甘州,正可邀了军中伙友酒食饱餐一顿。
这队人随后分作了两拨。军将们各整鞍鞯上马,因为没有了后顾之忧,此刻已改换为纵贯队形,将头领骑,众人跟随,这就往甘州城方向驰去。网鹰人这一伙离了官路,往山口行进,两名家奴在前引路,程子迁和仁贵儿郎一个骑驴一个骑马,两人并辔而行,一路无话。
日暮时分,四人来到了山口前。转上一长段陡峭难行的碎石坡,再通过一道隘口,地面突然抬升,顺着两边山势向远方延展而去的,是一片展阔的山间草场。别样的天地间,金色的夕照透过薄云,将这里点染得如画一般。少年此前已按捺了许久,一入此境,立刻欢叫起来,座下那匹骏骑也来了精神,奋足向前驱奔。
程子迁没有叫住他,任他随性撒野。
再行一个半时辰,于太阳落山之前,他们到了“小昆冈”,在坡下石壁有泉眼流出的地方,觅得了一个避风处露营。虽是初秋,入夜过后还是寒凉,在那里,他们四人可以安稳地睡上一宿。
两个随行家奴自早间起就在赶路,腿脚已酸累,到此才得歇息,一人两枚胡饼吃下就早早睡下了,不一会儿,帷帐里就起了鼾声。仁贵儿郎安顿好马儿,四下里走了一圈,到天光暗下就回返了,行了一天路,人已困乏,他钻进帐里倒头便睡下了。
这晚,程子迁却几乎没有合眼,裹一条厚毛毡,背靠着石壁,就这么半躺半坐着。栓在身旁的老驴不时挤挨过来,将他当成了可信赖的伙伴:远处不时可以听闻野兽的低嚎,这时节,狼虽然很少成群出动,但仗着草深叶茂,常会有单匹公狼夜出游弋;帷帐前后虽然点了两丛篝火,但还是留一个人警戒为好。
头顶的黑天里,缀满了无数星粒。
前次在灵图寺听讲经,座间休息时,唐和尚恰好曾与在座的优婆塞们说起占星学问。据说周天星宿的位相运行,暗合了地上人间的运命变数。果真如此幺?西南方,那披发半裸、手持长刀的罗睺星神,正北方,那背插宝鞘剑、发髻如盘蛇的计都星神,此时就隐匿在这星河中?程子迁不能辨识,但他相信,天上的神煞确有真实无疑的威力。于是,在这两个方位各选了明亮的一颗,他默默祝祷起来,一求捕鹰顺利,二愿神煞及其灾殃,能远离沙瓜全境。
此行正好带了绘有炽盛光佛和诸曜图像的神像图卷。沙州出发前,程子迁专程去灵图寺与唐和尚告别,和尚特意借与他路上方便使用,月半时如法供祭,有辟邪之功效,可保出行平安云云。看眼前月相,明日正是供养神煞的时节。不如此,心中实在不能安定。
驴儿打了个响鼻,尾巴却不摇动,是已睡着了吧。月光下,它脊背上的皮毛看去如一匹灰白匹缎。程子迁伸手轻抚它的颈脖,皮毛下的血肉正与他有着同样的体温,虽然驴儿并没有给他回应,他却分明觉得一件显明的事实:自己正随同这头驴儿一起老去。
许久,石壁上方的某处,传来了夜兽走动的声息。
不是狼,是不知名目的兽。蹄足踏地,不时碰击着小块碎石,似乎是野羚羊。他放心不下,丢开毡毯,立时挺身站了起来,抓起近手边的短刀,从篝火堆里捡起一支火把,绕过石壁,爬坡登上了“昆冈”上部的石台。
果然是羚羊,火把投出的光圈里,它站定了不动,正盯视着自己。那双瞳目发出暗黄的眸光。
程子迁恍然觉得在做梦,因他分明听到那匹羚羊在对他说话:
有蛇!有蛇!
低头看地面,月光照映下的石台一片枯白,就近并没有蛇。可是,那声音还在呻叫,时断时续,而且,现在他听出了是谁的声音。那是太保!可是,这怎么可能!?在山间旷野中,怎么会听到故去太保的语声呢?这绝无可能。
再抬眼看去,他真真确确看到了太保,场景却恍然移到了太保入质长安后所居住的宣阳坊邸宅。太保身披甲胄、头戴兜鏊,就站在庭院中,两手扪胸,面状甚苦楚,他不停地在叫唤:
有蛇!有蛇!有蛇!
程子迁浑身僵住了,前进不得,后退亦不得,地上似有一双巨人之手,攫住了他的两脚。他想不出该说什么慰解的话,嘴巴张结着。手一松,火把落到了地上,四周光影乱动;待重新拾起,再看前方,太保的脸却模糊了起来,如一罐奶浆倒入水盆中,慢慢地变浑又变白。
幻像消失了,眼前复原了一匹羚羊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