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我在考察了这484个择偶案例后发现,爱情也发生在介绍型婚姻中。这印证了Victor DeMunck在斯里兰卡的研究中应用的“爱情牵线”的说法。 在集体化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为上一代人如果没有媒妁之言,在情感表达方面要困难得多。在介绍型婚姻的情感发展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在同村人结婚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都是男女双方在媒妁出现之前本来就认识。这时,媒人往往充当两家讲条件的中间人。在一些情况下,媒人不过是请来走过场,因为当事人已经偷偷自己定了婚,有时甚至两家父母都已经讲好了彩礼条件。一位好友告诉我,在他父母找来媒人之前,他和对象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都是村里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女方是演员,男方演奏乐器。在宣传队和大伙混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之间觉得轻松随意,可私下到了一起时却感到紧张。这位朋友说,姑娘太封建,不敢跟他更接近;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姑娘却说,两人在一起时,他傻呼呼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她说点贴心的话。这两人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所以农忙期间就没法见面,而他们在分开期间才意识到他们都相互想念对方。于是,1968年农忙完毕,男方家就请了媒人。在这类情况下,双方在订婚后马上就密切往来,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已经有了明媒,就有权利放任一点感情了。
第二类情况是,双方在有人做媒之前并不认识,而是在订婚后才谈起了恋爱。这往往发生在与外村人特别是远地方的人订婚的情况下。比如1975年,某个下岬姑娘和35公里外一个村子里的青年订了婚。双方在初次见面之前完全不认识。那次见面是姑娘的远亲安排的。女方后来告诉我说,第一次见面时她对对方毫无感觉。这姑娘的父亲几年之前就去世了,她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家里境遇困难,希望她赶紧结婚。她在与对方见了三次面之后接受了婚事。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到男方家里去过四次,每次都呆了几天,男方也到她家来了三次。他们还一起到哈尔滨照了订婚相。姑娘在村里的好朋友都发现,每次她和未婚夫见过面之后,他们的感情就又进了一步,因为每次她都非常兴奋,在往后几天里总是不断地提起未婚夫。村里人都说,她那么想结婚,在婚礼那天和娘家告别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像其他新娘一样象征性地掉几滴眼泪。后来她对我说,她根本挤不出眼泪来,往手绢上撒胡椒面也没管用。她告诉朋友,自己是那么想念他,巴不得马上离开。村里传说,她在订婚不久后就和对方有了性关系,于是也就开始了两人的热恋。15年后,当我在1991年做调查当面问她村里人的说法是否有根据时,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了起来。我说你这一笑就算是肯定,她也还是继续笑而不答。我对她说,你可真够浪漫的。她却不以为然,因为当年的同辈人都这么做。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订婚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原来早在70年代就已存在了(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讨论)。
订婚后发生恋情的事不仅出在隔村男女之间。事实上,下岬本村不少男女青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一对在1976年订婚的人至1998年才告诉我,虽说他们两人一起在试验田里工作,在有朋友牵线之前他们之间从来不多说话。不过在订婚后,他们越走越近,因为他们有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便利条件。我问他们,这种情况是否因为70年代的年轻人还很害羞,经常避免和异性接触。他们不同意。妻子说,甚至在1998年还有类似情形。有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和书记的女儿订了婚。女方是学校的民办教师。男方的母亲觉得与书记结亲非常荣耀,给女方付了高额彩礼。当儿子的开始时并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是顺从母亲的安排。不过他和姑娘在订婚之后日益熟悉,结果他成了尽人皆知的痴情汉,心甘情愿地为姑娘做任何事。他经常陪姑娘到学校上班,帮助她清理教室、收作业。有的小学生搞不清楚,对父母说他们班上有两个老师。结果这成了村里的笑话。
最后,即使在一些完全由父母作主的婚姻中,双方也有可能在订婚后才发生爱情。有趣的是,在我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3个人甚至觉得自己的父母干预得有道理。90年代中期出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个姑娘很聪明,上了中专,毕业后却面临困境,因为她在班上交了男友,到毕业时两人已经难舍难分。但是,他们毕业后被分回了各自的县。如果她继续这段关系并最终和男友结婚,就必须远离父母,搬到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的男友不但家里很穷,而且要供养父母,无论是现时的家庭责任还是将来的经济负担都很重。自然,女方的父母强烈反对这桩婚事,父母与女儿之间发生了许多争执。她的父亲最后设法帮她在县城附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又通过城里一个有权有势的干部给她介绍对象。经过一段情感反复,她接受家里的劝告,和男友分手并与这个新对象发展了关系,最后很高兴地结婚成家。数年以后她对我说,幸好她父母干预,才没让她干出傻事。不过她又说,最终还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她决定要和第一个男友结婚,谁也没法拦住。而她的父母不过是给她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用他们的人生经验说服了她。
择偶理想的变化
老一辈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很少出现婚前性关系,因为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而订婚夫妇除了在父母眼皮底下之外也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另外,那30年里的意识形态也不容许有那种行为。无论是在自由恋爱还是在介绍型婚姻里,婚前性关系都是个很敏感的内容。我自己70年代生活在下岬时,就经常听到已到婚龄的朋友谈论起新娘是否处女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在调查这个题目时,有好几个中年人谈起他们年轻时规矩之严。有个男人悄悄和一个姑娘谈恋爱,最终在1967年结婚。这人回忆说,他们当时总是在晚上到野地里去呆上很长时间。他碰过她的身体,但是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因为如果女方怀孕的话,两人的名声就完了。
一般情况下,我在调查时总是先搜集最近的资料,之后再沿着发现的各种蛛丝马迹往前追寻。在调查婚前性关系时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991年,我在当地的一次婚礼上第一次触及这个题目。新娘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而村里有些人并没有对此表示大惊小怪,这令我印象很深刻。1997年时我仔细研究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从中发现了婚前性关系普遍的程度。不过,直到1998年,我才碰到一个愿意详细讨论这个题目的村民。
在199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与50岁的老梁讨论1949年以来夫妻关系的演变。老梁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是我的重要消息来源。他说,自从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睡在一起。他爹除了回来吃饭睡觉之外从来不着家。即使在冬天农闲时,他爹也是到外面去呼朋唤友。老梁的姐姐嫁给了个聋哑人,他无法想象姐姐怎么能够一辈子没声没息地和一个人呆在一起。说到今天的年轻人,老梁摇了摇头,感叹说时代也变得太快了一点。
据老梁介绍,现在的年轻人订婚之后,每个姑娘都会在男方家里住上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再一起去照订婚相。显然,照相前住一个星期这道手续是80年代才出现的。多数情况下是姑娘住在男方家里,因为男方父母照例将这看作是敲定婚姻的办法。不少未婚夫妻在这期间都有性关系。老梁估计,80年代中期以前有大约1/5的人这么做,80年代末期上升到1/4,90年代后期就已经到了1/3。他还说道:
其实我家也这样。我们大小子订婚那天,他问我老伴是否能让未婚妻在家里呆上两天,因为她打算帮我们干点活。我们都很高兴,觉得姑娘会来事儿。姑娘的确很会干活,她和我老伴、儿子一起下田。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可是,第二天清早,我却发现她没有睡在房子里,而是到库房里和大小子睡在一起。我们老两口都感到害臊,不过后来老伴想通了,说这样媳妇就不会把儿子给甩了。我相信老伴的话,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明白。所以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甚至都没有给她在屋里铺床,而她和我儿子吃过饭后就不见了。这些年轻人真有精神!整整辛苦了一天,他们还有玩的功夫!要是在过去,我可没脸告诉你这个,不过现在人人都这样,也就无所谓了。
老梁又说,他的二小子和三小子分别在1987和1991年订婚,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简直成了家庭传统了。他一面开着玩笑,一面却小心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有好几个全国性的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中的婚前性关系在全国各地都大大增加,所以他的例子并不特别。比如,有个调查发现,24%的农村受访者表示可以允许订婚男女之间有性关系,或者并不将婚前性关系当回事(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1993:53)。80年代末另外一次调查则发现,41%的男性与30%的女性认为婚前性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完全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婚前性关系发生在未婚夫妇之间时,极少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Zhao and Geng 1992:10)。 显然,在60年代曾经是禁忌的婚前性生活在90年代已经流行于订婚夫妇之间。听完之后,老梁显得轻松了许多,我们又开始谈起美国60年代的性革命来。
虽然不像老梁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开诚布公,但村里其他人也承认未婚夫妻间的性关系越来越普遍。许多年纪大的人开脱说,这些人反正是要结婚过一辈子的。而一个青年人争辩,如今开彩礼单就是结婚了,所以睡在一起本来就应该。不过,同一时期内解除婚约的案例却不断增加。例如,从1994到1997年的42对订婚男女中,有5对解除了婚约。其中4对是女方解除的,而大家知道这其中至少有一个姑娘和未婚夫有过性关系。
为探究未婚夫妻婚前性关系的普遍程度,我特意分析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对比1979年以来每对新婚夫妻结婚与头生子出生的时间。在1991至1993年结婚的49对夫妻中,有13对在结婚8个月之内生了孩子,其中10对的孩子是在7个月内出生的。所以,即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这期间的新婚夫妻中至少有20%婚前有性关系。而且,并不是每个有婚前性关系的妇女都会怀孕,所以实际比例肯定还要更高。
村里人怎么看待这一变化呢?正如老梁说过的那样,多数人都把这当作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许多当父母的在未婚媳妇上门时也给儿子提供方便。结果,有好几家的父母因为害怕生出“五月鲜”的孙子只好仓促举行婚礼。有个比老梁年纪更大的人回忆说,他和妻子恋爱时什么也不敢做。而他在1990年发现大儿子的未婚妻怀了孕,只好赶紧让他们结婚。按照他的说法,事情虽说是紧急,但最终还是有惊无险。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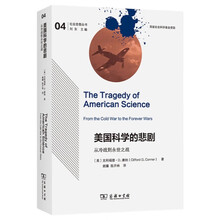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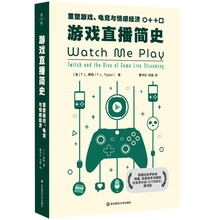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zui好的民族志写作。他花费了数年时间与村民们共同生活,并分析他们的生活状态。他把私人生活研究放在了个体性和家庭联合体重要性的经典讨论之中。他生活过,他做到了,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黛博拉·戴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阎云翔首本书,《礼物的流动》于1996年出版后,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了该领域。阎教授的第二本书《私人生活的变革》更清晰地表现了他在这本书所展现的才华。事实上,《私人生活的变革》作为《礼物的流动》这一书的同系列著作,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部关于丰富而独特的村庄民族志。那里同时也是阎教授成为人类学家之前花费了15年观察、生活过的村庄。
——《China Quarterly》
优秀的研究,它清晰地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家庭生活的变化图景,而从中,村民们的内心道德世界和情感生活流露着些许微光。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在这本精心研究和高度原创性的书中,阎教授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民族志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捕捉农村社会变化背后的多层微观性因素的能力。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