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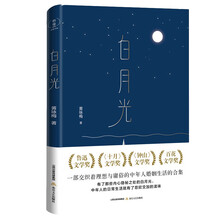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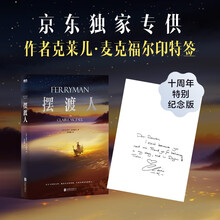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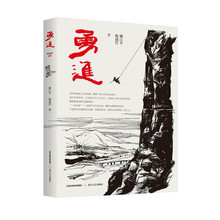




◆ 继2016年《北鸢》横扫各大文学奖项、图书榜单之后,葛亮推出的全新力作。甄选近年来创作的具有悬疑感中短篇小说,集日常与宏大于一体,必将成为新的经典。
◆7个关于你我身边平凡人的故事,7个庸常生活之下的意外结局。剥落传奇的外衣,以残酷的真相洞穿生活温情脉脉的表象。他们你我身边的平凡人,带着巨大的秘密生活着,下一秒,这秘密将会石破天惊;这一刻,却如同风暴来袭前的宁静。
◆葛亮被海外评论界誉为“当代zuiju大师潜力的小说家”,在温暖慈悲的民间书写之中,包含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尽隐没于日常中的现代传奇,更写尽人生转角时的荒唐与无奈,于无声处听惊雷。人间烟火如涓涓细流,也会被卷成旋涡,众生回响。
《问米》甄选了近年来葛亮创作的7篇具有悬疑感的中短篇代表作。在悲悯的民间叙事中,是人生的风姿百态,也是命运的横强与无常。娓娓道来之下,总能看到些许平庸又熟悉的样子,他们面目模糊、泯然众人,却被巨大的秘密裹挟着,在下一秒堕入深渊。自认聪明的,以破釜沉舟的信念,步入迷障。更多的人则在观望,终于亦步亦趋。
他们是旅居越南的通灵师,是隔壁的奇怪邻居,是擦肩而过的路人,是我,也是你。
面前是一片浩浩汤汤,自时代的跌宕,自历史深处的幽暗,或自个人的痛快与无涯苍茫。彼岸处,刹那间似有一两点星火。不明亮,但足够暖。
问米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题记
这是我zui后一次见到阿让。
是的,我需要解释一下,我如何与他相识。
这涉及我的工作性质。怎么说呢,我是一名摄影师。当然,这是我的副业。我没有兴趣说我还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因为无可圈点。可以叫作公务员。但其实,只是在殡仪馆里做一些迎来送往的事情。送生也送死。
所以,我会重视这份副业。它让我觉得自己有用和高尚一些。当然别人未必这么看。毕竟,我是个自尊心很容易膨胀的人。
问题在于,摄影师也并不完全是个理想的职业。因为业务范畴广泛,我替人拍过结婚的Video、拍过宠物,也偶尔为了紧巴的日子,跟踪过一两个明星,拍过他们的闺中秘事。但我要说明的是,我是个将兴趣和事业处理得壁垒分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没有原则。
因为我的原则,我才会和老凯相识。或者说,我才愿意搭理他。
老凯的丈母娘死了,在我们的殡仪馆火化。
那天丧礼,租用了我们zuida的一个厅,极尽奢华。排场摆得很足,包括全程录像。我对这一点很不解,毕竟不是什么伟人的遗体告别仪式。录像的意义,除了让亲友在痛定之后再思痛之外,难说还有什么历史价值。照片上的老太太十分老,眉目并不舒展。不是颐养天年后的寿终正寝,听说是胃穿孔死掉的。这就让整个事情变得勉强。前来吊唁的来宾,他们在礼堂外面,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一个大肚子的男人正在打电话给股票经纪人,面部表情丰富。他身旁的女人掏出化妆棉,将嘴上紫黑色的唇膏一点点擦掉。擦了一半,又不甘心地抿一下嘴。更多的人,是百无聊赖的样子。
的确,即使从专业的角度,我也觉得准备的时间过于漫长。依客户的要求,将雏菊、康乃馨、天竺葵、菖蒲和薰衣草一层层摆成俄罗斯套娃一般的心形,确实需要时间。何况这个方案,是在追悼会开始前两个小时才告诉我们的。而那两只棉纸扎成的仙鹤,在前一天晚上受了潮,怎么都摆不出雄赳赳、气昂昂的派头,也实在叫人郁闷。在所有人都忙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只有一个哥们儿,叼着烟扛着摄影机走来走去。
我说:“哥你差不离行了,这么走我眼晕。”
他轻蔑地看我一眼,说:“什么叫差不离,没个合适的机位,拍出来效果不好你担当得起?”
我就闭嘴了。他是客户从电视台请来的摄像,以掌镜一档大型相亲类节目而闻名,所以拍活人还是蛮有经验的。
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人生没有NG。”
这可吓了我一跳,这么有哲理的话,搁我们这儿就让人起鸡皮疙瘩。我干笑着走开了。
这又忙了一阵,我正训一个刚来的小姑娘把“音容宛在”的联给贴倒了。
老李过来慌慌张张地说:“那哥们儿不行了!”
我说:“谁?”
老李一指,“摄像。”
我一看,那哥们儿脸煞白,捂着肚子,豆大的汗珠可劲儿淌。我走过去,问他怎么了。
他看我一眼,嘴唇直发抖,说:“早上喝了碗豆汁儿,刚跑了三趟厕所。得,又要窜了。”
看他那熊样,我心想这还真是英雄气短。我说:“赶紧地,回家歇着去吧。”
他为难地说:“那这个怎么办?”
我说:“不拍了呗。”
他说:“那不成,订金都收了。”说完脸色一阵发青。
旁边老李就说:“马达,你不是摄影挺能耐的吗?帮帮这哥们儿。”
我说:“李叔,我哪敢来班门弄斧啊。”
哥们儿眼睛一亮,说:“那谁,你摇镜特写什么的,都会吧?”
我冷笑一下,心想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这儿臭显摆。就说:“不会。”转身就走。
“唉……”他痛苦地抬抬手,说,“得,就你了。”
要说人在这镜头底下,都挺能装。该肃穆的时候格外肃穆,号得也一个比一个带劲儿。孝子贤孙们赛着哭天抢地,生怕日后翻了带子出来,被人咂味说不孝而遗臭万年。晚上,我一边看录像一边想,到这时候真都是影帝影后哦。这时一中年男子经过,突然抬起脸,歪过脑袋看一眼镜头,笑了。他这一笑,可把我吓得不轻。等回过神来,赶紧倒带子再看一遍。还真笑了,笑得亲切和蔼。这大半夜的,我心里“咯噔”一下。我觉得,他这笑,是笑给我看的。
一周后的中午,我正在办公室打盹儿,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很沉稳的男声。
他说:“小伙儿,听你们领导说,老太太那录像是你拍的?”
我说:“嗯,您哪位?”
他说:“我是老太太的女婿。”
我说:“哦,我就是一带班跑龙套的,拍得不好您见谅。”
他说:“不,你拍得很好。构图、氛围的感觉,都把握得很棒。”
我心想,好嘛,还构图,机位基本就没动过。
我说:“有事您说吧。”
他说:“我想找你合作个项目,你有兴趣吗?”
我想一想,说:“哦,您细说说吧。”
就这么着,我见到了老凯。当我见到这中年人,一眼认出他就是在镜头里微笑的男人。我当时有不祥的预感。他冲我亲切地笑了,笑容与镜头里一样,然后对我伸出了手。我和他握了手,他的手心是湿热温暖的。
“我是个风水师。”他说,“我找你呢,是想拍一个通灵人物的纪录片。”
我一听,想都没想就摆摆手。
我说:“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我没兴趣。我是国家公务员,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从专业的角度来说,死者为大。走都走了,何苦接回来再折腾一程。”
他也不恼,笑得更亲切了。
他说:“你这么说,还是对鬼魂不够了解。鬼魂是什么?从科学的角度说,鬼魂实际是某种磁场。你得承认磁场是唯物的东西吧?”
我不置可否。
问米
不见
罐子
鹌鹑
朱鹮
龙 舟
竹奴
后记:刹那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