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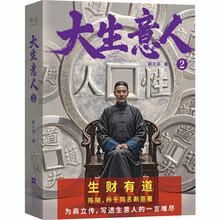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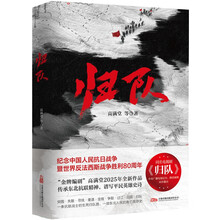






如果说在这越来越坏的世界里,注定有一场残忍的败仗。那你打还是不打?
正如黄丽群为《大裂》所做的序言《暗室明眼人》中所说,“胡迁的小说集《大裂》里,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作为格格不入的一代,现阶段的社会和我们现在的生活总有一种莫名撕裂感,胡迁用爆裂的文字写作,用层层意象铺设出一条条离开“这里”的路,我们或许身处这里,可总要知道离开这里很远的路在何处。
海报:

我要看清楚那头大象为什么要一直坐在那儿,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困惑。/《大象席地而坐》
上帝经常会让你一无所有,再给你一点甜头,这点甜头就是在闭上眼睛的一瞬间,让你错觉拥有了很多东西。/《漫长地闭眼》
我们始终坚信荒原上的藏宝图,能指引我们挖出黄金,走向黄金的大道,那个入口感人肺腑,低吟浅唱着通向云层的歌谣。/《大裂》
……
《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一本伤害之书。
15个中短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
暗室明眼人
黄丽群
说起来我跟胡迁有两面之缘。2014年他来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学程结业功课是改编一篇短篇小说,因其中有我的作品,便被主办单位找去开了场两小时的短会。
匆匆来去,印象里就是一群敏思闪烁的年轻人,我昏头昏脑,瞎说一场,会后却收到胡迁认真写了 e-mail 过来讨论,态度大方,应对有古典的节度。他回北京后,彼此也偶尔通信,某日他很客气,先问能不能寄作品给我看,我答复了,才发过来。老实说我原先没有什么预设,读过却着实吃惊:他似乎太没有自信了,这是很好的小说,干净,浑然天成。他对文字这古老介质的驾驭能力可谓天造地设,每个字是似有若无的纤维,每段句子是气孔绵韧的密丝,分分寸寸,行若无事,在你意识到以前他已捻出漫长的线索,在你意识到以前嗖一下已被卷了进去。
他不像许多人克制不住以其为鞭的诱惑,也不要喧嚣抽打读者,制造浮夸的声响与迹象;他沉默地缠缚,沉默地收敛,丝线一点一点绞紧了勒深了,心仿佛都要裂了。
但写出这样小说的作者,到底是那群均貌似明朗的学员里的哪一位呢?……两年间我一直没搞清楚,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因为这未免也太少根筋。
直到2016年他以中篇《大裂》得到台湾的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因领奖再来台湾,有机会请他喝个咖啡(饭则被小说家骆以军抢去),才大概算认识了,是个从整体到细节都很清爽的年轻人,言语简洁,带冷涩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攒的弹珠。人不似其文。我一下子有点懵,无法理解他的写作中为何会出现那样极致的伤害性,就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会写这样的小说啊……”
真是愚蠢的问题,这甚至是我自己作为写作者最讨厌遭遇(并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的问题。但胡迁恳切回答。其实他本人的质地能够说明很多:一个心灵如精密仪器的青年,多半会因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时时震动,为了不被毁损,难免必须长久出力压抑著位移,那压抑的能量终要在他的写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绽了。书名“大裂”两字或者是无意识的流露,却也收束出胡迁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在风景,他的小说中每一抹淡到几近透明的草灰蛇线都有繁复意象,语言平静,一丝滥情自溺的赘肉都没有,落在地上,望似滚珠,若去拈起,才发现是水银,凝重荒暴能让人从头裂开到脚,剥掉了一身的皮。
胡迁学的是电影,他非常擅长利用人物的对话,及对话间不可见的细微波动,如牙科探针般挑出生活的疼痛神经。然而我以为影像训练又不足够解释他短篇小说的魅力:这些作品的结构有时其实不太工整,但那当中的强烈能量让技术问题的刮痕甚至不让人感觉是瑕不掩瑜,而莫名显得那歪斜是一种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了。
许多创作者,终其一生在追求这种无言中说动的境界,他羚羊挂角地恐怕自己也没发现地轻易做到。这样想想我都觉得真是挺可恨的 。
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写作一事之诡谲,虽存于文字,又不存于文字,更在如何魔术般介入现实中肉眼不可见的微妙间隙,胡迁带著他松德哨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这本小说中一次又一次演示著吹毛断发的天分。《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本伤害之书,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我可以想像它会被什么样的读者排斥,让什么样的人不安,我可以想像会有什么样的人因在这其中求其安慰与修饰不可得,而感到不满。也可以想像它是多么地不符合某种主流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大义。
但我想好的创作者,本来也都是这样的。生命如拥挤的暗室,他坐在当中,视线炯炯,眼中没有蒙蔽,什么角落都看见,不怕痛地指出来,也不因此就佯装或者自命是谁的一道光。至于救赎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担与碰撞,若主张创作者必须为此负起责任,就是一种贪小便宜。
我不敢妄言自己多么了解胡迁及其作品,但承他不弃,这两年他陆续写了什么,会发来给我看看,有时我们会在信中聊几句,有时我工作焦头烂额难以为继,他也不介意。这当中的《大裂》《一缕烟》《荒路》《漫长地闭眼》等都是我反复再读的秀异之作。然而令人比较困扰的恐怕在于,他的作品,不管放在哪一条脉络下,哪一种已知的模板里,都显得不易解释,像块在视野中任何位置都无法嵌合的拼图。要描述为格格不入,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我以为,也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头角峥嵘。
离队少年
王小帅
在西宁的青年导演论坛上,胡迁的宣讲引发了哄堂大笑和鼓励的掌声。事情是这样的,主持人介绍完下一位宣讲人后特意提了一下这位导演比较害羞,万一中途有什么情况请大家谅解,然后胡迁就上台了。大大的脸庞,头顶着年轻人舍不得剪的厚重的长头发,黑框眼镜后面目光迷离,像是没有睡醒。他的剧本项目起名“金羊毛”,来自于某个希腊神话传说。他一开口就暴露了他在背稿,他的眼神对着前方的虚无背了开头的一小段之后,眼睛突然看向台下的听众,然后就顿住了,那一刻整个空气也顿住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只是这个台上的年轻人突然石化了,一动不动。等所有人反应过来已经十几秒过去了,哄堂大笑就是在那一刻爆发的,随即是理解和鼓励的掌声。后来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也说什么都没发生,就是空白了。后来的宣讲这个人严重跑题,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了漫无目的的描述希腊神话上,而且就这个希腊神话也没有讲清楚,并且接连又顿住了几次。作为当时台下的评委,我知道这次的所有奖项恐怕和这个年轻人无缘了。但奇怪的是,尽管如此,这个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所有宣讲人中最深的。
看到“金羊毛”的完整剧本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了,这回轮到我“顿住”了。整个故事和文字竟散发出一股迷人和离奇的氛围,那种空气中弥漫的失落和伤感不用影像,文字已经抖落了出来,完全和他在台上絮絮叨叨的古希腊神话失之千里。不过,正是这样的间离和反差倒是十分的契合了那天在台上石化了的年轻人的气质。我立刻约了他再次见面。不见不要紧,一见吓一跳。除了相同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同门背景之外,毕业没几年的他其实已经是一个作家了,中篇小说集“大裂”刚刚在台湾出版,还拿了个什么奖。问他为什么会这样?他的回答是因为当不了导演,无聊。他的控诉是这样的,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拍了一个和他的文字气质高度一致的短片之后被导师批评太艺术,让他模仿韩国人那样拍商业片,他照做了一个,混杂了黑色、动作、凶杀和悬疑,拍完的结果就是对自己的投降出离地愤怒起来,愤怒的结果就是把自己关起来,写字。因为有了宣讲那次的阴影,每次听他说话都十分担心他在某个时刻再次顿住,当然这样的情况没有再发生,尽管没有再发生,但他时常的沉默和话语间的游离感还是让人产生联想,就像一个有着满腹心事和幻想的孩子,因为没有办法像常人一样表达自己而被人误解,然后他就更深地回到自己的世界,让人担心的是,他有那个世界吗?这样的担心很快就解除了。
解药就是他的文字。像他的剧本一样,读胡迁的小说,其中的人物、行为、故事有一种天然的不确定和游离感,他的文字更是紧紧地契合着这个气质,制造出让人惊喜又沮丧,真实又荒诞的氛围。这就是他的世界,一个文如其人的世界,一个时常会什么都没有发生而顿住的世界,那个世界空白,游离。以他的年龄,能如此熟练的控制文字、句式和情绪的年轻写者实不多见。然而年轻也是一把双刃剑,刺向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容易暴露自己的软肋,胡迁的年龄正好是这个时候。剑的一面是未被污染的想象力在年轻的血液里驰骋,荷尔蒙和精液的味道又浓又足,他的文字可以肆意挥霍它们,一切都可以原谅,一切也可以浪费,三天一个中篇就像一个年轻人夜夜勃起的生殖器,随时都兴致勃勃。剑的另一面也正像这只随时都兴致勃勃的生殖器,充满了骄傲的生命力却一时找不到格斗的对象,所以有时候他要自己解决它。胡迁拥有这两面,从高中时候就开始的写作练习让他像一个离开了正常队伍的少年,早早的进入了自己的象牙塔,他就在自己的象牙塔中用掌握的文字宣泄着年轻人天然的愤怒和反叛,就像那只找不到对象的勃起的生殖器。我相信他,这个离队少年。不苛求他马上看到自己之外的风景,因为自己的风景还没有描绘完。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那个不想听导师话的导演系学生,至今没有成为导演,却俨然是一个作家了。以后的胡迁会是怎样?一切,交给时间吧。
序/暗室明眼人/黄丽群
序/离队少年/王小帅
一缕烟
大象席地而坐
漫长的闭眼
气枪
张莫西去了沙漠
猎狗人
大裂
婚礼
鞋带
静寂
荒路
倾泻直下
羊
约会
玛丽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