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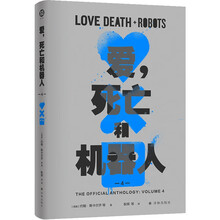
时隔四年,继《地铁》《高铁》的热销之后,韩松为我们带来了又一部反乌托邦里程碑之作!“得什么,也不能得病”,这一次,欢迎来到“药时代”,进入噩梦般栩栩如生的“医院”, 直面白大褂的诱惑,重置医患关系与性别关系,而治疗,抑或逃离,我们是否真有选择?……如何思考我们时代的医疗变局?怎样理解宇宙尺度的病与痛?韩松给出了科幻现实主义的解决之道,“用科幻的思维,把现实中的荒诞重新组织成为具有强烈逻辑性、理性的东西”,就像侦探一样,不仅目击案件的现场,而且挖掘记忆的秘密,把那些正在遗忘中的,却噬咬人的心灵及潜意识的,阴阳交界处的,重新回忆并记录下来,形成一幅更精细确致的地图。
我出差时,在报销标准许可内,选择住高级些的酒店,因为比较舒适和有面子,服务也花样繁多。这次我一下飞机到C市,就对出租车司机说,去某某酒店。我已在网上订好它了。
这是一家知名国际连锁酒店,外形明快简洁,具有后现代风格。门童殷勤为客人搬运行李。前台服务员满脸谦恭笑意。似乎一切令人放心。
我办完手续,进得房间,有些口渴,就喝了一瓶酒店备的免费矿泉水。
但很快我感到一阵腹痛,也不明原因。后来痛得厉害,我就倒在床上,昏睡过去。未料一睡三天三夜。
醒来时,我见床边站着两位身穿灰色西装的女服务员,也不晓得她们是何时、怎么进来的。
她们见我醒转,就一字一句说,接到大堂经理指示,要送我去医院。我奇怪酒店是怎么得知我腹痛的。
想到身负公务,我不愿去,但这两个女人,三十五六岁,一个烫发,一个扎辫;一个尖脸,一个圆脸,异口同声:“不行,你病了。”
她们伸手拉我。我急忙说:“我没病,只是稍稍腹痛而已。”
但她们说:“你确实病了。已经睡了三天三夜。”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酒店的人,怎会不知道!”
“有那么严重吗?”
“这可是天大的事。得什么,也不能得病呀。”
我才明白是有问题了,心想或许就是病了吧。但我提出:“要去就去医保定点医院,否则报销不了医药费的!”
二女应声:“哎,放心,都考虑周全了!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客人满意。”
说到这里,她们飞快为我穿上衣裤鞋袜,把我拖下床、架出门。两人身手娴熟,看样子为客人提供这种服务,不止一次了。我只好听之任之。关键是,能够报销医药费,这就可以了。
酒店叫来急救车。车子载着我们三人,一路鸣笛穿过C市,驶向医院。
2. 个人行动转换成了组织行为
这是一座江水环抱的山城,人烟浩穰,商贾辐辏,娱游壮阔。城中栽满高大的银杏树,建筑物崔嵬险峻,凌空飞出,如戟逆天,却雾霾昏沉,气象阴冷,淫雨连绵,黏滑溽湿,一切模模糊糊。
我痛得无心欣赏景致,只是想到,我出差至C市,是这里的B公司出钱,请我来写司歌的。
我的本职工作,是在京城做公务员,每天的任务就是为上司撰写总结报告和讲话稿。好在我业余还是个歌词作者,用爱好转移了工作的无聊。我在社会上小有名气,时常也应邀为企业写作,弄点外快贴补生计。因为这个,B公司找到了我。
但我的上司喜欢暗中检查下属的往来函件,把B公司写给我的信扣下,拆开来审视,然后以单位名义派我出差。个人行动于是转换成了组织行为。这让事情变得不太有趣,不过也无所谓吧。这么多年早习惯了。只是未料甫抵C市就病了。
提起医院,本是我熟悉的去处。像单位一样,这也是一个大型组织。此二者,掌控了我的起居作息、生老病死。在我国,跟它们打交道,是最基本的公民素质。
我体弱多病,总得三天两头上医院拿药。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害怕去医院,却被它磁石般吸住,不去不行。但C市医院,还是头遭拜访。也好,认认门。还要在这儿写歌呢。工作时再犯病,麻烦就大了。我不是一个喜欢多事的人。
汽车上山下坡,兜来绕去,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抵达目的地。医院依山临江而建,如这座城市一样鸿篇巨制。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蜷伏在雨雾中,像一头灰头土脸而又威风凛凛的猛兽。
送我来的女人如释重负说:“这便是本市的中心医院,要来就来最好的医院。小杨,你可是我们的贵客哟。”
她们疾步如飞,轻车熟路,拖着我直奔门诊部。
3. 不能证明生病,人就没法活了
我凭借丰富的就医经验,仅扫视一眼,便知这医院建得不错。门诊大厅雕栏玉砌,高阔深远,体象天地,经纬阴阳。锡白色无源光线滚滚洒来,四方覆射,映照着数十列不见首尾的队伍。我认出这是排队挂号的长龙。病人们面目不清,阴暗的江河般缓缓流淌。有的拖着行李箱,有的拎着小板凳。更多病人及家属,支流般从不同方向汇入,不时激起波澜。“岸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站着身穿黑制服、臂戴红袖章、手执防暴盾的保安,用火眼金睛扫射人群,令现场秩序保持谐美。
哦,这正是我熟悉的一幕。我始放心。这时,两个女人从我衣袋里搜走钱包,一人排在队尾,要帮我建卡、挂号,另一人则为我能快些建上卡、挂上号,找熟人去了。大厅里扬声器发出此起彼伏的轰鸣,那是数不清的窗口后面医务工作人员在呼喊,与黄牛加价兜售专家号的嘶叫混合为交响曲。
肚子又痛起来,我就蜷缩在一张长椅上。椅中苍蝇一样层叠落满病人,发出嗡嗡的刺耳呻吟,好像对我说:幸亏及时来到医院,否则死在酒店,都无人知道呀。
我才有些后怕。性命攸关,我最先想到的,却是报销医药费。在我国,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很多人死掉,不是因为有病,而是因为没钱。
钱的确要紧。门诊大厅的几面墙上,大幅张贴着收费标准一览表,以便病人尽早阅知。检查、治疗和用药的价格俱公之于众。专家挂号费,十几元至几百元不等,各个专科排列得细致入微,把一个整人分解成眼、耳、鼻、头、颈、胸、腹、心、肝、肺、肾、血、神经、皮肤等部分,仅皮肤便又有真菌、红斑狼疮、肿瘤、过敏、梅毒、结缔组织、色素、银屑、胶原、毛发、大疱等诸种病目,收费亦各不相同;从指血到尿检,从超声到尸检,要缴多少钱,也写得清清楚楚;针剂有几百元的,也有数万元的;病房床位则分为普通病床、干部病床、等级病床和特需病床,押金从几千到几万元。又把病人分门别类为市医保病人、农村合作医保病人、公费病人、自费病人、其他保险病人、VIP病人等,所付款额差异颇大。在医院,人不是按男人和女人来定义的。
但病人刚到门诊部,还难立即显出分别,大家只是不分彼此挤在一起簇拥攒动,像要去赶火车——虽说有庙堂的即视感,但此地细看确似候车大厅,病人的模样就跟农民工似的,他们心急如焚,生怕错过车。
空气浑浊,咽喉刺痛。地面流溢着一层像是烂泥、雨水、汗渍、尿液、口痰和呕吐物的混合物,又纷纷扬扬漂浮起小广告纸片,上写“代办挂号,安排住院”、“提前做各项检查”、“代开发票,不能报销的改成能报销的”等等。每过一刻钟,就有一排身着黄色制服的女清洁工冲上来,把垃圾迅速扫除掉。
忽然,一辆平车斜刺钻出,上面站着两个穿脏兮兮暗白色外套的青年男子,手举黑乎乎的汤勺,哐哐敲响一口大铁锅,原来是热气腾腾卖快餐的,有包子、稀饭和咸菜。病人们眼睛陡然一亮,从四面八方轰隆隆围拥上去,没挤到跟前的,急得用拳头擂打胸脯,猩猩般吼叫。卖饭人说:“嚷什么,都有!”
我嘴里涌出津液,意识到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但一到医院就想进食,这岂不表明我胃口很好吗?胃口很好不就证明我没病吗?没病怎么会来医院呢?不来医院又如何证明自己是病人呢?不能证明生病,人就没法活了。
想到这里,我不禁要笑,人真是贪心的动物。可不能这样哦。我宁愿挨痛,也要忍着不去进食。这是医院,不是酒店。医院除了治病,还是抑制人的欲望的。
我抬头,见一块液晶大屏幕吐出红字:“服务好,质量高,医德好,群众满意。”“生命相系,性命相托,共克疾病,服务人民。”这才心有慰藉。
等了一个多小时,两名女人蹦蹦跳跳回来,兴高采烈举着信号旗似的挂号单,冲我起劲招摇。我却痛得无力起身讶迎。
4. 把生命交给了医院
女人把我拽起,搀扶至分诊台。由于是第一次到C市医院,我颇羞涩,若初次相亲,不知进退。女人又好气又好笑,说:“别这样呀,咱可是老病号了。”
我不好意思道:“请放心吧。”
她们又争着去帮我取病历——原来,它就存放在医院地下室。我分明是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这家医院呀,这儿怎会有我的病历?
转念一想,也说得过去吧。天下医院是一家,已经连锁联网,实现异地医保就诊了。现代医院虽起源于西方,发扬光大它的却是我国。
女人去取病历,我独自留下。又看到,候诊大厅里,除卖餐食的,还有更多项目,贩售花圈、鲜花、水果、针线、口罩、健身器、轮椅、洗洁用具、便盆、轮椅、盗版书、出口转内销服装、过期化妆品、骨灰盒、棺材、假发、人参、鞭炮、棉被、望远镜、指南针、手电筒、笔记本、贺年卡、水果刀、切菜刀、佛珠、观音像、指甲钳、旧电视机、二手收音机……应有尽有。另有招徕旅店生意的、出租房屋的、算命看相的、倒卖药品的、自荐医托的等,形成一个集贸市场,吆喝声、还价声、哭叫声、碰撞声、吐痰声、咳喘声、行路声、器物声、叮当声、哗啦声、吧嗒声、咿呀声……此起彼伏。
哦,这一幕亦令人动容。仔细观察,等待就诊的,各色人皆有,以老年人最为瞩目——正如新闻报道所说,我国已进入银发社会,老人数量超过儿童。这些病人满脸深渊般沉寂,面对撕裂耳膜的噪音杂音,从容镇定,听而不闻,裹着旧军大衣,稳如泰山,昂头枯坐,周身冒出膏药、顽石和尘埃气味,有人腋下和胯间结满蛛网,肿胀的手爪攥住陈皮般的病历,与活泼雀跃的商贩对照,形成别具一格的审美趣味。
看到老人在,我心里有底了。想到这是与C市医院首度约会,我掏出手机,拍了一照,以作留念。
立即,两名保安冲上来,揪住我的衣领。我刚要解释,他们就举手做出揍人状。我欲反问,凭什么?依据哪条法律?有“禁止拍照”告示吗?但我想到,既已身为病人来到此间,就算把生命交给医院了,怎可造次?就乖乖把照片删了。
保安骂骂咧咧走了。这个插曲令我腹痛加剧。其他病人都在看我。我深感耻辱,便挣扎起身,向前走去。
四通八达的走廊像蛛网,无尽无终,又柳暗花明别有洞天。有病人迷路了,累趴了,昏倒了。我踉跄半天,至一诊室前。门口贴了一组照片,大红大紫,为医院灰白二色的单调打上一抹光亮。一张拍的是一个胃,黑乎乎的底色上,长满鲜红疣疮;另一张是惨白的食道,膜上结出珍珠般的肉团;另有一个青色菜花状东西,大张旗鼓用文字注明是十二指肠癌。这就像京城七九八艺术区的画廊一样。
不用说,是消化内科了。大群病人堵在门前,吵嚷不停,着急进去。我观察一会儿,明白如果死等,只怕到医院下班都看不上病。我就搡开病人,抢到头里,推门而入。众皆不悦,怒目相视,却俱噤声。他们在猜测我是医生的什么关系。我利用多年就医经验,获得了先机。
5. 像窃贼在作案现场被抓住
诊室里有一张办公桌,里三层外三层被病人围住,他们唾沫横飞,比手画脚,争先恐后向坐在桌后的一名医生陈述。室内气温骤升,有病人把上衣捋起,露出肚皮。一位病人一进来就抖出两米长的山水国画,要送给医生。几名病人争着把花生、核桃、鸡蛋等土特产放到医生桌上。还有病人及家属干脆跪在地上,冲医生喊:“教授,加个号吧,挂您的号挂了两个月,都挂不到哇。”医生大约也习惯了,视若无睹。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六旬男人,如盆景里的一面精致假山,身着棱角分明的白色长衣——这乃是真正的炫目白色,像镇魔用的法瓶,对此我亦不陌生。医生胸前口袋插满一大排红、蓝、黑色的钢笔、铅笔和圆珠笔,白大褂后面是深色的西服领带,脚下一双黑皮鞋锃亮。他位居人群中央,仪态威严,亦不多言,令我觉出一种特别的美感,心生依恋。等待半天,医生终于慢条斯理冲我说:
“你怎么了?”
“喝了点儿水……”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台词简明扼要背出,尽量显得不像是在申诉冤屈,以给医生留下良好印象。
“是酒店的矿泉水吧。”
“啊?!”
他怎么知道的?C市医院的医生这么厉害?我忽然想到,如果要我现在就送红包,可怎么办?钱包攥在女人手里哟。我像窃贼在作案现场被抓住,顿时面红耳赤。
“是外地人吧。”医生又道,冷峻的面目,令我想到审判庭上的法官。
“是、是。”京城公务员的骄气被打消了。
“为什么要来我市?”
“因为、因为……”
“你确定喝的真是矿泉水吗?”
“大概、大概……”
“矿泉水!矿泉水!你以为那水能喝吗?患者,这儿可不是外国哟!”
医生老大不满似的说,抽出一支铅笔,啪啪敲打桌面。这位大夫水平太高啦,连正眼也没怎么瞧我,连我的主诉也不详细听,连叩诊也不做,就一眼瞧出了问题。他是说本地的矿泉水是假冒伪劣产品吗?还不如外国那随便拧开龙头就能喝的自来水?里面有致命病菌?还是它太高级、太特别,外地人喝了肠胃不适?这就是我的病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就要收红包了吗?我惊惶失措。病人们向我投出幸灾乐祸的目光。
正尴尬时,诊室里一个铁皮柜乒乒乓乓发出爆响。
……
韩松有一种极其特别的“幽黯意识”,从中延伸出一个大历史思维的脉络,并以一种外太空的视角观察着当今这个世界的文明。
——王德威
从某种意义上说,韩松处在从鲁迅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先锋作家的人性批判的延长线上。
——严 锋
我写的是二维科幻,韩松写的却是三维科幻。如果说中国科幻是一个金字塔,二维科幻是下面的塔基,而三维科幻则是塔尖。
——刘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