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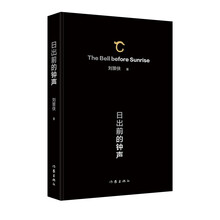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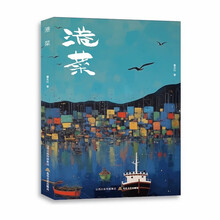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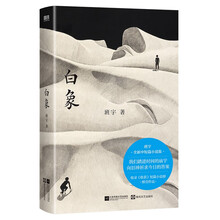
1、 葛亮“人间烟火”系列,芸芸众生的时代回响。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经历者,同时也是谛視者。我们都在观照他人的人生风景的过程中不断地成长,也走向成熟。
“人间烟火”这四个字,从某种意义而言,代表了一个时代中*平朴和日常的氛围,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的,非常朴素简单,甚至于微小的人与事,如同涓涓细流,不断汇聚,共同构成这个时代真正的声响。
2、 每个作家都会为自己的成长写一部分小说,《七声》与《戏年》即是葛亮的成长经历。
斯文特拉说每一个作家都必须为自己的成长写一部小说。《七声》与《戏年》,正是从作者自己的成长经历出发,给予读者的一份回馈。这是一个人的声音,同时也是一群人的声音,在这声音的脉络里你能体会到,这是我们共同的休戚与共的经历。每个人的声音虽然细隐,却与大时代的跫音同奏。一则则平凡又跌宕的人生故事,交叠出流淌于坊间的动人旋律。
3、人生如戏,戏若人生。导演是时日,演员是你。
“人生如戏,戏若人生”,两者之间充满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辩证的关联,将戏当成人生来演,“戏骨”所为,是对现实的*大致敬。而将人生过成了戏,抽离不果,则被称为“戏疯子”。
每个人都在上演自己的一出戏,《戏年》这本书,它的主题也是人生,说到底就是一出戏,导演是时日,而演员是你,这期间的苦乐、哀伤、悲壮、渺小,实际上也都在提示着我们成长乃至于成熟。有的人冷静观照,有的人激荡不拘,有的人全情投入,有的人漠然抽离,但每一个认真生活在这时代与生命的舞台上的人都值得尊敬。
4、 悲天悯人的写作风格,日常温暖的民间书写。
作家葛亮虽然年轻,却有颗悲天悯人的“老灵魂”。故乡南京的文化浸润,让他不知不觉更热爱“民间”的声响。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厅一堂,一花一木,一茶一碗,皆为传说。他的文字,充满良善与温暖,带来宁静会心的阅读体验。在这快马扬鞭的滚滚红尘中,体会民间风情所传达出的温柔与幸福。
“人生的过往与流徙,最终也是一出戏。有人负责戏,有人负责现实。人生如戏,戏若人生,此去经年,往复不止。”
在《戏年》这部小说中,叫作毛果的少年再次登场,以他自身的观影经历去体验别人的人生,去看这一个又一个时而启幕时而谢幕的平凡人的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和我们有关电影的时代记忆紧密相连。通过这些故事,你会看到一部一部曾经在我们的生命深处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那些影片。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苦痛也关于离别。那些似乎已经褪色的画面,深植在记忆的深处,也许有一天,因为一段文字一触即发,提醒着你的蒙昧与成长,昭示着你的得到与失去。而这也正是《戏年》这部小说,希望与你分享的,带着时代温度的人生风景。
刚到香港的时候﹐我住在一幢唐楼里﹐住在顶楼。在西区这样老旧的小区里﹐楼房被划分为唐楼与洋楼。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没有电梯的。我住在顶楼七楼。换句话说﹐楼上即是楼顶﹐楼顶有一个潮湿的洗衣房和房东的动植物园。
动植物园里风景独好﹐除去镇守门外的两条恶狗。房东是个潮州人﹐很风雅地种上了龟背竹﹐甚至砌了水池养了两尾锦鲤﹐自然也就慈悲地养活了昼伏夜出的蚊子。
有了这样的生态﹐夜里万籁齐鸣就不奇怪了。狗百无聊赖﹐相互撕咬一下﹐磨磨牙当作消遣。蚊子嗡嗡嘤嘤﹐时间一长﹐习惯了也可以忽略不计。房东精明得不含糊﹐将一套三居室隔了又隔。我这间隔壁﹐给他隔出了一间储藏室。一个月后,有天听到有声响。出来一个中年人﹐有众多印度人黧黑的肤色和硕大的眼睛。中年人是医学院的博士。博士握了我的手﹐说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博士败了顶﹐是个孱弱谦和的样子﹐眼睛里有些怨艾的光芒。当天晚上﹐储藏室里就发出激烈的声响﹐我再不谙世事﹐男欢女爱的动静还是懂的。这一夜隔壁打起了持久战﹐我也跟着消停不了。安静下来的时候﹐已是东方既白。清晨起来博士又是温柔有礼﹐目光一如既往的忧愁。而到了当天晚上﹐又是判若两人。日复一日﹐隔壁总是传来饥渴的做爱的声音﹐雄狮一样的。他总是换不同的女人。这对一个适龄男青年的正常睡眠﹐是莫大的考验。
在一个忍无可忍的夜晚。我终于夺门而出。在皇后 大道上兜兜转转。穿过蚊虫齐飞的街市。在太平洋酒 店﹐我看到了远处的灯塔的光芒被轩昂的玻璃幕墙反射了。汽笛也响起来﹐那里是海。香港的海与夜﹐维多利亚港口﹐有阔大的宁静,近在咫尺。我想一想﹐向海的方向走过去。
穿过德辅道﹐有一座天桥。上面躺着一个流浪汉。后来 我才知道﹐他是长年躺在那里。他远远看见我﹐眼皮抬一抬,将身体转过去。像要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又沉沉地睡了。
下了桥﹐有腥咸的风吹过来。我知道﹐已经很近海。再向前走。是一个体育场。我只是一味向海的方向走。也许我是不习惯香港天空的逼狭的。海的阔大是如此吸引我。越过篮球场﹐走到尽头﹐巨大的铁丝网却将海阻隔了。我回到篮球场﹐在长椅上坐下。旁边的位置上坐着几个女人﹐很快人多起来﹐是些年轻人在夜里的聚会。这里顿时成了一个热闹的所在。一个姑娘快活地唱起来。但是﹐他们还是走了﹐回复了宁静。看见远处的景致﹐被铁丝网眼筛成了一些黯淡的碎片。我觉得有些倦﹐在长椅上仰躺下去。
远远走过来一个影子﹐是一条狗。很大﹐但是步态蹒跚。后面跟着两个人﹐走到光线底下﹐是个敦实的青年。穿着汗背心。还有个中年人﹐则是赤着膊﹐喜剧般地腆着肚 子。青年沿着塑胶跑道跑上一圈﹐活动开了﹐在场上打起篮球。中年人站在篮球架底下﹐抽起一根烟。抽完了﹐和青年人一块打。两个人的技术都不错﹐不过打得有些松散。谈不上拼抢﹐象征性地阻攻﹐是例行公事的。突然两个人撞上 了。中年人夸张地躺倒在地。拍一下肚子﹐嘴里大声地骂了 句什么﹐青年人一边笑﹐一边将球砸过去﹐中年人翻一下身﹐躲开了。两个人就一起朗声大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能听出他们是很快乐的。
那条狗很无聊地走来走去﹐没留神已经到了我跟前﹐汪汪地大叫。我并不怕狗。和它对视﹐我在它眼睛里看到了怯懦﹐还有衰老。那里积聚了一些眼屎。我伸出手摸一下它硕 大的头﹐它后退了一下﹐不叫了。龇了一下牙﹐却又近了些﹐蹭了蹭我的腿。我将手插进它颈间的毛。它并非前倨后恭﹐而是知道﹐我对它是没有敌意的。
这时候﹐青年远远地跑过来﹐嘴里大声地喊﹐史蒂夫。听得出﹐是呵斥的意思。大狗缩了一下脖子﹐转头看一下他﹐又看一下我﹐转过身去。青年在它屁股上拍一记﹐上了狗链。然后对我说﹐对不起。没事吧?我说﹐没事﹐它叫史蒂夫?他眼睛亮一下﹐说﹐哈﹐你说普通话的。他的普通话很流利﹐说﹐这狗的种是鲍马龙史蒂夫﹐我就叫它史蒂夫。它太大﹐常常吓到人﹐看得出﹐你懂狗的。我说﹐我养过一头苏牧。大狗的胆子﹐反而小。青年说﹐我叫阿德﹐你呢。我说﹐我叫毛果。
阿德说﹐毛果﹐过来和我们打球吧。
这是我与阿德言简意赅的相识。还有史蒂夫。
阿德的球打得很好。但是有些鲁和莽﹐没什么章法。而我﹐却不喜欢和人冲撞。往往看到他要上篮﹐我就罢手了。
阿德就说﹐毛果﹐你不要让我。这样没什么意思。我就和他一道疯玩起来。
中年人这时候﹐坐在地上﹐斜斜地叼着一根烟﹐没有点燃﹐看着我们打。
打到身上的汗有些发黏的时候﹐中年人站起身来﹐大声说了句什么。我算粗通了一些广东话﹐听出说的是“开工” 两个字。阿德停了手﹐说﹐毛果﹐我走先了。
我其实有些奇怪﹐这样晚﹐还开什么工。不过我也有些了解香港人的时间观念了﹐一分钟掰成八瓣使﹐只争朝夕。
阿德牵上史蒂夫﹐说﹐我夜夜都在这里打球﹐你来就看到我了。然后抱一抱拳﹐说﹐后会有期。
我笑了。阿德也笑了。笑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
我回到房间﹐冲了个凉﹐隔壁的储藏室已经没什么声响了。博士结束了折腾﹐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看到史蒂夫硕大的头﹐旁边一只手拍了一下它。然后是阿德的声音﹐走吧﹐史蒂夫。
和阿德再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仍然是暗沉沉的夜里。四面的射灯将球场照成了酱色﹐阿德一个人在打球。角落的长凳上一些菲佣在聊家常。史蒂夫和一头圣伯纳犬互相嗅嗅鼻子。史蒂夫为表示友好﹐舔了一下圣伯纳﹐圣伯纳不领情﹐警戒地后退一步﹐狂吠起来。
史蒂夫横着身体逃开了几步﹐看见我﹐飞快地跑过来﹐蹭蹭我的腿。冲着阿德的方向叫了一声。
阿德对我挥挥手,将篮球掷向我。我向前几步﹐远远地投了个三分。球在篮板上弹了一下﹐阿德跃起﹐补篮﹐进了。我们抬起右手﹐击了下掌。远处有菲律宾姑娘吹起了响亮的口哨﹐为这一瞬的默契。
我们默不作声地玩了一会儿﹐灯光底下﹐纤长的影在地上纵横跃动。史蒂夫兴奋地跟前跟后﹐捕捉那些影子。最后徒劳地摇摇尾巴﹐走开去。
阿德的体力是好过我的。他看出我有些气喘的时候﹐停下来﹐说﹐投下投下( 广东话﹐休息的意思)。我去自动售卖机买可乐。回来﹐看到阿德坐在长凳上﹐点起一支烟。球场上有些风﹐阿德转过身﹐避过风口﹐点燃了。眉头皱一皱﹐是个凝重的表情。阿德没有接我手中的可乐﹐将手指在烟盒上弹一弹。取出一根﹐就着自己的烟点燃了﹐递给我。
我抽了一口﹐有些呛﹐咳起来。
阿德笑了﹐看你拿烟的手势﹐就知道不惯抽的。我原来也不抽﹐现在抽了﹐解乏。 这烟还好﹐不怎么伤肺。阿德对我扬一扬烟盒﹐是 “箭”。 毛果﹐你是来香港读大学的吧。我点点头。 阿德抽了一口烟﹐说﹐真好。 我说﹐阿德﹐你的普通话说得很好。 阿德停一停﹐说﹐我也是大陆过来的。 阿德说﹐我老家是荔浦﹐广西荔浦﹐你知道吧? 我说﹐我知道﹐荔浦的芋头很有名。全国人民都知道。 阿德笑了。对﹐我阿奶在后山种了很多芋头﹐芋头是个 好东西。吃一个就够饱肚了。 阿德沉默了一会儿﹐看看表。说﹐我该走了﹐开工了。 他牵起史蒂夫﹐远远地走了﹐有些外八字﹐走得摇摇晃晃的。
自序/Ⅰ
于叔叔传/1
阿德与史蒂夫/67
老陶/109
戏年/141
附录/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