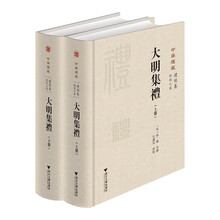《红楼梦》中的寓意
多少年来,《红楼梦》一直作为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受到珍视。红学家们不停地考证作者的身世,并且希望在小说的字里行间发现诟病清朝统治的曲笔,因为他们体会到小说里充满了正中有反的寓意。脂砚斋的批评,特别强调书中的一辞、一句、一诗、一词都蕴涵着深意,处处从个别细节的观察引申到对全书寓意的理解。例如,第二回通过贾雨村之口,说到宝玉的一种怪癖——他每遇父母杖责,便呼姐唤妹,借以减轻疼痛,脂砚斋于此作眉批道:“此是一部书中大调侃寓意处。”
有人也许会说,脂砚斋和其他清代评点人所说的“隐意”,以及我们这里所说的“寓意”,实质上不过是指这部小说体现了某种深刻的含义而已,并且这种含义也不比任何其他反映生活真实的集大成式的写实小说更多。争论看来还得回到寓意的定义上去。我认为,作者通过叙事故意经营某种思想内容才算是寓意创作。如果在现实的描述中简单地呈露某种生活的真实,我们只能说这部书有思想内容,至多可以说它适宜于寓意式的阅读。如果作者确实有意对人物和行为进行安排,从而为预先铸就的思想模式提供基础,我们就有理由说,他已经进入了寓意创作的领域了。
《红楼梦》在结构上有一个特点,似是寓意创作的标志,即作者浓墨酣畅地以“二元补衬”的模式展开描写。中国小说戏剧不乏悲欢离合、荣枯盛衰的描写,然而,即使从这种俗见的文字看去,《红楼梦》在情节陡转之处,在因否泰莫测而摇人心旌之处,也无不暗含阴阳哲理的结构形式。第七十五回和第七十六回贾府在中秋佳节时的强颜欢笑,小说最后那种不了了之的收场等等,都是复杂的二元错叠的例子。明斋主人颇为赞赏作者的这种精细的布局技巧:“小说家结构,大抵由悲而欢,由离而合,是书则由欢而悲,由合而离,遂觉壁垒一新。”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按照从“悲中喜”到“喜中悲”,从“离中合”到“合中离”的无休止的替代,而不必按照从冲突高潮到冲突解决,甚或从幻想到觉醒的辩证发展,去总结小说安排情节的特点。
也许有人说,“二元补衬”的复杂现象,正是整个中国白话小说的总特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特地选出某些二元概念而进行布局,显然是寓意创作意图的透露。“动静”的交替是二元补衬的主要脉络之一,它组成了小说大部分表面的情节。宝玉及其姐妹们的生活,忽而“热闹”,忽而“无聊”,即贯穿着这一脉络;同时,“动静”的补衬亦可说明:何以乍遇安宁又生是非,何以喜庆未酣而意外已至,何以远离人寰的幽园,却也自自然然地连涌波澜。另外,作者仿佛还着意把“内”(贾府的世外桃源——大观园)、“外”(出贾府门即是京中大内)当作一条脉络,使其与“出入”的描写,细密交织并不断伸展。“出入”的脉络,似是隐在出嫁、出仕、出家等(均可以“出门”一语囊括)事件之中。
《红楼梦》寓意结构的主脉是“真假”。其中有真假宝玉人魂并现的情节——“真”(甄)宝玉缅怀自己南京的家园,“假”(贾)宝玉在京中真真假假的梦幻——似乎是一种明显的游戏笔墨,甚至可贬为俗气的谑头。然而,仔细分辨一下,可以看出作者是在认真地对待其中的哲理的,因为他以“真假”情节开场而逗出全书的寓意,实在是经过一番苦心策划的。书中不仅用长达两回之多的篇幅写甄士隐和贾雨村判然有别的闲居、仕途生活,凸现他俩的一真一假、你上我下的情事,组织“真假”脉络(第一回中关于“时飞”的注脚,透露作者的意图尤为清晰),而且,后文不时地拨出贾雨村来,与开篇遥相呼应(高鹗也在末回安排了甄贾的重逢,使故事首尾衔接)。作者还设计了一个远居南国的甄宝玉,他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只是从亲友口中才知道他的存在。曹雪芹尽量避免写两个宝玉直接晤面(起码前八十回是如此),而高鹗却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戏剧性的(即使是缺乏说服力的)冰炭不相投的聚会。无论人们的评价如何,这两种处理手法,是引人注目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