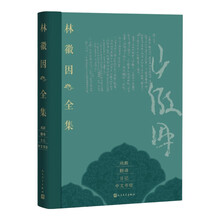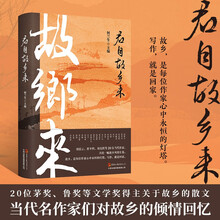一、我的读书生涯
很早以前,我读书几乎是不加选择的,或者是一部名著,或者是一部书的书名优美生动吸引我,随手拈来,放在床边,以备夜读所用。用这种方式我读到了许多文学精品,也读了一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对某几部名著我无法进入真正的阅读状态。比如麦尔维尔的巨作《白鲸》,几乎所有欧美作家都倍加推崇,认为是习作者所必读的,但我把《白鲸》啃了两个月,终因其枯燥乏味,而半途而废,怅怅然地还给了图书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以后再也没有重读《白鲸》。如果现在重读此书,不知我是否会喜欢。但不管怎样,我不敢否认《白鲸》和麦尔维尔的伟大价值。
令人愉悦的阅读每年都会出现几次。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时我在北师大求学,一位好友向我推荐并把《守望者》借给我,我只花了一天工夫就把书看完了。我记得看完最后一页的时候教室里已经空空荡荡,校工在走廊里经过,把灯一盏盏地拉灭。我走出教室,内心也是一片忧伤的黑暗。我想象那个美国男孩在城市里的游历,我想象我也有个“老菲芯”一样的小妹妹,我可以跟她开玩笑,也可以向她倾诉我的烦恼。
那段时间,塞林格是我最痴迷的作家。我把能觅到的他的所有作品都读了。我无法解释我对他的这一份钟爱,也许是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因此把《守望者》作为一种文学精品的模式,这种模式有悖于学院式的模式类型,它对我的影响也区别于我当时阅读的《静静的顿河》,它直接渗入我的心灵和精神,而不是被经典所熏陶。
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完全摆脱塞林格的阴影,我的一些短篇小说中可以看见这种柔弱得像水一样的风格和语言。今天的文坛是争相破坏偶像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塞林格是浅薄的误人子弟的二流作家,这使我辛酸。我希望别人不要当着我的面鄙视他,我珍惜塞林格给我的第一线光辉。这是人之常情。谁也不应该把一张用破了的钱币撕碎,至少我不这么干。
现在说一说博尔赫斯。大概是1984年,我在北师大图书馆的新书卡片盒里翻到那部书的书名,我借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从而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
我为此迷惑。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几年以后我在编辑部收到一位陌生的四川诗人开愚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博尔赫斯的光明》。散文记叙了一个博尔赫斯迷为他的朋友买书寄书的小故事,并描述了博尔赫斯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哀伤。我非常喜欢那篇散文,也许它替我寄托了对博尔赫斯的一片深情。虽然我没能够把那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我同开愚一样相信博尔赫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启发了一批心有灵犀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得以一显身手。
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阅读中你的兴奋点往往会被触发,那就给你带来了愉悦。那种进入作品的感觉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对于一部你喜欢的书,你会记得某些极琐碎的细节,拗口的人名、地名,一个小小的场景,几句人物的对话,甚至书中写到的花与植物的名称,女孩裙子的颜色,房间里的摆设和气味。
两年前我读了杜鲁门·卡波特的《在蒂凡纳进午餐》,我至今记得霍莉小姐不带公寓钥匙乱揿邻居门铃的情节,记得她的乡下口音和一只方形藤篮。
有一个炎热的夏天,我钻在蚊帐里读《赫索格》,我至今记得赫索格曾在窗外偷窥他妻子的情人——一个瘸子——在浴室里给赫索格的小女孩洗澡,他的动作温柔、目光慈爱,赫索格因此心如刀割。在索尔·贝娄的另一部作品《洪堡的礼物》中,我知道了矫形床垫和许许多多美国式的下流话。
卡森麦勒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我读过两遍。第一遍是高中时候,我用零花钱买了生平第一本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美国当代短篇小说集》。通过这本书我初识美国文学,也细读了《伤心咖啡馆之歌》。当时觉得小说中的人物太奇怪,不懂其中三昧。到后来重读此篇时,我不禁要说,什么叫人物,什么叫氛围,什么叫底蕴和内涵,去读一读《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明白了。
阅读确实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二、把他送到树上去
卡尔维诺在仰望一片茂密的树林时,发现粗壮杂乱的树干酷似一条条小路,树干之路是幽暗的、弯曲的,当它们向四面八方延伸时,一种神秘的难以勾勒的旅程也在空中铺展开来。是光线的旅程,还是昆虫、苔藓或者落叶的旅程?许多从事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人都可能产生诸如此类的联想,但卡尔维诺慧眼独具,他看见了别的,他还在树上看见了一个人和他的家园。很可能是一瞬间的事,灵感的光芒照亮了卡尔维诺。这一瞬间,作家看见了“树上的男爵”,他正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去,那个在树上跳动的人影,正是作家守望的“人物”……所谓灵感来了,很多时候说的是人物来了。
有个人爬到树上去,不是为了狩猎和采摘,不是孩子的淘气,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在树上生活!读者们之所以无法忘记《树上的男爵》,其实是无法忘记一个爬到树上去生活的人。小说家从来都是诡计多端的,他们塑造的人物形象千奇百怪,套用如今商界的广告营销战略语汇,越怪越美丽,乖张怪谲的人物天生抢眼,印象深刻自然是难免的,但爬到树上去的柯西莫超越了我们一般的阅读印象,这个人物设置至今看来仍然令人震惊,在文学史上闪着宝石般的光芒。
《树上的男爵》出版于1957年,此时距离卡尔维诺的成名作《通向蜘蛛巢的小径》发表正好是十年时间,距离他的另一篇精彩绝伦的作品《分成两半的子爵》则相隔了五年时光。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青壮年期的十年时光应该是一段河流般奔涌的创作史,可以泛滥成灾却不允许倒流,而卡尔维诺似乎是斜刺里夺路狂奔,背叛自己的同时也脱离了保守的意大利的文学大军。卡尔维诺脱颖而出之时正是意大利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疮疤渐渐结痂之时(而他早已经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触及了那块溃烂时期的疮疤),战争年代他在破败的街道和酒馆中体会意大利的悲怆,在和平年代里他有闲适的心情观察祖国意大利了,结果从树上发现了自己的祖先。从开始就这样,卡尔维诺善于让人们记住他的小说。即使是在《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人物也是不易忘却的,一个孤独的男孩,被同龄的孩子们所抛弃,却被成年人所接纳所利用。没有人会忘记男孩的姐姐是个妓女,而且是个和德国军官睡觉的妓女。我曾尝试拆解小说中的人物链条:皮恩—姐姐—德国军官—游击队,感觉它像一种再生复合材料,可以衔接无数好的或者很平庸的情节人物关系(由此有了皮恩偷枪的故事,有了皮恩和游击队营地的故事)。这个人物链所滋生的小说材料是多快好省的,但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过于讲求效率的职业手段都有一定的危险。《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也如此,看似牢固的人物链后来不知怎么脱了链,小说渐渐发出一种机械的松散无力的噪音,也许是从皮恩越狱后碰到“大个子”开始的,一切细节几乎都在莫名其妙地阻碍小说向辉煌处发展。我们最后读到了一个少年与游击队的故事,加上一把枪,很像一部二流的反映沦陷的电影。
一个过于机巧科学的人物链对于具有野心的小说也许并不合适,而作家也不一定非要对“二战”这样的重大题材耿耿于怀,卡尔维诺对自我的反省一定比我深刻。五年过去后意大利贫穷而安详,卡尔维诺写出了《分成两半的子爵》,单就人物设置来说,已经抛弃了人们熟悉的模式,十年过后《树上的男爵》应运而生,令人震惊的卡尔维诺来了。
卡尔维诺来了,他几乎让一个传统的小说世界都闪开了。让亲人们闪开,让庄园闪开,甚至让大地也闪开,让一棵树成为一个人的世界,让世界抛弃孤独者,也让孤独的人抛弃他人的世界,这是五十年代卡尔维诺对小说人物的设想,也是他文学生涯中一次最决绝而勇敢的小说实践。
少年男爵柯西莫可以为任何一个借口爬到树上去,不一定是为了拒绝吃蜗牛。反叛与拒绝在文学作品中的例子和实际生活中一样多,但卡尔维诺是处心积虑的,爬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这声音是圣洁的,也是邪恶的,是人们能听见的最轻盈也最沉重的召唤。不仅仅是为了反抗,也不是为了叛逆,当一个孩子任性的稚气的举动演变成一种生存的选择之后,这个故事变得蹊跷而令人震惊起来。读者们大概都明白一个不肯离开树顶的少年身上隐藏着巨大的哲学意味,但每个人也都为卡尔维诺惊世的才华捏了一把汗,他怎么让这出戏唱完呢?柯西莫将在树上干些什么?柯西莫会不会下树?柯西莫什么时候下树?(大家都明白,柯西莫下树,小说也该结束了。)
卡尔维诺不让柯西莫下来,柯西莫就下不来。柯西莫在树上的生活依赖于作家顽强的想象力,也依赖于一种近乎残忍的幽默感。柯西莫在树上与邻居家的女孩薇奥拉的糊涂的爱情在人们的预料之中,但他在树上与大强盗布鲁基的交往和友谊在小说中却又是奇峰陡生。布鲁基这个人物的设置同样让人猝不及防,他是个热爱阅读的浪漫的强盗,他强迫柯西莫给他找书,而且不允许是无聊的书,一个杀人如麻的强盗最后被捕的原因也是为了一本没看完的书,更奇妙的是布鲁基临刑前还关心着小说主人公的下场,当柯西莫告诉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是被吊死的,这个沉迷于文字的强盗踢开了绞架的梯子,他对柯西莫说:“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
卡尔维诺放大了柯西莫的树上世界,这个人物便也像树一样长出许多枝条,让作家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柯西莫在树上走来走去,从十二岁一直走到年华老去。“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柯西莫变成了老人。”老了的男爵仍然被作家缔造神话的雄心牵引着,沿着树上世界一直走到了遥远的森林中,传奇也一直在延续,树上的男爵亲历了战争,最后见到了拿破仑。作为真正的传奇,小说的结尾无情地挫伤了读者的热望和善心,柯西莫再也没有回到地上来,垂死的柯西莫最后遇到了热气球,奇迹开始便以奇迹结尾,我们最后也没等到主人公回归,小说却结束了。
请注意作家为他的人物柯西莫撰写的碑文,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物,也帮助我们勾勒了卡尔维诺塑造这个人物的思路: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这碑文不知为何让我想起对卡夫卡《变形记》的读解:变为昆虫—体会人的痛苦—无处生活。
最汹涌的艺术感染力是可以追本溯源的,有时候它的发源就这么清晰可见:树上有个人。在我看来,《树上的男爵》已经变成一个关于生活的经典寓言,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卡尔维诺的树也成了世界的尽头。然后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课堂式的问题,你觉得是哪一步棋造就了这部伟大作品的胜局,如果有人问到我,我会这么回答,其实就是一步险棋,险就险在主人公的居所不在地上,而是在树上。
总是觉得卡尔维诺优雅的文字气质后隐藏着一颗残酷的心,细细一想豁然开朗:有时候一个作家就是统治人物的暴君,对待柯西莫这样的人,放到哪儿都不合适,干脆把他送到树上去。
三、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菲茨杰拉德那个时代的作家,写小说多少都有点吊人胃口的习惯,好似我们的京戏,主人公化好了妆,在后台严阵以待,却迟迟不上场,锣鼓胡琴声中拔头筹的是些跑龙套的,最后等得你要骂娘了,那主人公才出来,一个亮相,没有满堂彩,读者心里说,看把你傲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平心而论,等待盖茨比的出场是值得的,尽管小说已经进行到第一章的末尾,盖茨比的出场仍然先声夺人,他“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儿,仰望银白的星光”——这是非常平庸的客观描写,但主观描写却已经足够机智、俏皮了,他“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光是机智和俏皮哪够得上石破天惊?于是叙述者紧接着看见盖茨比先生向着幽暗的海水和一盏又小又远的绿灯伸出了双臂,而且还在发抖。
对写作与阅读都敏感的读者会意识到,作家咬了自己的钩,从此以后,他必须在剩下的篇幅中彻底满足读者对这个主人公的期望了。
汤姆·布坎农和他的社交圈“可疑地”霸占了一会儿小说篇幅,打闹一番后终于知趣地让台。大人物盖茨比却仍然躲闪着什么,似乎在说,小的们先玩。总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味道,当他花园里的夏日派对以穷奢极欲征服上流社会虚荣浮夸的男男女女时,人们相信,西卵的天空确实是有一大片属于这个大人物——有传言说他是德国威廉皇帝的侄儿,理该如此。
但也有传言说盖茨比先生杀过人。这是盖茨比的花园派对上的客人在议论他时提供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多得令读者一时消化不了。比如还有人说盖茨比先生当过德国间谍,还有人否定前面的信息,说“二战”时候盖茨比是在美国军队服役的,比如贝克小姐透露说盖茨比告诉她他毕业于牛津,随后又表示她无论如何不相信盖茨比上过牛津大学。又比如有人说盖茨比是私酒贩子,说他不是威廉皇帝而是德国元帅兴登堡的侄子。
繁杂的信息互相矛盾,有效地堆砌着一个人物神秘的轮廓和线条,却无情地泄露了一个事实,“那么多人到盖茨比家做客,却对他一无所知,仿佛是对他所表示的一种微妙的敬意”。围绕着盖茨比的来历,这么旺盛这么神秘的火焰扇起来,人物反倒被作家架在空中了,怎么办?只好慢慢地放下来,结果,坐在一个“吵吵闹闹的小姑娘”身边的大人物与“我”来了个战友相认,此后是邀请“我”一起试飞水上飞机,此后才是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一句话,“我就是盖茨比”。
盖茨比的财产来历不明,他的性格和形象特征却很明显。喧闹中的若有所思,一掷千金时的若有所失,都是矛盾。矛盾的当然还有他聚集人群后的孤独。他聚集人群又远离人群,在请来乐队为客人演奏交响乐时,“盖茨比单独一个人站在大理石台阶上,用满意的目光从这一群人看到那一群人”。当客人们在自己的花园里狂欢的时候,盖茨比“却变得越发端庄了”。这确实就是大人物的做派了,这做派是财富、傲慢、居高临下造成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它仅仅说明了孤独、拘谨、怯懦,或者心事重重。
盖茨比的人物塑造始终与他的身世解密齐头并进地进行,他的客人已经让他的故事光怪陆离。
偏偏当事人盖茨比自己似乎也在向人文雅地诉说他身世的谎言。这令人头晕,随后作者敏锐地预感到读者将出现的不良症状,适时地调整了叙述节奏,先是解开了“我”、贝克小姐、汤姆和黛西夫妇和盖茨比之间人物关系的纽扣,闹了半天,这葫芦里卖的药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不光是黛西的表亲“我”、黛西的闺中女友贝克小姐会意外,不光是黛西的丈夫会嫉妒,就是读者也会失落,看了半天,看的还是一个爱情故事呀。怎么不是爱情故事?了不起的盖茨比,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与初恋情人黛西的再次相见。
作为一个人物矛盾体,除了被虚荣和浮华的生活方式所俘获,盖茨比也被爱情所俘获。他比一个纯真的小镇青年更执着地追求纯真的爱情。五年后他再次看见黛西之前先是绕着房子跑了一圈,看见以后“面如死灰”,交谈之前局促不安,交谈以后欣喜若狂,大人物盖茨比好不容易流露出小人物的可爱之处,秘密约会却结束了,请注意作家在刻画盖茨比性格的苦心孤诣。“我走过去告辞的时候看到那种惶惑的表情又出现在盖茨比脸上,仿佛他有点怀疑目前幸福的性质。”一个矛盾重重的大人物转瞬间又回来了。“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
突然一下,什么都清楚了,大人物盖茨比不是什么神秘人物,他是一个生活在幻梦中的人。五年以后他以一种幻梦的方式演出着与黛西旧梦重温的好戏,同时尖锐地指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而把小说进行得悠闲过度的作家此时也清醒过来,残忍起来,一个高潮就把数个人物捆扎一遍,作出处理,在盖茨比和黛西一行五人的纽约之行不欢而散后,是盖茨比和黛西的那辆车撞死了威尔逊太太,这个威尔逊太太,正是黛西的丈夫汤姆·布坎南的情人。为什么让这个胖女人去死?为什么让黛西开车去撞她,然后再让盖茨比揽下责任?为什么盖茨比一定要在游泳池边为寻凶上门的威尔逊所杀?也许不为什么,只为一个似乎有利于毁灭盖茨比的情节,作家造就一个传奇然后再毁灭传奇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在毁灭盖茨比这个传奇之前,作家接受着良心的煎熬,一段段貌似莫名其妙的插叙都在替说谎的盖茨比开脱,他当过兵,他去过牛津,他在自己神秘的身世上并非都在撒谎。但一切已经不能掩盖读者在目睹盖茨比灭亡时的不安和骚动,还有伤心,不管怎么说,在大人物盖茨比临死之前,读者都已经爱上了他。就像爱上另一个幻梦中的自我。
文学史上大概很少有这样的例子,用最烦琐的通俗小说路数去言情,结果写出了一部经典著作,盖茨比先生的身后令人肝肠寸断,他的葬礼上,所有曾经在他花园里纵情欢愉的男男女女都不见了,来的是他的父亲,一个寒酸纯朴的小镇老人。他没有分享儿子在世间的荣华,却随身保存着盖茨比先生年轻时的作息表。我斟酌再三,决定把这张时间表抄录下来,以此对我们这里探讨的一个人物盖棺定论,顺便怀念一个年轻人业已消失的青春,怀念一个小说人物(或许是真实人物)悲喜交加的一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