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
女人肯定不光是我一个人在画,以前“性”可能是一个非常忌讳的题目,不能做,不能说。但是不做不说是不是大家就都不想?不对。肯定很多人在想。
以我自己为例,“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十二岁,朦朦胧胧已经觉得跟女孩子在一块与跟男孩子在一块味道不一样了,觉得有意思。到了十五六岁或者十六七岁,对这个问题就更感兴趣。但是你想读到这方面的书,想看到这方面的画,很难,连读到跟这方面有关的零散文字都不太可能。我们当时换书有一种说法,这个书里面有相对多的有关性的描写,价值就大一点,《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要比《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大一些,因为写女人多一点。《静静的顿河》就可以换《战争与和平》,但你要拿《战争与和平》换《静静的顿河》,这就难说了。假如是《金瓶梅》,那就很厉害了,在我印象中,最高的市价是可以换一辆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凤凰牌自行车当时是176元一辆,还要几百张工业券等,176元差不多是南京市省厅级的工资了,可能还没这么高,现在的概念差不多小十万了。全部原因就是它描写性多一些。
那时候我们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好奇加上生理因素推动。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南方来信》中描写美国鬼子怎么强奸越南妇女之类的,这么厚一本书里面大概只有两三行,谁都背得出来,第几页第几行,这些都会作为黄色小说的经典,被大家传阅。还有一种黄色读物的来源,是马路上的布告,流氓犯强奸女人,为了写他的罪行,里面会有一两句描写,大家都伸着脑袋看。所以那个时候对这种东西很感兴趣,由于兴趣的强烈,可能画得就特别投入。但是我从来都是自己在家里画,从没想过要拿出去给大家看。这有点像卡夫卡写小说,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一天要发表,只是写着玩。有人问,你又不想发表,又不想换钱,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卡夫卡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他说是为了减轻内心的压力。他内心有一种压力,迫使自己想写,为了使这种压力得到释放,他就写,写完了就往办公室抽屉里一塞。他一些好事的同事觉得很奇怪,不知道这家伙整天写的什么玩意,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抽屉弄开,翻出来看,发现写得非常好,就拿出去给他出版了,变成书。然后他自己在书店里翻书,一看这个书怎么这么像自己写的,后来一看真是他写的,就变成很有影响的文学事件。
我画这些东西只是为了自己快乐,不想给别人看到。最早拿出来是1985年,李世南到我这儿来。1985年11月份湖北武汉在弄一个中国画创新作品展,是“’85美术思潮”里面很大的一件事情。谷文达、江宏伟、周京新、徐乐乐和我,都是那次以后才出来的。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是谷文达,我的影响也比较大。李世南为了找展览的作品,跑到我这儿来,我就给他看了一些小的山水、花鸟,他说这些画得不错,但是听说你画好多女人,能不能给我看看。因为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不会出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展出,也就自己画着玩,我说可以给你看,但是好像不能展出。他说不一定,可以试试。我就拿了几张裸体女人的小画给他,后来他就说拿去试试。他们展览会的作品都是放在镜框里,评委喜欢,但是领导不一定通过。李世南选了五张,其中有两张比较一般,女孩子穿衣服,但画得比较性感,他就把那两张脸朝外放。还有三张比较过分,基本上没穿衣服或衣冠不整,他就把这三张装好以后,装作很无意地把玻璃朝着墙放,没有上墙,就跟领导说画都装好了,你们看一下,你们觉得行我们就挂了。有的镜框是背朝着他们,领导也懒得翻过来,觉得就那么回事,好,你们挂吧。
挂完以后,我的画引起很大争议。当时周思聪指着我那几张小画说,这几张画是我这么多年来看过的最好的中国画。叶浅予很不高兴,说你看看他都在画什么,你还说是你看过的最好的。周思聪就吓到了,说,我没注意他画的是什么。她怎么可能没注意呢?然后叶浅予就大跳起来,到处去说。展览的名字叫中国画创新作品展,他说这哪里是创新,这是复辟,是封建糟粕,我们继承传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继承的恰恰是糟粕。周思聪吓得不敢说话。
当时刘骁纯是《中国美术报》的主编,化名砚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朱新建的挑战性》,说叶浅予老先生认为他这种画是糟粕,而我们认为凡是创新的东西都是具有挑战性的,朱新建的这种中国画是具有挑战性的。其实我当时不是为了这个意义,但是真正发表并引起争论后,最起码有了这个意义,就是我喜欢中国画文雅的笔墨情趣。
其实中国对性的禁忌不是从那时开始,儒家、宋理学就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传统的文人画里面很少看到对于性的描写,只能在一些民间的插图或春宫图里看到。而这些画得其实并不好,严格讲中国传统的春宫图不如日本的好,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忌讳。当时由于特殊的社会情况,“文革”太压抑这个东西了,我就特别希望能用中国画的办法把中国式的性感表达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一个东西被压抑得太厉害,实际上它反过来就很凶。中国传统文化在性的方面反过来也很凶,包括《金瓶梅》、《肉蒲团》这些书,其实写得都很好,我就是对这种所谓反动的东西特别感兴趣。
我突然用文人画的笔墨画这种性感,画得又很自如。其实严格说,叶浅予他们三十年代是想干这事,但1949年以后,当时社会不可以弄这种东西,内心很痛苦,他必须说服自己,以前那个东西是不对的,不能弄。以前他们卡在这个关口上,中国解放前的几个很有成就的漫画家,叶浅予、张仃等,他们不在宣纸上画的时候,都非常有创新精神,画得非常自由,非常好。但只要一到宣纸上,都不行。因为中国画的传承太厉害了,当时像齐白石都被认为是野狐禅,根本就不是中国画。我认识上海的几个老先生,收藏世家,他们家里原来藏画,我说你们怎么不藏齐白石的画?我那个朋友他爸爸或是爷爷就说,齐白石算什么?我们怎么会要齐白石的画?我说那你们都要谁的画,他说,八怪里我们最多也就要一个半个。比如黄瘿瓢(黄慎)的某几张画我们要,金农的一部分画我们要,其他就不要了。而海派就根本不看了。往上说到石涛也不是张张都要,再往上的话,宋元才算有点意思。
像叶浅予、张仃、张光宇,一拿到毛笔就觉得这玩意太神圣了。你去看叶浅予,他一画到宣纸上就小心翼翼。我不是说他不对,是说他认真,对这个画种有由衷的崇敬心理,因为这个传承太厉害了。现在演艺圈的人很了不起,可按照以前的说法,叫戏子,没有饭吃了,跟叫花子差不多的人才去干这事,这就是以前的价值观念。但是诗、书、画、印一直排在很高的位置。所以叶浅予他们这拨人在画漫画、画铅笔速写的时候非常自由,画得非常精彩。但是我仔细看,他们只要一落在宣纸上,马上傻眼。张光宇在普通的洋画纸上,神气得要命,这样画,那样画,嬉笑怒骂,全是文章,但一到宣纸上马上画得跟陈老莲一样,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不敢动。就像有人讲张仃的画,主要指他的装饰画或彩色的漫画,说张仃是“毕加索加城隍庙”。当然这是“文革”批判他的时候。但我们仔细想想,毕加索倘若真正和城隍庙加在一块,这个画太厉害了。他的一些装饰画和彩色漫画确实有这个倾向,但没有到这么厉害的程度。但张仃一画到宣纸上,就很简单、很单调了,就是在宣纸上用一层焦墨,画一个山水的轮廓,其实笔墨都谈不上,也是很小心,画得很拘谨。
我说的意思是,他们这些人都没有突破宣纸,而恰恰是叶浅予多少年之后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我当时三十三岁),一个三十来岁的人画中国画竟然敢这么肆无忌惮,把他们一辈子做梦都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就这么轻而易举、不知道天高地厚地弄起来了。他肯定受不了,一下子就跳起来了,天天在美术报底下骂。其实当时年轻人画什么的都有,他根本一个都不会看在眼里,就对着我的画天天骂,说你们来辩论吧,朱新建究竟是创新还是复辟?
后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国画艺委会,专门为我这个事开过几个讨论会,其中有一个讨论会我参加了,周思聪就跟我说,朱新建,能不能就叶浅予先生对你的批评发表一下你自己的观点?我说了三条,第一,叶浅予先生本人的艺术成就我是很钦佩的,叶浅予是我很景仰的前辈艺术家。我之所以到今天,其实跟叶浅予有很大关系,叶浅予的画我到现在都可以背了,不信拿纸拿笔来,叶浅予很多速写我可以画给你看,一模一样。我个人是在叶浅予身上下过很多功夫的,叶浅予速写画得非常好,对女人的造型很有研究,画得很好。叶浅予肯定是我基本造型因素里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画成今天这样,也是学了叶浅予不少东西。第二,像叶浅予这样的前辈艺术家,能对我们后生晚辈的作品这么关注,我表示感谢。第三,叶浅予的知识结构、时代背景等很多东西,跟我的都不一样,所以我和叶浅予先生的价值、趣味等也会不尽相同。这种不尽相同,我希望你们这些作为领导的人能够容忍。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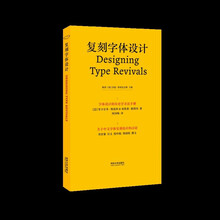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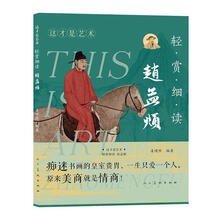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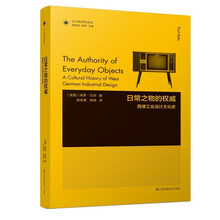



——王朔
★回看新建的作品,我想起费舍尔对罗丹的带有嫉妒之心的敬意。
——陈丹青
★我觉得一个弄文字的人弄出来的文字也没他好看。
——陈村
★武侠小说中有一种境界,叫独孤求败,朱新建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想来也是去之不远。
——叶兆言
★去冬朱爷羽化,眼看就要一年。多次梦见他痊愈,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回过头来和我讲笑话。有次实在太真,我醒来很久,还在琢磨天亮了,要打圈电话给村长老费江芮报喜。慢慢回过神来,想我们这位爷,吃饭走路,从不等人,脾气急得很,所以这一走,也是不等你们,一个人自在玩耍去也的意思。
——郁俊
★相对于他的画而言,这些文字应该算是他某种形式上的原形,或深或浅地折射出一些画里未尽的意思。
——朱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