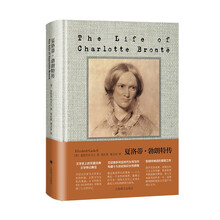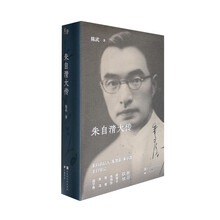仰慕他的人津津乐道于这面具人格,诋毁他的却要揭开面具,只为搜寻底下的缺陷:他们都没有看到的是,对于这个惯走极端的人,德行与过错几乎不分彼此。这个忠于“我们心中的自我”的青年在1925 年还默默无闻时就下定了不为自己立传的决心。他恳求身边亲密的人保持缄默,也将许多信件封存至下个世纪。但与此同时,他也构想着自己的传记,在接连的诗作里浓墨重彩地刻画一个将自己的人生看作灵魂求索的形象,全然不顾与宗教格格不入的时代基调,不顾来自女人、朋友与其他职业令他分心的召唤。他曾提到一个努力向自我解释“一系列事件在信仰里最终达成”的人,在一封1930 年的信中也写到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即尝试探索灵魂自传(spiritual autobiography)这一在二十世纪已经失传的文体。
“一刹那果决献身的勇气,”他在《荒原》中写道,“我们就凭这一点,只凭这一点而存在。”这本书的确描述了诗人生活的外部事实,但这些事实仅用以支撑那些塑造他作品的内在经验,后者对他来说才是决定性的。只有精简关于生平的琐碎细节,才可能勾勒出艾略特事业轨迹的延续性,将诗歌与生活看作一个整体图景中互为补充的部分:这个整体图景,就是诗人对救赎九死不悔的追求。贯穿他一生与创作生涯的是,艾略特对灵魂传记崇高情节的不懈践行。那是在《出埃及记》中就奠定了的情节:逃离文明,在荒地上经受漫长的苦难,随后进入应许之地。用繁冗的细节遮蔽这主要的故事情节无疑是南辕北辙,这也是为何对艾略特来说,一份巨细无遗的传记并不适用于理解他的人生。
艾略特1905 到1906 年就学新英格兰首屈一指的寄宿学校弥尔顿学院期间,以及后来在哈佛的日子里,都为走上家庭期望的职业道路做着准备,但他却逐渐感到诗的召唤压倒了家族的期许:“文学艺术迫使人抛下他拥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整个家族―而孤身去追随艺术。因为艺术要求人既不属于他的家庭,也不隶属于他的阶层、党派、圈子。他只能纯粹是他自己”。1915 年,艾略特决定留在伦敦而非回到哈佛完成博士论文,几年里只写了些零散地见诸冷门杂志上的诗歌,这让他的父母不解又忧虑。父亲1919 年去世时,还认为这个小儿子毁了自己的人生。然而,艾略特虽有反抗,然而,艾略特虽有反抗,他的职业生涯倒也暗合了家族的模式:他先是像父亲早年在密西西比州一样做了个贫困潦倒的职员,后来从事出版业,成了成功的出版商。他终其一生兢兢业业对待每日的劳作,这也正是每一代艾略特家族的成员借以自我肯定的方式。
1910 年,艾略特在东格洛斯特度暑假期间,决定将自己未发表的诗歌辑录起来。他从波士顿的老角书屋买了本大理石花纹的笔记本,在上面题写了诗集的名字―“三月野兔创意曲” ―并在里面抄录了年1909年11 月以来实验性较强的一些诗。(艾略特未收入更早发表在《哈佛呼声》里的诗。)这个笔记本跟随他在巴黎度过了随后的一年,又随他回到哈佛,最后与他一起在1914 年来到伦敦。他同时还漫不经心地保留了些粗略的草稿,以及他1913 至1914 年间购买打字机后一些诗作的打字稿。在这期间,艾略特积累了大量的诗作,其中有些还相当出色。他以惊人的耐心与自律保存着这些诗作,从未试图发表。1914 年,稍长于艾略特的庞德遇到这位美国青年,惊叹他全凭一己之力把自己训练成一个现代诗人。即使在这些最初的作品中,艾略特也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核心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