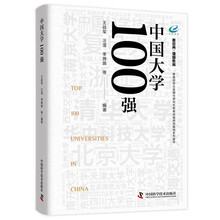一个晚春的下午,四年级白人男孩加勒特·塔林格正在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里,笑着喊着,击水嬉戏。他家住在市郊一座有四间卧室的小楼里。和大多数傍晚一样,快速吃过晚饭他的父亲就会开车带他去参加足球训练。踢足球只是加勒特参加的众多活动之一。他的弟弟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场棒球赛。这两个男孩的父母在有些傍晚也还是可以放松下来慢慢去品味一杯葡萄酒的,但今晚却不是这样一个夜晚。当他们匆匆换下工作服并帮孩子准备好去训练时,塔林格先生和他的太太显得很忙乱。
离这里开车十分钟之遥,四年级黑人男孩亚历山大·威廉斯刚参加完学校的家庭招待会,正在回家的路上。他的母亲开着一辆米黄色皮革装潢的丰田雷克萨斯。当时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9:00。威廉斯女士下班后已经很累了,而且第二天还有一个日程很满很忙的星期四在等着她。她一早4:45 就得起床出差去另一个城市,一直到当晚9 :00 才能回来。星期六早上8:15 她还要开车带亚历山大去上钢琴课;课后去唱诗班排练,跟着再去参加一场足球赛。当他们在黑暗中驱车前行时,威廉斯女士轻声地和她的儿子谈着话,问他一些问题,并引他讲出自己的观点。
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问题是中产阶级家庭抚养孩子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很多中产阶级家长一样,威廉斯女士和她的丈夫也认为他们是在“发展”亚历山大的能力,是在以一种协作方式培养他的才干。由父母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支配着像加勒特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通过确保他们的孩子拥有这些和更多其他经历,中产阶级家长参与了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中产阶级家庭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这种优越感在制度环境中扮演着尤其重要的角色;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这些制度环境中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讲话。
从这里再往前驱车二十分钟,在一个蓝领工人居民区,以及再稍远一点,在一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公租房社区,孩子们的童年看起来有很大不同。一位白人工人阶级父亲扬内利先生开车到课后加时班去接也在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小比利。回到家,小比利先看了会儿电视,然后跑去街上骑车玩耍,与此同时扬内利先生则在喝啤酒。没有课后加时班的晚上,小比利会和他爸爸坐在屋外路边打牌。小比利母亲的工作是帮人打扫房间,她下午5:30 左右下班回家。她做好晚饭后,全家一起共进晚餐。大家庭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扬内利女士每天都会打电话跟“ 整个一大家子”联络。多数晚上小比利的叔叔都会来串门,有时还会把小比利最小的表弟带来一起玩。春天的时候,小比利在当地一个棒球队打棒球。与每周至少参加四项活动的加勒特和亚历山大不同,对小比利来说,棒球是他整个学年中唯一有组织的课外活动。这条街下边,白人女孩温迪·德赖弗也是工人出身,她也是和她的表姐妹们一起度过傍晚时光,一起挤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边吃爆米花边看录像。
更远一些地方,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四年级黑人男孩哈罗德·麦卡利斯特正在外面玩耍。他住在那个由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社区。那天晚上,他的两个表兄弟也在那里,他们经常来找哈罗德玩。整个下午他们都想找个篮球玩但却没找到,之后他们便干脆坐下来看电视体育节目。现在已是黄昏,他们又跑出去用装满水的气球打闹。哈罗德想把他的邻居拉蒂法小姐给浇湿了。人们坐在这排单元房外的白色塑料草坪座椅上。音乐和电视声在敞开的门窗间飘来荡去。
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身边的成年人都想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经济上的艰难困窘使得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成为这些家长的主要生活任务,他们要挣钱糊口,安排住处,克服住处附近的不安全环境,带孩子去看医生(常要久久地等候那些根本就不会来的公交车),给孩子洗衣服,催孩子按时睡觉,帮孩子第二天一早准备好东西上学。但与中产阶级家长不同,这些家长并不认为协作发展孩子的能力(尤其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而实现的协作培养)是教育好孩子的必要因素。与塔林格家和威廉斯家不同,这些母亲和父亲并不看重协作培养。对他们来说,为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并不在于要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感想、观点和思想。相反,他们认为大人与孩子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些家长倾向于下达指令:他们会直接告诉自己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而不是给出理由来说服他们去做事情。和与他们对等的中产阶级孩子不同,这些工人阶级出身的孩子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那些固定的由大人为他们安排的活动,他们对自己业余活动的特性有更多控制权。大多数孩子都跟自己的小朋友和亲戚住得很近,都能自由外出并和这些亲戚朋友玩耍。他们的家长和监护人推动了他们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然而,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仍然需要与像学校这样的社会核心机构配合互动;而这些社会核心机构又都坚决果断地推崇以协作培养方式教养孩子的策略。对工人阶级家庭和贫困家庭的父母来说,他们在家中教养孩子的逻辑与教育机构的标准是不同步的。其结果就是,采用协作培养策略的家长,他们的孩子看起来就获得了一种优越感;而像小比利、温迪和哈罗德这样的孩子,看起来就在他们的机构体验中得到了一种形成中的疏远感、不信任感和局促感。
美国也许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一片不平等的土地。本书确认了,父母的社会地位会以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但又是强有力的方式冲击着孩子的人生经历;而本书就标识出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影响教育方式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