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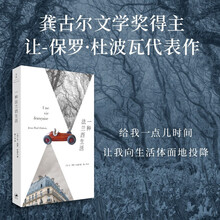

日本“无赖派”文学大师太宰治完整代表作集结,一部纯粹的“私小说”,太宰治的灵魂之书。
太宰治是日本文学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家,他39岁便自杀身亡,一生命运多舛,良作颇多,《人间失格》是他人生中的收官之作,很具有研究价值。
五次自杀,天鹅绝唱,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的颓废,毁灭式的绝笔之作。
《人间失格》是日本小说家太宰治颇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品,发表于1948年,是一部自传体的小说。纤细的自传体中透露出的颓废,毁灭式的绝笔之作。太宰治巧妙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借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在发表该作品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为自己画下一个句号。
早晨,母亲在饭厅里嘬了一小口汤后,轻轻地“啊”了一声。
“汤里有头发吗?”我觉得肯定是什么讨厌的东西掉进汤里了。
“不是的。”母亲若无其事地又轻盈地嘬了口汤,然后转头欣赏起厨房外盛开的野樱花来。她就那么侧头看着窗外,一小口一小口轻盈地嘬着汤。用“轻盈”二字来形容母亲喝汤一点也不夸张。她喝汤的方法和女性杂志上提倡的喝法完全不同。
弟弟直治有次喝着酒给我说:“现在的贵族不一定都有爵位,那些没有爵位的绅士才是真正的贵族呢!而像我们这样有爵位的人其实已和平民无异。岩岛(直治的同学,拥有伯爵爵位)他们比新宿街头的皮条客还粗俗。前两天,柳井(直治的同学,子爵的二儿子)的哥哥结婚时,竟然穿着无尾小礼服!真是的,现在谁还穿无尾小礼服呢?更滑稽的是,那家伙祝词时竟然还用‘go za i ma su ru’(以前日语里的郑重表达,用于句末,现在已不常用)的说法呢。那种虚张声势、装模作样的样子真让人作呕。还有,在本乡一带经常会看到写有‘高级住宅’的牌子,其实住在那里的华族大部分只是高级乞丐而已。真正的贵族才不会像岩岛那样装腔作势呢。而在我们家里,恐怕只剩妈妈是贵族了,其他人再怎么学都是学不来的!”
的确如弟弟所言。就说喝汤吧,一般我们都是俯下头,横握着汤勺把碗里的汤送进嘴里,可母亲却是用左手轻轻扶着餐桌,昂头挺胸,看也不看汤碗,像蜻蜓点水一样,右手横握汤勺轻轻舀一勺汤,然后让汤勺和嘴巴呈九十度,悄无声息地、一滴不漏地把汤轻盈地嘬进嘴里;同时她还能平静地旁顾左右,手里的汤勺就像小鸟的翅膀一样,一张一合很自如。这种据说合乎传统礼仪的喝法,看上去非常可爱,好像还能增加食欲。不过,就像弟弟直治所说的一样,我只是一个高级乞丐,无法像母亲那样轻盈地、自如地使用汤勺,只会俯下身去,用不合礼仪的方法喝汤。
除了喝汤,母亲很多吃饭的方法都很神奇。吃肉的时候,她会用刀叉快速将肉块全部切成小块,然后放下叉子,只用右手一小块一小块叉着吃;还有吃带骨头的鸡肉时,当我们还在发愁如何从骨头上取下肉时,只见母亲不慌不忙地用手拿起骨头,直接就用嘴咬着吃了起来。这种看似野蛮的吃法,一到母亲这里就变得又可爱又性感,让人不得不感叹“真正的贵族就是不一样”。另外,母亲吃菜里的火腿和香肠时,也会直接用手拿起来吃。
母亲曾经对我们说:“你们知道饭团为什么好吃吗?告诉你们,那是因为它是人手直接捏出来的!”
有时我也觉得用手直接吃饭很香,可我这种高级乞丐就是模仿不了。有时试着模仿一下,反而感觉自己就是真乞丐。
真的,不光弟弟,我也觉得模仿母亲太困难了,最后我们都以放弃作罢。曾经在一个月光明亮的秋夜,我和母亲坐在西片町我家后院池塘边的小亭子里,一边赏月,一边聊着狐狸娶妻和老鼠娶妻有何不同等闲话。突然母亲起身钻进了小亭子边的小树丛中。接着她从白色的胡枝子花丛中探出嫩白的脸庞,冲我笑着说:“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
“您在折花吗?”
“我在撒尿。”她小声笑着说。
可奇怪的是,那时她根本就没蹲下去啊!虽然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但依然觉得她很可爱。
我记得之前读过的一本书上说,法国路易王朝时代的贵妇人,经常会满不在乎地在皇宫的院子或走廊的角落里撒尿。那种满不在乎让人感觉很可爱,这点和母亲很像。因此我觉得母亲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贵族式的妇人了。
再接着说早上喝汤的事。母亲喝了口汤后“啊”了一声,我问她汤里是不是有头发,她说不是。于是我接着问:
“那是汤咸了吗?”
今早的汤是把美国配给的青豌豆罐头过滤后做成的法式浓汤。我一直对自己的厨艺不自信,尽管母亲说不是,我还是不放心,接着问了一句。
“汤很好喝!”母亲很认真地说。喝完汤后,她又用手直接捧起紫菜饭团吃了。
小时候,早上十点前因为肚子不饿,常常不想吃早饭。经常喝完汤后,用筷子把碟子里的饭团戳碎,再用筷子扎一块,像母亲喝汤一样,让筷子和嘴巴呈九十度,像小鸟啄食一样一点一点啃着吃。通常,母亲先吃完后就靠在洒满阳光的墙上,默默地看我吃。
“和子,你又不想吃了吧?你可得好好吃早饭啊!”
“妈妈,你觉得早饭香吗?”
“我没有病,当然觉得香了。”
“可我也不是病人啊?”
“不许这么说!”母亲苦笑着摇头指指我。
五年前,因平时生活不注意,我曾一度患肺病卧床不起。这一直让母亲非常担心。其实母亲最近的身体才让人担心和不安呢。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啊”地叫了出来。
“你怎么了?”这次把母亲吓了一跳。
我看着母亲,感觉她和我心心相通,不由得“哈哈”笑了出来。看见我笑,母亲也跟着微笑起来。
当强烈的羞耻心袭来时,我总会莫名其妙地“啊”一声叫出来。刚才我又清晰地想起了六年前离婚的一幕,才忍不住叫出来。不知母亲刚才为什么会“啊”地叫,她可没有和我一样羞耻的过去,难道是因为别的事?
“妈妈,您刚才是不是想起什么事了?”
“我忘了。”
“是我的事吗?”
“不是的。”
“那是直治的事吗?”
“好像是吧。”母亲歪着头,思索着说。
弟弟直治大学还没毕业,便应征入伍去了南方的小岛。去了后音讯全无,战争结束后仍然下落不明。母亲悲观地认为再也见不着他了,可我却不那样想,我一直坚信他会回家的。
“本来我早就死心了,可我刚才喝汤时又突然想起了他,便忍不住叫出了声。早知道他回不来,当初就应该对他再好点。”
直治上了高中后,开始迷恋文学,整个人也成了不良少年,不知让母亲操了多少心。可即便这样,母亲喝汤时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母亲的话让我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妈妈你放心,直治会没事的。通常来说,只有老实、漂亮、善良的人才会早死,像直治这种坏人才不会轻易死的,就是用棍棒打也打不死。”
听了我的话,母亲笑了:
“照你那么说,和子你岂不是早死的那类人吗?”
“才不是呢!我可是一个大脑门坏人,活到八十岁也没问题!”
“要那样的话,我也会活到九十岁的!”
“会的!”
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却直犯嘀咕。我怎么能对漂亮的母亲说长相漂亮的人会早死呢!我不是一直希望她能长寿吗?啊!心里好难过。
“妈妈,您可真会开玩笑!”我声音颤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曾发生过一些和蛇有关的故事。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邻居家的孩子们在院墙根的竹丛里发现了十几个蛇蛋,他们都说是蝮蛇的蛋。我害怕将来竹丛里孵出十几条蝮蛇的话就没办法去院里了,就鼓动孩子们说:“咱们用火烧了它们吧!”
在我的鼓动下,孩子们高兴地跟着我从竹丛里捡来树叶和干柴,点着后把蝮蛇蛋一个一个扔了进去。可蝮蛇蛋在火里怎么也烧不着,没办法,孩子们又捡来更多的树叶、树枝把火烧得更旺,可即便这样,蝮蛇蛋还是没烧着。
这时,一位农家的小姑娘正好从墙外经过,看见我们后笑着问:
“你们在干什么呢?”
“我们在烧蝮蛇蛋呢,不然蝮蛇孵出来的话会咬人的。”
“你们烧的蛇蛋有多大啊?”
“和鹌鹑蛋一样大,是雪白色的。”
“要是那样的话,你们烧的就不是蝮蛇蛋,只是普通的蛇蛋。生蛋是烧不着的。”说完,小姑娘就笑着离开了。
烧了三十多分钟,蛇蛋果然没烧着。于是我让孩子们把蛇蛋从火里拿出来,埋在了一棵梅树下,我还用小石头做了墓碑。做好后,我对孩子们说:
“来,咱们拜拜它们吧!”
我合掌祈祷,孩子们也听话地跟在我身后合掌祈祷起来。和孩子们分手后,我独自一人沿着石阶往家走。刚一走上台阶,就看见母亲站在树荫下默默地看着我。
“你做了一件可怕的事啊!”
“我本以为是蝮蛇蛋呢,原来只是普通的蛇蛋。不过我已经埋了,没事了。”
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真不愿让母亲看到这一幕。
其实母亲一点也不迷信,只是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家里去世后,她就开始害怕蛇了。父亲临终前,母亲在他枕头边看见一根细黑线,正要捡起来时,才发现是条小蛇。那条小蛇爬到走廊后就不见了踪影。当时只有母亲和和田的舅舅看见了这一幕,他们害怕引起大家的恐慌,就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当时也在旁边,可对蛇的事却一无所知。
父亲去世的那天傍晚,我在院里池塘边的树上又看到了一条蛇。我今年二十九岁,十年前父亲去世时正值十九岁,已经是大人了,所以对十年前发生的事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到院里池塘边的树丛中准备剪些花来祭奠刚去世的父亲。刚走到一棵杜鹃树下,一抬头就发现枝头上爬着一条小蛇。我吓了一跳,想在旁边的棣棠上重新折一根花枝,却发现棣棠上也爬着一条蛇。旁边的木樨花树、枫树、金雀儿树、紫藤以及樱花树上都爬满了蛇。当时我并不十分害怕,只觉得它们是为了祭拜我去世的父亲,才悲伤地从洞里爬出来罢了。当我把在院里看到蛇的事情告诉母亲时,她只是默默低头思忖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这两件和蛇有关的事情发生后,母亲就开始讨厌起蛇来。说是讨厌,其实是尊崇和害怕的心理混合成的一种敬畏。
烧蛇蛋的事被母亲发现后,我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因为这一定会让母亲觉得我们会遭到报应。
可就在我为烧蛇蛋的事而提心吊胆时,今早我在饭厅又随口说出了美人早死这句不该说的话。说完后才发现话一旦说出来就再无法收回了,我后悔得直想流泪。吃完早饭,我一人在厨房收拾时,突然觉得自己的胸口盘踞着一条想诅咒母亲短命的小蛇,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那天我在院里又碰见了蛇。当时风和日丽,我在厨房收拾完后,就想搬张藤椅去草坪上打毛衣。可藤椅刚搬到院里,就看见石头缝里有条蛇。唉,真讨厌,我想都没想,又搬着藤椅回到后檐下,坐在后檐下开始打毛衣。下午,我打算从堆在院角佛堂里的藏书中找一本洛朗桑的画册看看,可刚一进院子,又看见一条蛇在草坪上蜿蜒爬着,好像和上午看到的是同一条。那条蛇身材匀称、举止高雅,应该是条母蛇。她静静地爬过草坪,爬到树荫下时慢慢抬起头,嘴里吐着细信,像燃烧的火焰似的。环顾四周后,她又忧郁地低头向前爬着。我往佛堂走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条美丽的母蛇。当我从佛堂拿出画册再次经过草坪时,已不见那条蛇的踪影。
黄昏时分,我和母亲在中式的客厅里喝茶时,一抬头,又看见早上的那条蛇出现在第三级石阶附近。母亲看见后,赶忙起身来到我身边,抓住我的手颤抖地说:
“不会是那条蛇吧?”
“您是说被我烧了蛇蛋的母蛇吗?”
“是,是的。”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我俩手握着手,屏息静气地看着那条蛇。她忧郁地盘卧在石阶上,过了一会儿,开始晃晃悠悠地爬动。她无力地横穿过石阶后,爬进了燕子花丛中。
“你看我怎么说来着,她在找自己的蛋吧!真可怜!”她声音低沉地说。
听她这么说,我只得干笑两声。
夕阳透过窗户照在母亲的脸上,让她的眼睛微微泛着蓝光。她幽幽嗔怒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异常美丽。我突然觉得,母亲的表情竟和刚才那条蛇的表情出奇相似。而盘踞在我内心的那条丑陋的蝮蛇却不知为什么总想杀死那条美丽而忧伤的母蛇!
我搂着母亲柔软纤细的肩膀,内心不禁生起了一股无名的悲伤。
我们卖掉东京西片町的房子,搬到伊豆这座中式的山庄时,是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去世后,我家的生活开始仰仗母亲唯一的至亲——家住和田的舅舅来管理。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整个社会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田的舅舅劝母亲说,最好卖掉房子,辞退用人,母女二人在乡下买一栋漂亮的房子住比较安全。听到舅舅的话,管理金钱的能力还不如小孩子的母亲便赶紧央求舅舅帮我们办理。
十一月底,舅舅来信说,骏豆铁路沿线有一栋河田子爵的别墅要出售。那栋别墅建在高坡处,景色优美,还带有一百多坪的田地。当地盛产梅子,冬暖夏凉,很适宜居住。因为买家要求见面,所以请母亲明天去他在银座的事务所。
看了信后,我问母亲:“您去吗?”
“拜托别人的事当然要去了。”她无奈地苦笑着说。
第二天午饭后,母亲在我家以前的司机松山先生的陪同下,去了银座。晚上八点左右,才被松山先生送回家。
“我已经说好了!”她冲进我的房间,扶着桌子一屁股坐下后兴奋地说。
“说好什么了?”
“全都说好了。”
“可是……”我很吃惊,“还没看房子您就……”
母亲用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手掌轻轻拍着额头,叹了口气。
“你和田的舅舅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觉得直接搬过去不会错的。”母亲抬头笑着说,她的脸庞愈加显得端庄秀丽。
“一定不会错的!”母亲对和田的舅舅的信任感也感染了我,我也附和着说,“我也觉得用不着看。”
说完我便和母亲会心地大笑起来,笑完后却又满心惆怅起来。
之后家里便每天都有工人来收拾行李,做搬家的准备。和田的舅舅也来家里把该处理的东西陆陆续续都变卖了。我和女佣阿君一起整理衣物、在家门口烧垃圾,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只有母亲一人既不帮忙收拾东西,对搬家的工人也不闻不问,每天躲在屋里不知在干什么。
“您在忙什么呢?是不是不想搬到伊豆去啊?”我忍不住问母亲。
“我没事。”母亲含糊地答道。
经过十几天的忙碌,搬家前的准备工作终于妥当了。傍晚时分,我和阿君在家门口烧垃圾时,母亲从屋里出来,站在屋檐下默默地看着我们。寒冷的西风把灰色的烟雾吹得离地面很低。我抬头看见母亲的脸色很难看,不禁有些担心。
“妈妈,您的脸色可不好啊!”
“我没事。”母亲强挤出一丝微笑,说完便转身进屋去了。
因为被褥都已整理打包了,当晚阿君睡在二楼客厅的沙发里,我和母亲也盖着从邻居家借来的被褥凑合了一晚上。
“唉!”母亲无力地叹了口气,“因为有和子,我才会去伊豆的。”
听母亲这么说,我大吃一惊。
“要是没有我呢?”
听我这么问,母亲突然哭了起来:
“我干脆死了算了,这样就会和你父亲一样,能死在这个家里了!”她哽咽着说,哭得更厉害了。
母亲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得如此软弱过,也从未在我面前哭得这么伤心过。父亲去世时、我出嫁时、我离婚后怀着孩子再次回到她身边时、后来孩子在医院生出就已夭折时、我卧病在床时以及弟弟直治做了坏事时,她都没这么难过过。父亲去世后的这十年间,母亲依旧高雅温柔,和父亲在世时没有任何变化。我和弟弟也在她的爱护下快乐舒心地生活着。可慢慢地,母亲手里的钱越来越少,为了我和直治,她花了太多的钱。这让我们母女俩最后不得不搬出长期住惯的房子到伊豆,去过寂寥的乡下生活。要是当初母亲对我们再严厉点,给我们钱时再手紧点,她就不会这么拮据。就算世道再怎么变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让她伤心。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人没钱是这么痛苦,就像掉进恐怖、悲惨的地狱一样!我胸口憋闷,内心极度悲伤,想哭又哭不出来,只能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像块石头一样默默发呆。所谓人生的苦难,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第二天,母亲的脸色依然异常凝重,她故意磨磨蹭蹭,好像想在这个长期住惯的家里多待一分钟。见她这样,和田的舅舅便催促说,行李已全部运走了,今天必须动身去伊豆。听舅舅这么说,她才慢慢穿上外套,向前来送别的女佣阿君和其他人默默点点头,和舅舅、我三个人出了西片町的家门。
前往伊豆的火车比较空,我们三人都坐了下来。在火车上,舅舅很兴奋,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母亲脸色依旧很难看,她低着头,好像很冷似的蜷缩着。在三岛换乘骏豆线,在伊豆长冈站下车后,我们又坐了十五分钟的汽车,之后沿着缓缓的山坡朝山里走。不久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小村落的旁边便是我们买下的中式小别墅。
“妈妈,这儿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兴奋地叫道。
“是啊!”母亲站在小别墅的门前,脸上的表情一下高兴了起来。
“住在这里的第一个好处是空气很清新!”舅舅自豪地说。
“的确,”母亲微笑着说,“这里的空气真香!”
听母亲这么说,我们三个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进门一看,从门口到屋里都堆满了从东京运来的行李。
“住在这里的第二个好处,是起居室外面的景色非常漂亮!”一进门,舅舅便拉着我们坐在起居室看外面的景色。
那时正值午后三点,冬天的阳光柔和地洒在院里的草坪上。顺着草坪尽头的石阶望去,只见一个小池塘的边上长满了梅树。再往远处是一片橘园,橘园的尽头是村里的大路,大路的旁边是稻田,稻田的尽头是一片松树林。透过松树林,能看见湛蓝湛蓝的大海。坐在起居室水平看去,大海的高度正好与我的胸口持平。
“从这儿向外看,景色真柔和啊!”母亲悠悠地说。
“恐怕是和这儿的空气有关吧。阳光也和东京完全不同,柔和得就像用绸绢滤过一样!”我兴奋地说。
这个小别墅里有一个十榻榻米的房间、一个六榻榻米的房间,一个中式客厅,一个三榻榻米大的玄关和一个同样大小的洗澡间,还有饭厅和厨房。再加上二楼带有大床的洋式客房,这么大的房间就是弟弟直治回来也够住了。
舅舅去村里唯一的旅馆要了吃的。不一会儿,便当送来了。舅舅喝着自带的威士忌,愉快地给我们讲述小别墅的前主人河田子爵游历中国时的奇闻异事。可母亲只动了两筷子就不吃了。
天黑时,母亲轻声说:“我想稍微躺一下。”
我赶紧从行李中找出被褥让她躺下。担心她身体不舒服,我又找出体温计给她量了体温,发现她已高烧到三十九度。
舅舅也很紧张,他赶紧去下面的村落请医生。
我拉着母亲的手,哽咽地叫着:“妈妈!”可母亲的反应很迟钝。
我突然觉得母亲和我两个人太可怜了,便难过地哭个不停。我甚至想和母亲一起死了算了。从东京西片町的家搬出来后,我们的人生意义就已画上了句号。
两小时后,舅舅请来了村里的医生。医生是位老者,他身着仙台平袴,脚穿白袜子。给母亲做完检查后,他不是很确定地说:
“可能是肺炎,不用太担心。”
说完,给母亲打了一针后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的烧还没退。和田的舅舅留下两千日元并嘱咐我如果母亲的烧不退需要住院时要给他发电报后,当天便返回东京了。
我从行李中找出厨房用具,熬了点粥给母亲喝。母亲躺着喝了三汤勺就摇头说不喝了。
午饭前,村里的医生又来了。这次他没穿仙台平袴,不过脚上依然穿着白袜子。
“我母亲需要住院吗?”我着急地问。
“那倒没必要。今天我给她打一次强效针烧就应该退了。”医生的说法依旧不是很确定。打完针后他就回去了。
或许是那一针强效针奏效了,午饭后母亲的脸通红,并开始大量出汗。换睡衣时,母亲笑着说:“那位医生可真是位神医啊!”
我给她一量体温,三十七度,烧退了。我很高兴,便到村里的那家旅店买了十几个鸡蛋,回来煮到半熟端给母亲吃。母亲一口气吃了三个煮鸡蛋,还喝了半碗粥。
第三天,村里的医生穿着白袜子又来了。我告诉他昨天打完那针强效针后,母亲的烧已经退了。听了我的话,医生只是自信地点了点头。再次仔细地做了检查后,他对我说:
“老夫人的病已经全好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医生的说法听起来很滑稽,我强忍着没笑出来。
送走医生,我回到起居室一看,母亲已经自己坐了起来。
“真是神医啊!我的病已经全好了。”母亲小声嘟囔着,心情看起来很轻松。
“妈妈,我打开窗子吧,外面正下雪呢!”
窗外正纷纷扬扬下着鹅毛大雪。我打开拉窗,和母亲并排坐着,透过玻璃窗欣赏起外面的雪景来。
“我的病已经全好了,”母亲又自言自语道,“坐在这儿,我感觉往事都像在做梦一样。其实打心底我是不愿搬到伊豆来的,我真想赖在西片町的家里不走,哪怕是半天呢。在来这儿的汽车上时,我觉得自己只剩半条命了。刚到这儿时心情还可以,可天一黑,就开始怀念起东京的家了,心里一焦急,头就晕得不行。我这次生病可非同寻常,这可是老天爷让我脱胎换骨的一个过程啊!”
从那天开始,我们母女两人便开始了平静的山村生活,村里的人对我们都非常好。从去年十二月搬到这里后的四个多月里,除了吃饭,我们每天都在屋檐下打毛衣、在中式的客厅里读书喝茶,基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二月梅花开时,整个村落都笼罩在梅花的花海里;到了风和日丽的三月,盛开的梅花会一直持续到月底。这段时间里,从早到晚,我们呼吸的都是梅花的香味。每次打开玻璃窗,浓浓的梅花香便会扑鼻而来。三月底起风的时候,梅花的花瓣便悄悄透过窗户,飘落在黄昏饭厅里的茶碗里。四月份,在屋檐下打毛衣时,我告诉母亲我打算自己种田,母亲说她会帮我的。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我和母亲就像她说的那样,已经脱胎换骨了。可毕竟我们常人无法像耶稣那样再次复活,母亲虽然那么说,可她在喝汤时依然会“啊”的一声想起弟弟,我也会时不时想起自己过去的伤心经历。
说心里话,有时我会觉得小别墅里的平静生活其实只是一个假象。它只不过是老天爷赐给我们的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因为我已预感到一些不祥的影子在逼近我们。母亲看似很幸福,其实正在一天天衰老。盘踞在我内心的蝮蛇为了吞噬母亲的生命,正在不断膨胀着,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唉,这样的日子我已经受够了,希望下一个季节快快到来,好让我们的日子能有所改变。正是在这种焦灼的内心驱使下,我才做出烧蛇蛋这种蠢事,结果让母亲更悲伤、身体更衰弱。
不说了,感情上的事是说不完的。
译者序 / 01
人间失格 / 001
序言 / 003
手记1 / 006
手记2 / 016
手记3 / 047
后记 / 091
维荣之妻 / 095
斜阳 /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