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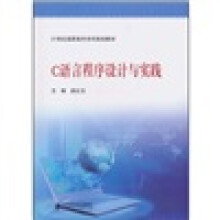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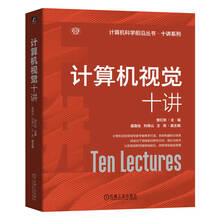





★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2018年力作。
世称辛神,近年著述颇丰。围绕2017年中蒙联合考察队在蒙古国杭爱山一带发现的东汉班固所撰《燕然山铭》石刻,辛德勇教授从学术研究出发,对这一石刻铭文的撰写及镌刻背景、拓本真赝、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读者非常关心的问题,紧扣热点,做出了学术界“应有的说明和认识”。
★深入浅出,高深的学术问题浅近地表达。
高深的学术问题在这里低而又低,低到了尘埃里。围绕《燕然山铭》,扩散开来,一个个具体问题逐步解析,一个个事实逐渐浮出水面:燕然山战事起于何因?《燕然山铭》是事先有准备的,还是临时起意?《燕然山铭》和《封燕然山铭》是一回事儿吗?
★以小见大,小处着笔精彩讲述大道理。
这一点,辛德勇教授日前在复旦讲学时候说过的一段话非常具有说服力:“在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这是我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问题时经常提醒自己要努力为之的一个基本做法。”“历史研究的魅力和价值,往往就在细节当中。西洋人的成语,说魔鬼在细节之中。我在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却时时都会感受到,上帝的灵光正是透过细微空隙而闪现。”在这里,编辑隆重推荐给有志的青年学者,你可以对《燕然山铭》不感兴趣,但是可以借鉴辛德勇教授的历史研究方法,或有裨益。
★知识丰富,广泛搜罗史籍,旁征博引。
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文献,无不告诉我们辛德勇教授涉猎的典籍之多,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学术研究之严谨,凡有所引必有出处。
★逻辑严密,抽丝剥茧,考证丝丝入扣。
这一点尤其值得推崇,书中对于《燕然山铭》铭文的核校,一字字一行行地校勘,通过合理假设、精细比对、逐步核校,逐渐为我们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燕然山铭》的原貌。
★幽默诙谐,语言非常生动、直观、形象。
历史本身是枯燥的,幽默诙谐的语言会带领读者进入那个历史场景,一切变得生动起来,甚至成为连续的影像浮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在“办砸了的交易”一节中:“和后来诸多蠢猪笨熊式的帝王相比,对于这样一位风流儒雅的天子来说,这话讲得未免有些刻薄,元朝人还有比这稍微宽厚一点儿的说法,乃谓其书画诸艺虽过于常人,但正是因为‘见其善于此,则知其不善于彼’(元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前甲集卷三三徐琰《跋徽宗御书》)。事实上,宋徽宗不仅不具备人主所需的高识远见,就连所谓私智小慧也未必灵光。”
东汉永元元年(89年),车骑将军窦宪联合南单于、东乌桓等势力一起攻打北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大获全胜,几乎全歼北匈奴的主力。这一战役在历史上非常著名,当时随军出征的班固撰写了这篇流传千古的《燕然山铭》。
二〇一七年七八月间,中蒙联合考察队实地踏勘,确定了蒙古国杭爱山一带的一处摩崖石刻系东汉史学家班固所作《燕然山铭》。这一发现,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认为,“学术界有责任和义务做出应有的说明和认识”,陆续撰写了“《燕然山铭》漫笔”系列文章,遂成《发现燕然山铭》一书。该书对《燕然山铭》拓本真赝、铭文布局、铭文核校、刻者其谁、燕然山战役,等等,都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考证。
第四篇
《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一、.想当然的说法
在我的“《燕然山铭》漫笔之三”《〈燕然山铭〉的真面目》这篇文稿中,依据目前有限的条件,尽最大努力,对这篇铭文,做了初步的复原。我谈到,通过这一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班固原稿写定本的形态。
或以为班氏既与操刀锓石者同在燕然山旁,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他直接动笔,写在石上,亦即“书丹”于崖壁,再由刻工依样雕凿。如此一来,今天我们看到的摩崖石刻,就成了班固的手迹,就成了最最可靠的亲笔“写本”。
史料价值的大小姑且不论,仅仅就古物的艺术品价值而言,这就像后世镌刻名人“法书”于碑版一样,若是通过这一刻石使我们得以目睹大史学家班固留下的字迹,当然引人瞩目。
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只是一种很浮泛的说辞。由于班固这篇《燕然山铭》就写在窦宪军中,当时当地,当然也就可以由他本人直接移写上石,这是显而易见的,谁都想得到,无须专家者流来做专门的表述。然而,我们若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这种直观的生理感觉并不具有太大意义,也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而且还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在学术研究领域,想当然的说法,不管是对是错,其实都不具备学术的价值。学术研究,需要的是切实的论证,而不是空泛的议论。
稍有一点儿文化的人都知道,唐代以后,在刊刻碑石时,会比较普遍地延请书法名家上手。若是按照这一情况来逆推的话,当年窦宪指使人刻制《燕然山铭》时,班固似乎应该是书字上石的合适人选。
按照唐人张怀瓘在《书断》一书中的说法,班固除了以辞章著述知名于世外,在书法方面,确实也还颇有造诣。不过班固所擅长的,并不是《燕然山铭》刻石上镌刻的普通汉隶,而是以大篆、小篆而被张氏列入神品、妙品、能品三等级书法名家中最下一等的“能品”,并具体描述说,班固“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终“以大、小篆入能”。(唐张怀瓘《书断》卷下)
当然,这种篆书艺术水平,是作为名世长技而载入书法史册的。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绝不可能提起笔来就写大篆、小篆而不会写一个当时通行的隶体字。
在《汉书·艺文志》里,班固对古今字书颇有一番论述,有意思的是,竟然把自己也写到了里面(《汉书》不像《史记》那样是贯穿古今的“通史”,它是一部“断代史”,只写西汉一朝,不写班固身处的东汉):
《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救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
文中写到的“臣”,就是班固本人的自称。盖班固最终纂就《汉书》,乃明帝永平时受诏所为,章帝建初年间进呈御览(《后汉书》卷四○上《班固传》),故自谓曰“臣”。
从《汉书·艺文志》的上下文义来看,秦丞相李斯的《仓颉》等字书,应是篆体,而至汉代,应是采用了秦时开始兴起的隶书,不过《汉书》没有直接的表述而已。后来唐人张怀瓘曾指明对汉代的这类字学书籍“皆用隶字书之”(唐张怀瓘《书断》卷上),今所见出土汉简中的《仓颉》,皆属隶书写本,可以实际证明这一点。
尽管像《仓颉》这些字书重在字形结构,而不是书法艺术,但当然也需要尽可能写出精当美观的标准字体。在另一方面,班固既精于篆书而又对隶书的字形结构有系统的研究,自然不会写不好当时广泛通行的这种隶书。简单地说,班固充分具备了写字上石的书法技艺。
前 言
第一篇
班固《燕然山铭》刻石的发现与旧传拓本、另行仿刻及赝品
第二篇
赵家那一朝人看到的《燕然山铭》
第三篇
《燕然山铭》的真面目
第四篇
《燕然山铭》刻石的文字出自谁人之手
第五篇
登高何处是燕然
第六篇
苍茫沙腥古战场
第七篇
一字之衍生出三年之疑
第八篇
张公那顶破帽掇不到李公头上
第九篇
《燕然山铭》不是封燕然山之铭
第十篇
《燕然山铭》与汉代经学以及史学家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