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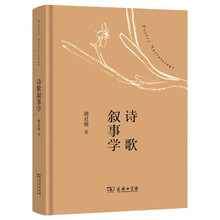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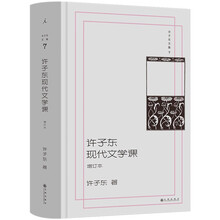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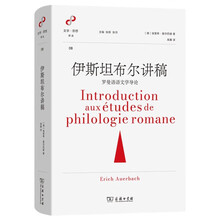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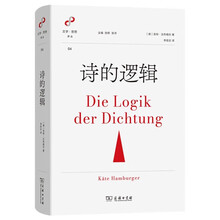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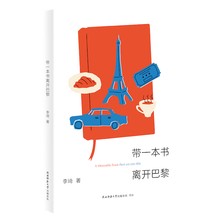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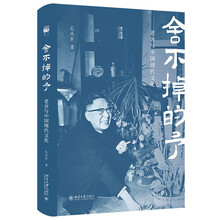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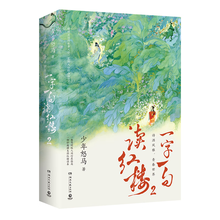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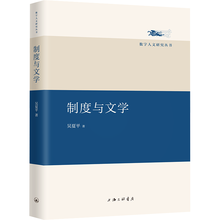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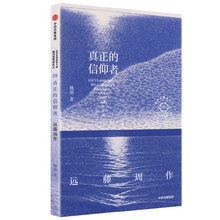
1. 著名小说大师的盛誉经典文学课: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身是二十世纪备受推崇的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大家,文学声誉卓著且越来越受到无可置疑的认可,他将欧洲贵族趣味与传统修养带进美国文化,又持有深刻而世故的批判与讽刺眼光,这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品味。擅长反讽、怀旧与滑稽模仿技法;同时又注重语言的锤炼,他以广博学识和文学修养形成令英美本土作家赞叹的英文风格。移居美国后,他在康奈尔大学等几所高等学府讲授欧洲文学,《文学讲稿》正是在这些讲稿的基础上,编辑修订成书。由于风格独特,且闪烁着文学解读和批评的精彩光芒,随着时间的积淀,其作为文学评论经典名作的品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尊崇。
2. 对七位文学大家的七部文学名著的永恒的探讨:
简奥斯丁 《曼斯菲尔德庄园》
查尔斯狄更斯《荒凉山庄》
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 《化身博士》
马塞尔普鲁斯特 《去斯万家那边》
弗朗茨卡夫卡《变形记》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
每一部都熠熠生辉,都被谈论过无数次,但这次是作家解读作家,天才剖析天才,经典成就经典。
3、兼具可读性与极高的文学批评典范价值,塑造优秀读者。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一九四O年代纳博科夫移居美国后,在韦尔斯利学院和康奈尔大学教授欧洲文学,《文学讲稿》即是他为此精心准备的课堂讲稿和笔记的编录集,收入其对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狄更斯《荒凉山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斯蒂文森《化身博士》、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卡夫卡《变形记》、乔伊斯《尤利西斯》等七部作品的细读分析。彼时正逢新批评理论在西方文评界盛行,纳博科夫以注重文本分析(有时具体到了几乎逐字逐句讲述的地步)、独特的艺术观和批评方法,丰厚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昆虫学研究训练出的逻辑性和严谨风格,使《文学讲稿》成为运用新批评理论对作家和文学作品具体研究的典范之作。
纳博科夫在这本书里讨论了《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等七部文学名作,相当于带领学生做了七次艺术侦查和解剖,皆以简洁明晰的语言、深入浅出的方式,极为鲜明地表达他对作品的看法,同时从文本而非观念出发,细致地捕捉和艺术特点,点明作品在艺术上成功的原因。
《文学讲稿》还有一个特点,即较多地引用了作品的原文。这一方面保留了此书原为课堂讲稿的本色,另一方面也具体说明了作者的见解是如何形成的。由此也形成了本书的魅力,即经过纳博科夫的讲解,他把作品中那些原来并未显示出深长意味和特殊价值的文字,如珍珠出蚌般的展示给读者。
我的计划是找几部欧洲名家作品来进行研究。做的时候想本着一种爱慕的心情,细细把玩,反复品味。因此,“怎样做一个好读者”或“善待作家”这类标题或可作为这些针对不同作家的不同讨论的副题。早在一百年前,福楼拜就在给他情妇的一封信里说过这样的话:谁要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成为大学问家了。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应当注意和欣赏细节。如果书里明朗的细节都一一品味理解了之后再做出某种朦胧暗淡的概括倒也无可非议。但是,谁要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思想来看书,那么第一步就走错了,而且只能越走越偏,再也无法看懂这部书了。拿《包法利夫人》来说吧。如果翻开小说只想到这是一部“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那就太扫兴,也太对不起作者了。我们应当时刻记住,没有一件艺术品不是独创一个新天地的,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这个新天地,研究得越周密越好。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件同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没有任何明显联系的崭新的东西来对待。我们只有仔细了解了这个新天地之后,才能来研究它跟其他世界以及其他知识领域之间的联系。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指望通过一部小说来了解世界,了解时代?当然谁也不至于天真到以为只要看看由那些新书俱乐部四处兜售的装帧漂亮的标以历史小说的畅销书,就能对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文学名著又当怎样看呢?比如简• 奥斯丁,她只了解牧师家庭的生活,而她书中描写的却是英格兰地主阶层的缙绅生活和田园风光,我们可以相信她所描绘的这幅图画吗?再如《荒凉山庄》,这本书写的是荒唐的伦敦城里的荒唐传奇,难道我们可以称其为百年前的伦敦大观吗?当然不行。这里所讨论的其他同类小说也当如是看。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并且这里选的小说更是最上乘的神话了。
就天才作家(就我们能猜测到的而言,而我相信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而言,时间、空间、四季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思想,凡此种种,都已不是授引自常识的古已有之的老概念了,而是艺术大师懂得以其独特方式表达的一连串独特的令人惊奇的物事。至于平庸的作家,可做的只是粉饰平凡的事物: 这些人不去操心创造新天地,而只想从旧家当,从做小说的老程式里找出几件得用的家伙来炮制作品,如此而已。不过,他们的天地虽小,倒也能导出一些有点趣味的花样来,招得平庸的读者一时的喜爱,因为这些读者喜欢看到自家的心思在小说里于一种令人愉快的伪装下得到反映,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发射星球上天,会仿制一个睡觉的人,并急不可待地用手去搔他的肋骨逗他笑。这样的作家手中是没有现成的观念可用的,他们必须自己创造。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不然这门艺术就成了无所作为的行当。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只要现实还存在),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不仅仅是外表,就连每一粒原子都经过了重新组合。作家是第一个为这个奇妙的天地绘制地图的人,其间的一草一木都得由他定名。那里结的浆果是可以吃的;那只从我身边窜过,身上带斑点的动物也许能被驯服,树木环绕的湖可以叫做“蛋白石湖”,或者更艺术味一点,叫“洗盘水湖”。那云雾是一座山峰,而且是注定要被征服的山峰。在那无路可循的山坡上攀援的是艺术大师,只是他登上山顶,当风而立。你猜他在那里遇见了谁?是气喘吁吁却又兴
高采烈的读者。两人自然而然拥抱起来了。如果这本书永垂不朽,他们就永不分离。
在一次巡回讲学途中,某天晚上我到了一所偏远的地方学院。讲课的时候,我提出了一道小测验题,列举“优秀读者十大条件”,让学生从中选四项足以使人成为优秀读者的条件。原题不在手边,现在记得大体是这样的。请从下面的答案中选出四条作为一个优秀读者所应具备的条件:
1 须参加一个图书俱乐部。
2 须与作品中的主人公认同。
3 须着重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书。
4 须喜欢有情节有对话的小说,而不喜欢没有情节、对话少的。
5 须事先看过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
6 须自己也在开始写东西。
7 须有想象力。
8 须有记性。
9 手头应有一本词典。
10 须有一定的艺术感。
当时,学生对作品大多看重感情上的认同、情节、社会—经济角度、历史眼光。当然,你可能已经猜到了,一个优秀读者应该有想象力,有记性,有字典,还要有一些艺术感—这个艺术感很重要,我自己也在不断培养,而一有机会就向别人宣传。
顺便说一句,我这里所指的“读者”是一种泛泛的说法。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听我说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读一本书的时候,两只眼左右移动,一行接一行,一页接一页,又复杂又费劲,还要跟着小说情节转,出入于不同的时间空间—这一切使我们同艺术欣赏不无隔阂。但是,我们在看一幅画的时候,并不需要按照特别方式来移动眼光,即使这幅画像一本书一样有深度、有发展也不必这样。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一幅画的时候,时间的因素并不介入。可看书就必须要有时间去熟悉书里的内容,没有一种生理器官(像看画时用眼睛)可以让我们先把全书一览无余,然后来细细品味其间的细节。但是,等我们看书看到两遍、三遍、四遍时情况就跟看画差不多了。不过,总也不要把视觉这一自然进化而来的怪异的杰作跟思想这个更为怪异的东西混为一谈。一本书,无论什么书,虚构作品也罢,科学作品也罢(这两类书的界限也并不如人们一般想的那么清楚),无一不是先打动读者的心。所以,心灵,脑筋,敏感的脊椎骨,这些才是看书时候真正用得着的东西。
好,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闷闷不乐的人看一本轻松愉快的书,他的心理活动会怎么样?首先,他的闷气消了,然后好歹便踏进了这本书的精神世界。但是,要开始看一本书,尤其在年轻人倘若又听到他们私下认为太保守、太正统的人称赞过这本书,往往下不了这个决心。不过,决心既下,随后的收获也是丰富多彩的。文学巨匠当初运用想象写出了一本书,后来读这本书的人也要善于运用想象去体会他的书才是。
但是,读者的想象各不相同,至少有两种。读书的时候哪一种合适?一种属于比较低的层次: 只从书里寻找个人情感上的寄托(在这类寄情读书法名下还可以分列许多细目),这种读者常常为书里某一个情节所深深打动是因为它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也有人特别钟爱某一本书,只因为其中提到某国某地、某处风景、某种生活方式,使他顿兴恋旧之情。还有一些读者就更糟了,只顾把自己比作书里某一个人物。这些不同种类的等而下之的想象,当然绝不是我所期望于读者的。
那么,一个人读书,究竟应该怎样读才合适呢?要有不掺杂个人感情的想象力和艺术审美趣味。我以为,需要在读者作者双方心灵之间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平衡关系。我们要学得超脱一些,并以此为乐才好,同时又要善于享受—尽情享受,无妨声泪俱下,感情激越地享受伟大作品的真谛所在。当然这种事情要做到非常客观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有价值的东西无不带有若干主观成分。譬如,分明你们坐在这里,却可能只是我的幻觉;而我也许只是你的一个噩梦。但是,这儿我要说的是: 读者应该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在哪一处得收拾起他的想象,这需要他弄清楚作者笔下是一种什么样的天地。我们必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必须设想小说人物的起居、衣着、举止。《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范妮• 普赖斯的眼珠是什么颜色,她那间阴冷的小屋子是怎么布置的,都不是小事。
气质人人不同,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 读书人的最佳气质在于既富艺术味,又重科学性。单凭艺术家的一片赤诚,往往会对一部作品偏于主观,唯有用冷静的科学态度来冲淡一下直感的热情。不过如果一个读者既无艺术家的热情,又无科学家的韧性,那么他是很难欣赏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的。
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①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那个可怜的小家伙因为扯谎次数太多,最后真的被狼吃掉了纯属偶然,而重要的是下面这一点: 在丛生的野草中的狼和夸张的故事中的狼之间有一个五光十色的过滤片,一副棱镜,这就是文学的艺术手段。
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无穷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
回头再来看看那个孩子叫狼的故事。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 艺术的魔力在于孩子有意捏造出来的那只狼身上,也就是他对狼的幻觉;于是他的恶作剧就构成了一篇成功的故事。他终于被狼吃了,从此,坐在篝火旁边讲这个故事,就带上了一层警世危言的色彩。但那个孩子是小魔法师,是发明家。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 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
我们期望于讲故事的人的是娱乐性,是那种最简单不过的精神上的兴奋,是感情上介入的兴致以及不受时空限制的神游。另一种稍有不同倒也未必一定高明的读者是: 把作家看作教育家,进而逐步升格为宣传家、道学家、预言家。我们从教育家那里不一定只能得到道德教育,也可以求到直接知识、简单的事实。说来可笑,我就知道有些人看法国小说或俄罗斯小说,目的只在于从中了解巴黎有多快活,俄国有多悲惨。最后,而且顶重要的还是这句话: 大作家总归是大魔法师。从这点出发,我们才能努力领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诗文、小说的风格、意象、体裁,也就能深入接触到作品最有兴味的部分了。
艺术的魅力可以存在于故事的骨骼里,思想的精髓里。因此一个大作家的三相—魔法、故事、教育意义往往会合而为一进而大放异彩。有些名著,虽然也只是内容平实清晰,结构谨严,但给我们在艺术上冲击之大,不亚于《曼斯菲尔德庄园》,或是狄更斯式的富于感官意象的跌宕文字。在我看来,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衡量一部小说的质量如何,最终要看它能不能兼备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聪明的读者在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充分领略其中的艺术魅力,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是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领悟作品的真谛,并切实体验到这种领悟给你带来的兴奋与激动。虽然读书的时候总还要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超脱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带着一种既是感官的,又是理智的快感,欣然瞧着艺术家怎样用纸板搭城堡,这座城堡又怎样变成一座钢骨加玻璃的漂亮建筑。
……
原编者前言 弗莱德森· 鲍尔斯 I
导 言 约翰· 厄普代克 XIII
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 3
简· 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 11
查尔斯· 狄更斯《荒凉山庄》 71
居斯塔夫·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143
罗伯特· 路易斯· 斯蒂文森《化身博士》 199
马塞尔· 普鲁斯特《去斯万家那边》 231
弗朗茨· 卡夫卡《变形记》 281
詹姆斯· 乔伊斯《尤利西斯》 319
文学艺术与常识 420
跋 431
附 录:考试题 433
译后记 申慧辉 437
想象的伟力再难找到如此活力充沛的代言人。——约翰•厄普代克
货真价实的魔术师。——保罗•贝利
多么荣幸,他选择使用我们的语言并使之焕然一新。——安东尼•伯吉斯
纳博科夫的感受力之强大、丰盈和多姿多彩,在现代小说家中无可匹敌,鹤立鸡群……
如果文字能唤起至纯的感官愉悦,那么舍此无它。
——马丁•艾米斯
他对小说创作的各色招式驾轻就熟,还发明了属于自己的新技法。——彼得•阿克罗伊德
我们时代具原创性和创造力的作家。——《金融时报》
纳博科夫的天赋不仅在于他能将一切主题都转化成清晰的视觉意象,
他还有近乎放肆的幽默感,任何悲剧在他笔下都能荒诞毕现。——《观察者》
鲜活的记忆萦绕其中,面对命运的恶意嘲讽,或游戏其间,或与之抗争…纳博科夫幽暗跌宕的故事之中闪烁着救赎的微光。
——《新闻日报》
他所使用的语言是一件神奇的工具,微妙至极,却又充满力量:
我们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作者,包括乔伊斯,能像他这样,捕捉世界瞬息万变的光影。
——《波士顿环球报》
天才之作……
遣词造句,精雕细琢,奔泻无隘,直抵始终如一的独造意象,
于无形中将思维的逻辑演绎到了极限。
——《沃斯堡星报》
任何一个认为人、人的思想及缺陷极为重要的个体,
自能发现其中的意趣。
——《里士满时讯报》
在塑造个人经历并赋予其意义上,心灵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纳博科夫对其刻画之生动、探索之灵活有力,无人能出其右,
由此推及,对于理解和包容个人的经历,亦无人能与他比肩。
——《华盛顿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