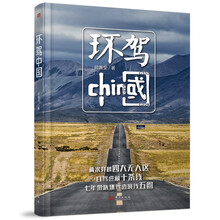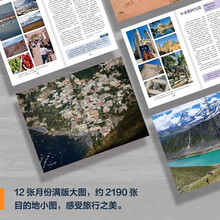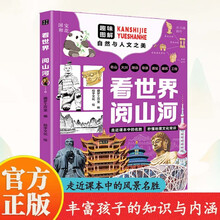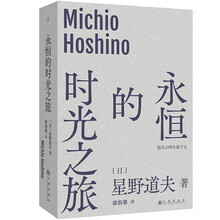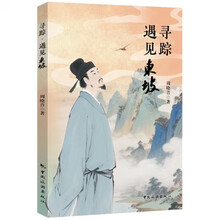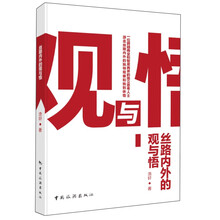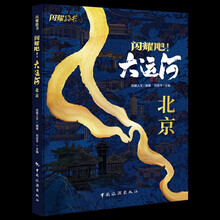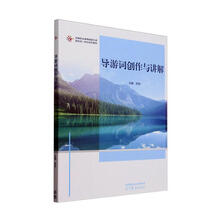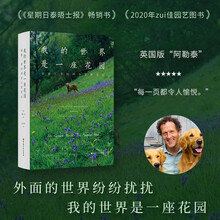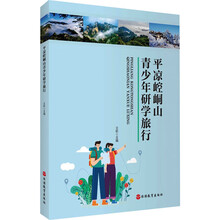02 航程<br> 船儿,船儿,你漂向海洋,<br> 我把你遥望,<br> 向你探问,<br> 你守卫什么?<br> 筹划什么?<br> 心向何方?<br> 一船出国贸易经商,<br> 一船留下守卫边疆,<br> 一船自远方归来,财富满舱。<br> 喂,可爱的船儿,你将漂向何方?<br> 凡去欧洲观光的美国人,须远涉重洋,但这不失为一个绝妙的准备过程。他将尘世与俗务一时摆脱,心境宁然——此情尤宜于观赏新鲜生动的景象。你看这大海,浩瀚无边,宛如一页现存的白纸,铺于地球当中。举目遥望,尽皆一色;犹如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浑然一体,其变化极难觉察。故土一旦从眼前消失,一切便成空白,直至你踏上大海彼岸;此时,你又立即被抛向另一个喧嚣而新奇的世界。<br> 陆地旅行,景物连绵不断,所见人事接踵而至,人生的故事得以继续,因此,我们不会有太多离愁别绪。不错,我们在远游中每前进一步,都拉着“一根长长的链条”;这链条节节不离,我们可沿此返回,感到其末端仍把我们与家紧连。但在大海上航行,我们便瞬间脱离一切,仿佛先前还在平稳牢固的锚地,现在忽被解缆,漂向一个疑惑丛生的世界。一片汪洋,把我们与家断然分开——这并非想象,而是千真万确。大海常遭风暴袭击,变幻不定,令人担忧,使你宛如远在天边,难以重返家园。<br> 至少我的情形如此。祖国的蓝天,像浮云消失在地平线下;目睹此景,我仿佛觉得关于美国的大书我已就此合上,终于有闲暇作一番悠然的遐想,之后再打开另一本书。那片故土,也正从我视野里消逝;我一生最可爱的东西,无不珍藏其中。当我重返故园,她将发生怎样的变迁?我自己的变化又将如何?——一旦起程远航,怎知这翻腾不息的大海要将你漂向何方?至于何时重返故乡,是否有幸再回到童年生活的地方,你均不可得知。<br> 如上所述,海上一切皆为空白——此言应予纠正。一个人若喜爱幻想,勤于思索,便能于航行中发现,可供思索的事物比比皆是:不过它们是大海与天空的奇迹,使你把世间置之脑后。我喜欢于夏季风平浪静之日,漫步至船后栏杆,流连忘返,或爬上主桅楼,在大海平静的胸怀里,沉思默想数小时之久;举目凝望一团团金光灿烂的云块从地平线上徐徐显露,将其幻想成美妙仙境,同时把我臆造之物置于其中;注视缓缓起伏的波涛卷起银色浪花,似欲奔向幸福的海岸。<br> 我从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看海里种种怪物笨拙地嬉戏;我虽并无危险,但仍感畏惧,此种感觉实在有趣。只见群群海豚在船头两边翻滚,虎鲸将巨大身躯漫漫浮出海面,或者,贪婪的鲨鱼像个鬼怪在蓝海上猛冲而过。这时我凭着想象,把曾经听到和读过的一切,幻化人海里——如漫游于深不可测的波谷中的鳍状兽群、潜伏于地球最深处的怪异之物以及渔夫水手颇爱讲述的狂暴幽灵。<br> 有时,远处忽现一叶孤帆,沿海边微微滑行,引起我另一番遐想。那片小小的世界,也急于奔赴坚实庞大的土地,多么有趣啊!人类发明了船只,便立下一座荣耀的丰碑:风浪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征服,天涯海角彼此相连,上帝的恩赐得以互惠——南方一切华贵之物,无不涌入北方贫困地区;知识的光芒普照大地;四处可见文明社会的善行义举;天各一方的人们得以团聚。而昔日,自然似乎让一个巨大障碍横隔其问,无法超越。<br> 某日,我们发现一个奇形物体在远处漂浮。海上这片浩瀚的世界,单调沉闷,因此某物一旦出现都会引人注目。原来是一只桅杆,船身必定已彻底毁损,残余的围巾仍依稀可见,一些船员曾用之将自己系于桅上,以免被海浪冲走。船为何名,无迹可查。这失事的船只显然已在海上漂浮数月:一簇簇水生贝壳类动物紧附四周,两侧漂浮着长长的海藻。<br> 我想,船员们此刻身在何处呢!他们早已不再挣扎,在咆哮的风暴中葬身海底,尸骨在大海深处发白。寂寞与遗忘,像波涛一样将他们淹没。他们何以遭此厄运,不得而知。怎样的哀叹曾飘随船后,他们凄凉的家中,曾有过怎样的祈祷!情人、妻子和母亲,每天又是怎样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消息,以期忽然听到漂泊大海的船只一点音信。然而,期待怎样变得黯然,成为焦虑,成为恐惧,成为绝望。哎呀!船上可资珍爱的纪念物均无从获得,人们只知船出了港,“从此杳无音信!”<br> 眼前这只破船,一如往常,令人想起许多可悲的往事。尤其在傍晚,晴朗之日突然天昏地暗,十分可怕,一场疾风暴雨将至;先前还一帆风顺,此刻便不得安宁。我们围着一盏孤灯坐下,其光昏然,室内因此更阴森可怖。大家依次讲述关于船只遇难的故事。船长讲的虽然不长,但使我尤为感动。<br> “一次,我乘坐一艘牢固的船,”他说,“沿纽芬兰海岸航行,遇上当地常见的漫天大雾,白天也看不多远。一到夜晚,天气十分阴暗,两船之遥的东西都辨认不清。我点亮桅杆顶部的几盏灯,随时观察,以免碰到前面的小渔船,这些船习惯停在沿岸。风呼呼地猛刮,船飞快行驶。突然,值班海员发出‘前面有船!’的惊呼——话一出口两船就撞上了。那是一只停泊的纵帆船,船身正好横对我们。上面的船员都在睡觉,连一盏灯也忘记升起。我们沉重的大船正撞中它胸怀,猛烈将它撞沉,并从其上面穿越而过,向前驶去。当它在我们身下渐渐沉没时,我瞥见两三个不幸的人半裸着身子,从船舱奔跑出来——他们刚从床上惊起,就在尖叫声中被海浪吞没。我听见风中传来他们被淹没时的哭叫。狂风把这声音卷到我们耳边,随之刮走,再也听不到了。那些哭叫声让我永生难忘!过了一些时间,我们才得以调回船头,因船速太快。我们尽力返回原地,猜想那只小渔船可能停泊的地方,并在浓雾里四处巡游了几小时。我们又鸣放信号枪,看是否能听到幸存者的呼叫;然而四周一片寂静——他们从我们眼里、耳里彻底消失了!”<br> 我承认,类似故事,使我美好的幻想一时化为乌有。夜愈深,风暴愈猛,使大海波涛汹涌,翻腾不息,发出沉闷可怕的声音。海水一浪高过一浪。有时,头上的阴云似乎被闪电撕裂,只见闪电在滔天的白浪上空震颤,随之而来的黑暗因此更为恐怖。这片汹涌的汪洋之上,雷声轰鸣,在巨浪中回响,连绵不断。我看见船在咆哮的海面摇晃,颠簸,竟保持了平衡,或者说仍未被巨浪卷沉,堪称一奇。帆桁时时沉入水中,船头几乎被波涛淹没。有时一个巨浪迎面冲来,仿佛要将它倾覆,唯有巧妙地把握好舵方能使其免遭重创。<br> 我回到船舱,可怕场面仍萦绕脑际。狂风从帆缆呼啸而过,发出丧葬似的哭声。桅杆吱嘎作响,船在汹涌的海浪中挣扎时,舱壁紧绷,发出呻吟,令人胆战。我听见海浪一次次猛击船身,在耳边咆哮,好像正围着这漂浮的监狱怒吼,寻捕食物——哪怕一个钉状的小孔,接合处的一点小缝,都会使之乘虚而入。<br> 但有一天,大海平静安宁,和风宜人,一切忧愁顿然消失。天气这样明朗,风儿如此和美,谁不为之欣喜呢。船鼓起风帆,欢快地在微波中乘胜前进,此时它多么傲然,多么英勇——似欲称霸大海!<br> 也许,一次航行,我即可将所思所想记录成书,因思绪几乎连绵不断——不过我该上岸啦。<br> 这天早晨,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桅头传来“陆地”的叫声,令人激动不已。美国人初见欧洲,总会心潮澎湃,妙不可言,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能心有所悟。只“欧洲”一名,便会使他浮想联翩。这是一个“希望之乡”,他童年时之所闻,学生时之所思,无不珍藏其中。<br> 从那时起,直至我亲临欧洲,皆满怀激动。战舰像守护的巨人,悄然潜伏海岸;爱尔兰岬伸入海峡;威尔士大山高耸人云,这些,令我兴味盎然。船驶向默茨河时,我用望远镜观察沿岸。整洁的村舍,置身于美丽的灌木与绿草之中,我凝目遥望,欣喜不已。一座大寺,日见腐朽,成为废墟,常春藤蔓延其上。附近山顶有乡村教堂一座,其尖塔直刺天空。种种景观,无不为英国所特有。<br> 此刻风平浪静,船很快靠住码头。只见人群熙来攘往,有的悠闲自在地旁观,有的热切期待亲友。有个商人似乎颇为精明,眉头紧皱,神情不安,我由此得知他专为接船而来。他两手插入衣兜,若有所思地吹着口哨,来回踱步;见他与众不同,人们专为他让出小道。船上、岸边的朋友不时看见对方,发出欢呼和问候。一个衣着简朴、举止异样的年轻妇女,尤其引起我注意。她从人群中挤出,船靠岸时急切地寻找,看久盼的人儿在何处,显得失望焦虑。忽然,我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呼唤她。原来是个不幸的水手,此次航行病魔缠身,人人同情。每遇晴朗天气,同伴就在甲板阴凉处为他铺一床垫。但近日他病情加重,整天躺在吊床上,咕哝着,希望死前见妻一面。船沿内河行驶时,他已被扶至甲板,此刻正靠支索,面容消瘦,极其苍白,难怪妻子充满爱意的双眼都没能把他认出。可一听见其声,她就立即转过身去,顿时眼里悲哀有加。她攥紧双手,发出一声轻微的尖叫,默默站着,痛苦万分。<br> 此时周围的人多么匆忙嘈杂。熟人相见,朋友问好,商人交易。唯我一人独处一旁,无所事事。无友人见我,没任何人同我欢呼致意。我踏上了祖先的土地——却感到置身此处,我倒成了一个陌生的人。<br> 03 罗斯科<br> 服务于人,<br> 作下界的守护神,<br> 勇敢地追求崇高真理——<br> 我们因此高于爬行兽群,<br> 得以永放光彩——此即人生。<br> 外国人一到英国利物浦,就迫切想先游览某些地方,“雅典娜神殿”即其中之一。它造型大方,颇为别致;藏书室堪称一流,阅览室宽敞舒适,难怪文人学士多云集于此。每到这里,总能见着许多人物,他们严肃庄重,专心看书读报。<br> 一次,我正观光这文人圣殿,忽见一人步人阅览室。他年事已高,身材魁梧,或许一度傲然挺立,但漫漫岁月——或忧思焦虑——已使其微驼。高贵的罗马人之风度,在他身上不难一见;头部特别,或许讨画师喜欢;因思虑不止,额上留下道道皱纹;然而两眼炯炯,焕发诗心光彩。置身熙来攘往的人群,他真似鹤立鸡群。<br> 我询问其名,方知正是罗斯科其人。我不禁略为退后,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他即大名鼎鼎的“作家”啊,其声名远扬天涯;即使在美国的穷乡僻壤,我亦曾和他有过神交。在美国,我们惯于仅凭作品了解欧洲作家,因此,将其想象成普通凡人,奔波于烦琐或卑微的事,与芸芸众生共行于尘土飞舞的世间,实难做到。在我们心中,他们已属高级生物,焕发天才的奇光异彩,时刻置身于光辉灿烂的文学殿堂。<br> 他系研究美第奇的杰出史家,所以刚见其身处熙熙攘攘的国民行列,我富有诗意的想象为之震动;但正因为处于如此环境,罗斯科先生才享有令人钦佩的崇高权利。有的人仿佛仅凭自身努力出类拔萃,以不可抗拒之精神,只身穿越重重障碍,面对种种逆境拔地而起;我每见此情景,颇觉有趣。艺术需勤奋,而自然似乎乐于使其受阻,以便使她从幼稚走向成熟。她会偶然获得一件富有朝气的精品,为此洋洋得意。她把天才之种撒向风中,虽有的死于石头狭缝,有的丧生于荆棘丛里,但有的却能扎下根来,勇敢拼搏向上,终受阳光沐浴,使原本贫瘠的土地长出美丽的奇花异草。<br> 罗斯科先生即属此辈。其故乡显然非文人才子的沃土;他身居商业闹市,家道贫乏,无亲无助;但他不懈自勉,自食其力,且几乎全凭自学,战胜道道难关,终于卓有成就,为民族增光添彩,竭尽所能促进家乡发展,使其日臻完美。<br> 的确,正是其上述特性,使我对他兴味十足,特意向同胞谈及。尽管他成就斐然,但英国属颇有智慧的民族,杰出作家比比皆是,而他仅为其中一员。然而,那些人只求虚荣,或自寻其乐,其历史对世人毫无告诫可言,要么则显示出脆弱矛盾的可耻品性。至多,他们易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溜走,纵情于文人享乐自私的生活,沉迷于孤傲势利的精神里面。<br> 相反,对赐予天才的种种特权,罗斯科先生从不索取。他并不囿于思想的花园或想象的天堂,而是投身于生活的阳光大道;他在路边搭建凉亭,让出外旅行、背井离乡者身心爽快;他挖掘纯洁泉源,让辛劳的人洗去一天尘土与酷热,吸取新鲜活泼的知识溪水。“其人生日常美丽”,人们可对之加以思考,自我完善。其美并非无与伦比,太超凡出众,似乎高傲无益,而是体现出积极纯朴、可仿可效的佳德——人人伸手可获;但不幸许多人不屑一顾,否则世界已成天堂。<br> 他的一生,尤值得美国公民注目。美国年轻活泼,其文学等诸多高雅艺术,必须与日常需要的粮草齐生并长。艺术的提高,非靠全体人民投入一切时间和财力,亦非靠高贵的保护人施予光彩,而靠聪明理智、热心公益的个人,从追求世俗利益中夺得短暂时光即可。<br> 由此,我们可知一位高尚的人,即使靠业余亦能大有作为,对周围的人事影响深远。一如其“美第奇”——他似乎把这统治者,作为纯粹的古物模型加以钻研——他将自身的历史与家乡的历史彼此交织,因此家乡的名望便成为其美德的丰碑。在利物浦,凡优雅开明之处无不有其足迹。他发现,财富之潮仅涌动于商业大道,于是从中盗取活跃的流水,用以滋养文学花园。他以身作则,不懈努力,将商业和文化有效地融为一体(在最近一文中,他也意味深长作过如此建议);并已实践证明,二者可多么美妙地互为协调,彼此促进。一个个高尚杰出的文学和科学协会,让利物浦名声大振,民众备受激励;但要知道,它们多由罗斯科先生发起且鼎力相助。利物浦迅速壮大,殷实富足,将与大都市在商业上一比高低;每虑及此,我们不难发觉他为英国文学事业确实立下汗马功劳,为唤醒市民意志,促进其思想进步颇有贡献。<br> 在美国,我们只知罗斯科先生是“作家”,而在利物浦人们称之为“银行家”,据悉他生意颇不景气。听说有的富人同情他,而我毫无此心。窃以为,他根本毋庸同情。凡只为俗世、仅于俗世活着者,每遇逆境即沮丧不堪;但像罗斯科其人,怎会向受挫的命运低头!挫折只会驱使他寻求自身丰富的精神资源,寻求内心的高尚友人。而这,优秀人物有时亦难做到,他们四处游荡,竟与卑者为伍。而他置身世俗之外,生活于古人与后人中间。他和古人一道,刻苦用功,共享幽居独处的美妙;和后人一道,胸怀大志,以求未来成果的斐然。此种人物,孤独寂寞时即处于至高享乐之中。高尚思想由此而生,它们是伟大心灵固有的养料,一如“吗哪”从天而降,被送至这荒凉世界。<br> 我一边深思默想,一边有幸对罗斯科先生的处境作更深了解。我与一位绅士驱车观光利物浦,他忽转向穿过一扇大门,进入一个优美的环境。片刻后,只见一座软性石的宽大住宅,呈希腊式风格,虽有所变异,但亦优雅宜人。旁有倾斜的草坪一块,美丽至极,簇簇树木长于其间,以作点缀,使这富饶和美之地更显风采。默西河宽阔平静,蜿蜒从青葱的大草地中穿越而过;地平线上,威尔士高山耸入云霄,相融于远方美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