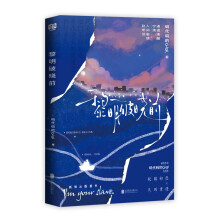《纯真及其所编造的(附赠精美书签)》是一部中篇故事集,由四个故事组成,包括《枯叶夏天》、《沦陷二〇〇X》、《窗上挂着霜的那些日子》和《小贾飞刀》。作品属于披在奇幻外衣下的青春文学,叙写了真实与虚构交织的纯真年代。
《枯叶夏天》写的是高三的故事,那是大家都为高考热火朝天的年代,我却因为身体里的精灵之血而总是感到莫名悲哀。毕业之后,我和阿木天各一方,谁也不记得我们曾经是同桌了。
《沦陷二〇〇X》主要讲述大学生活。我与小聂在校园偶遇,从此我在学业的挣扎和与小聂的逗贫中打发漫长又短暂的大学时光;我是精灵族,而小聂可能是个猎灵师。
《窗上挂着霜的那些日子》则关于童年,说话总是语气嚣张的璐是我的朋友,红领巾和解不完的数学题是我的生活。青春在某天突然离我而去,而我却突然想不起来自己和璐究竟认不认识。
《小贾飞刀》的故事发生在时空模糊的古代。飞刀是小贾的娘子,新婚之后就失踪了,小贾在寻找娘子的过程中走过了江湖;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寻找飞刀,并按原路返回家中,期望着这样一切可以回到过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