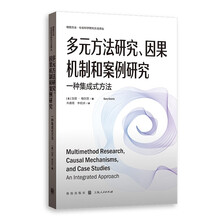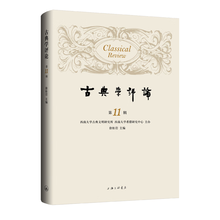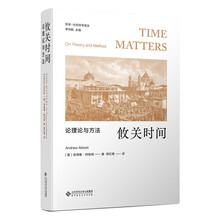在社会建设的全球经验中,在传统的现代化战略和发展主义式的社会发展框架中,作为平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社区建设一直被置于遮蔽、救赎和拯救的历史语境中。从作为重建历史道德之域的乌托邦想象到重建社会之域的现实主义关怀,从传统性的颠覆到现代性的明日花园式的精神鸦片,社区建设或被人唱衰,或被人颂扬;或作为反传统,非理性和专制主义的温床;或作为重建自由主义,减少过度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危害,鼓励责任心的一剂良药;或作为激进的平民主义者利用对抗性策略向政府施压,推动为民众赋权,促进民众觉醒,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或作为改造社会的想象或剧场。事实反复证明: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依托并着眼于以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来谋求社会的发展,并将社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已经日益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形成新的世界趋势。复兴社区意识、推动社区建设是矫正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痼疾和其他许多弊端的极其重要的手段。<br>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传统主义的昨日黄花和现实主义的狂飙突进,面对现代化战略和发展主义逻辑的迅猛发展,面对贫穷、怨恨、冷漠、社会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人们竟手足无措,陷入滑稽可笑的境地,不能创造新的知识范式来应对上述变迁。时间正在销蚀空间限制和社区边界,此时,如果顽固地沉浸在一种对传统的、狭隘的不合时宜的浪漫怀旧中,那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于是,人们对社区建设口诛笔伐,试图引入一些乌托邦的替代品,具有浪漫色彩的社区便流离失所,流落街头,成为海市蜃楼。现代社会到底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怎样的图景呢?现代社会又是如何把我们置于危险境地且不易被人所察觉呢?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温情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带来了过度个人主义,过度理性主义的危害;城市化进程又使陌生人定居在偶尔相遇的聚居地,都市生活的“视若陌生人的技艺”虽能让人们和谐相处,但这种温情的失落成为人们交往的障碍。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受现代主义理性牢笼的控制,现代主义盛行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盛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主义牢笼又会不断强化对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禁锢,大众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又变得疏离化,出现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和归属感减弱,带来的结果就是社区作为原初的同质性群体走向消解,而被异质性的、被动性的、疏离的大众社会所取代。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公民素质衰落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并不单纯是保守主义政治家的一种杜撰,它表现为乡村社区和城市街道中团结感的弱化,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婚姻和家庭的解体,频繁发生的城市暴力、恐怖主义袭击等。现代社会的痼疾使人们突然眷念早已置之脑后的社区,社区便得以被人所眷念和再次回忆。我们需要通过推动社区重建,加强社会教育,促进社会规范民主化,以正确的方向引导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以遏制工业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个性的缺失、道德滑坡和反社会力量的增长;通过社区重建,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以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br>基于此,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面对诸如“社区素质衰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社区建设才能发挥作用。“社区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方法。” 此外,社区建设中的广泛民主参与和互助合作, 还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公正”和“改善一个街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社区建设还可以培养、维护并发展公民精神与实现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培养社会成员彼此的信任与互惠创造社会资本。社区建设被视为恢复个人自由、重建社会道德方案的基础,这是当代社区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和共同信念。社区建设是解决现代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手段。<br>从全球经验来看,在欧美,由于城市的变迁,一些社区被遗忘,那里的人和环境也被边缘化了,成为一个“城中村”。为了重新唤起这些社区的活力,近30年来,欧美国家兴起了“社区重建”或者叫做“社区复兴”的运动。社区意义的转变某种程度上代表一种响应——响应这个工业化过程下的都市变迁,尤其是都市居民的认同变化与地方意识的形成。一个现象学式的探讨可以带我们进入人文地理学家亚当斯(JSAdams)等所说的地方纹理或者人类学家费尔德(Steven Feld)和巴索(KBasso)告诉我们的地方感。工业革命以来,从以社会学家、企业改革家为首倡导的“新协和村”、“田园城市”理论,到当代各个学科领域力量参与的“社区建筑”、“社区发展”、“都市社区规划”运动,从包括各种乌托邦空想式探讨、物质形态空间环境的建设到偏重于社会分析与内在运作机能等综合性的社区发展规划,这些都标志着西方国家的城市及社区空间研究的新时代的开始。<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