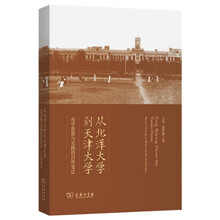<p> 想象一张清单,上面列着美国的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美国在世界上的别具一格。这份清单上可能包括原子弹、爵士乐、刑事辩护人的宪法权利、抽象表现主义、棒球、30年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和快餐……依列清单者的心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版本,但如果清单中没有收录美国的大学,那这清单显然是不完整的。<br /> 至少在印象中,我们都清楚这一点。美国人,尤其是渴望成为中产阶级的美国人,无时不在谈论大学——从蹒跚学步的小孩的第一次标准化考试开始,过程非常漫长,历经各种录取的捷报或噩耗,到最后,就像一百多年前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描述他第20次大学聚会所说:“黄皮、秃顶、牙齿掉光的人聚在一起,回忆红润的脸颊、乌黑的头发和远去的健康。”<br /> 对于当地的卖报人来说,一年中最开心的一周,恐怕就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出台年度大学排名那段时间。竞争性的出版物,如《花花公子》(Playboy)和《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等,也兜售着他们自己的排行榜:最佳派对大学、最佳“绿色”大学、少数族裔最受欢迎大学、性价比最佳大学……当然,还有他们自己版本的顶尖大学。如果你在 Google 里搜索“大学”(college)这个词——不久前,我试着这样干时,虽然会筛选出像“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或“枢机主教团”(college of cardinals)等和教育无关的关键词,但也会得到了52,800,000 个相关结果。<br /> 但是,对于一所好大学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搜索来的这些闲言碎语大部分都很少给出答案。实际上,在大学为其学生做了什么的问题上提供的信息很少。我们用来评估一所大学的标准还都是——其教师发表文章的数量、获得捐赠的规模、录取中的选择度、校友捐赠率,甚至是毕业率。不久前《纽约客》(The New Yorker)的一篇文章中,马尔科姆·加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指出,教师薪酬这一大学质量的标准衡量指标,可能实际上跟教师对教学的投入成反比关系——因为薪酬最高的教授很可能受聘于研究型大学,而在这样的学校里,本科生教育一般都是副业。<br /> 不过,我们互换地使用“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这两个词。我们说“她去了密歇根”,或者说“他上了欧柏林(Oberlin)”——都不大愿意说这些名字后面跟着的名词,似乎学院和大学是一回事。实际上,它们不是。诚然,它们彼此联系(大部分学院的教师现在拥有一份高等大学的学历),而且,学院可能以“系”或者“学院”(school)的形式存在于大学里。但是,学院(college)和大学(university)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学院(college)所做的是向本科生传播关于过去和来自过去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将来凭借它们谋生。大学(university)主要是教师和研究生开展的一系列研究活动,目的在于创造新知识,从而超越过去。<br /> 这两种体系都是有价值的,有时候它们会有重叠,比如一名学院的学生跟一名学者或科学家合作,做“尖端”或“开创性”研究——在现代大学出现以前,这是不可思议的。更多的时候,两种体系即使不彼此冲突的话,也是彼此竞争的,尤其是在这两者之一努力提升威望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加州大学的缔造者,以格外坦诚的语气承认道:“优秀的教师队伍会造成对本科生教学的不屑一顾。”差不多50年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就把这条“残忍的悖论”看作是“我们更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这个问题更是空前地紧迫。<br /> 确切地说,大学里哪些方面有危险?危险的多少何以重要?从根本上来说,大学应该是年轻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这段时期遨游人生寻求帮助的地方。它应该提供指导而不是强制灌输理念,应该帮助学生努力穿过成长这片危险地带,一路前进,实现自我认知。它应该帮助他们培养某些智识和心灵上的品质,使他们合格地成为具有反省精神的公民。下文中,我尝试把这些品质简化成一份清单。鉴于它们彼此密不可分,所以在优先性上没有特别的顺序:<br /> 1.通过认识过去对当下保持怀疑的能力<br /> 2.在看似互不相干的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能力<br /> 3.在科学与艺术知识的陶冶下欣赏自然世界的能力<br /> 4.愿意从自身之外的视角构想体验的能力<br /> 5.道德责任感<br /> 这些思考和感觉的能力,成就起来很难,要保持住更难。无论“分配如何合理”“发展如何全面”,单单学习人文、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获得它们;仅仅从事学术研究,也没法充分地培养它们。把它们想象成商品,由学生购买,交货给它们,纯属荒唐。最终,学生们要掌握的东西,不是在评分或考试中,而是在我们生活的方式中。<br /> 此外,鼓励和培养他们应该不偏离大学教育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会郑重讨论:在满足这项责任上,我们做得有多好。但是,我一直不情愿随声附和,呼喊说我们的大学状况糟糕透顶。全国各地,每时每刻——至少看起来大抵如此,我们都听说“管理人员膨胀,学费定价过高,教师薪水过高,设施破旧和教育经验欠佳”。对这种危机的呼喊由来已久。早在1776年,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写信给她的丈夫时就说,大学生“抱怨他们的教授……公共事务缠身,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教育“的状况从来没这么糟糕过”。100多年后,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宣称,“美国高等教育最紧迫的问题是对大学低年级生——一、二年级生——的关爱。”把类似的哀叹编成一张列表,从殖民地时期一直排到现在,不会是什么难事。<br /> 因此,任何想写一写我们的大学现状的人,都面临“喊‘狼来了’的男孩”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狼还没有来。美国的大学正在经历一段急剧变动期,经受着各种力量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经济不稳定、信息技术方兴未艾的革命、K-12教育愈发明显地不足、青春期的延长、教职终身制作为一项学术规范的崩溃,还有,或许最重要的是,教师和学生在应该了解哪些东西上的共识的瓦解。所有这些都让教育工作变得史无前例地艰难和富有争议。对于这些力量,现在我想通过一家高科技公司的CEO的话,仅就其中一种——被称为教师的“临时工化”的制度,啰唆一下。<br /> 他说,从前,在美国的电影院,有数千名钢琴师演奏现场音乐;然后有一天,电影配乐技术出现了,突然之间,除了“两名钢琴演奏者搬到洛杉矶”提供录制电影配乐外,其余的乐师都失业了。以此类推,课程“内容”(阅读、讲课、习题集、小测验等等之类)现在可以上传到互动网站上,还可以雇用讲师(基本上就是计件工)来在线评估学生的学业。在数字时代之前,在大学教室里做教师的人,将不得不“去做一些更富有成效的事”——就像那些过时的钢琴演奏者所不得不做的那样。<br /> 在开发“在线”学习的新技术上,麻省理工和卡耐基梅隆等以科学为导向的院校一马当先,这绝非偶然。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威廉·鲍温(William Bowen)所说,尽管这些技术已经在“很多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领域证明了其价值,但关键还是在于,它们是否能成功地适应新角色,成为推动真正的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英国教育学者埃里森·伍尔夫(Alison Wolf)这样写道:“对于精通专业的人文教师,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低成本、高科技的替代者。”——至少现在还没有。<br /> 这个幽灵,尽管它正游荡在高等教育的地平线上,但它还只是个影子,刚刚飘到本书要讲的故事的视线边缘里。这是因为,我关注的是所谓的精英大学,到目前为止,对于在更脆弱的院校中已经大发神威的教员溃败问题,它们有更强的抵抗能力。但是,每个地方,教员的角色都在改变,没有大学能够不受这种强大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它有转变大学的前景,也有削弱大学的危险。随着这些力量扑面而来,悲叹和欢呼都无济于事。在我看来,它们反而督促我们勇敢地面对某些基本问题:这个时代,对大学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对于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有越来越少的认同,那么,大学的目标和潜力在哪里?面对这些问题,本书试图陈述某些基本原则,它们由历史传承而来,目前面临着颠覆性的挑战,但在我看来,在未来,它们仍不可或缺。<br /> 在开始本书的故事前,我应该详说一下我对重点的选择。在谈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时,一名学者这样说道:“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设定的模式……成了全美国大学的模式。”这些院校跟其他不多的几所高校一道,确立了课程规范、录取程序、助学金原则,甚至还有大学生活的仪式和典礼。无论大众对它们的痴迷可能有多变态,它们赢得的关注有多么畸形(考虑到它们较少的在校生数量,是大大地不相称),事实依然是:通过这些院校,才能最好地洞察教育的悠久历史。此外,如果说它们对于理解过去有特别的突出之处,那么,在当前,对于未来应保持、改进或抛弃哪些教育原则的争论中,它们也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br /> 但是,如果说我对高校的关注视野较窄的话,在看待大学的纷繁多样性(如一名作家所说,“我们称之为大学的,有着五花八门的例子”)上,我还是竭力保持宽广的视野。美国的教育“系统”的一大优势就是,它从来没真正成为一个系统。在美国,大约有4000所大学:乡村的、都市的和郊区的;非盈利的、盈利的;世俗的、宗教的;有些小而独立,其他的则从属于大型研究院校;有些有高度选择性,其他的却几乎录取任何人,只要他们申请了并且有办法支付学费。在过去差不多20年里,我参观过100多所各式各样的大学,我希望,这会有助于减少错误,把他们想象成跟我最了解的大学差不多。<br /> 对大学的情况,即使只是做一番快速地扫视,也会明白:大学的意义在激烈地变化,院校之间的差异在飞速增大。对于较少数学生来说,大学依然是前耶鲁法学院院长安东尼·克龙曼(Anthony Kronman)回忆威廉姆斯的生活时,谈到的那种地方:他最喜欢的课,是在一位哲学教授的家里上的,教授的两只金毛猎犬睡在壁炉的两边,“就像炉床旁的书立”;与此同时,窗外,在夕阳的照耀下,伯克夏(Berkshire)山“泛着绯红和金黄”。对于大部分学生来说,大学意味着:在人员拥挤、资源不足的院校里,急于求成地学几门在市场上吃得开的技艺,却很少关注有时被称为“完人”的那不可捉摸的存在。对于还有一些人来说,大学意味着在晚上游荡到一座写字楼,或者跑到只存在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教室”里。想象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我们最富有的大学所提供的最好体验,这纯属白日梦。但如果只给钞票多、有才气或运气好的少数人提供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这是一个社会的噩梦。美国的社区大学、受埋没的私立大学和资金不足的公立大学中,很多出色的教师每天都在坚守着这条真理,竭力让民主教育的理想保持勃勃生机。<br /> 因此,阐述一所大学应该寻求为其学生做些什么,是我在本书中献丑的目的。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最近的小说《恐怖分子》(Terrorist),书中的主人公在新泽西的铁锈地带(Rust Belt)长大,父亲是一名常年不归家的埃及移民,母亲是一名爱尔兰裔美国人。当地的一位阿訇劝告这位男孩说,他应该从他爸爸的信仰中学习虔诚和纯洁,而不是让自己在美国的大学里遭受道德败坏的侵蚀。出于不同的原因,这个男孩的妈妈也看出,没有必要让她的儿子在高中读完后继续学业。在升学顾问不赞成她的观点并试图让她改变想法时,她问:“他会在大学里学什么?”这位顾问回答道:“任何人学习的东西——科学、艺术、历史。人类、文明的故事。我们怎样走到今天,现在是怎样的?”<br /> ……</p>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