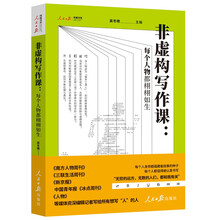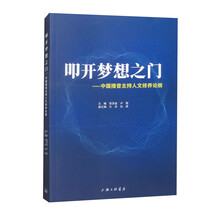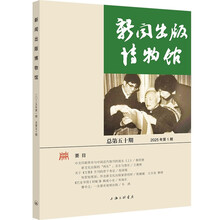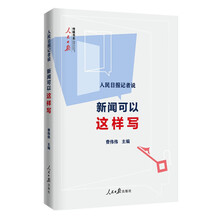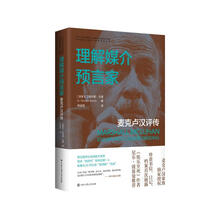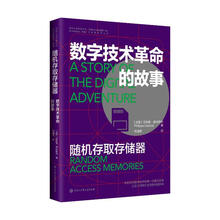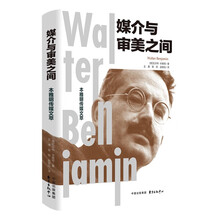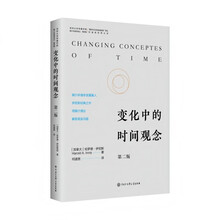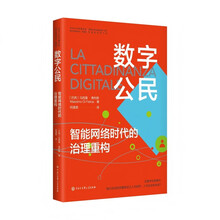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我国古代藏书的场所称藏书楼,近代以来新型的文献收藏机构称图书馆。这是通常的说法,也是图书馆史研究的专业术语。
细究起来,将我国古代的文献收藏称之为“藏书”似乎更为恰当。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注:“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这就是藏书一词的最早出处。老子所职掌的周王室藏书室,也是文献记载中最古老的正式的藏书机构,老子就相当于周朝国家图书馆的馆长。
然而,藏书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实际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得多。据传说,上古伏羲氏画八卦始有文献,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夏代也有负责图籍的太史。《河图》、《洛书》、《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都是远古文献的名称。上古传说固然渺不足征,但至迟在商代,即已有了可以确信的各类藏书:本世纪初发现的殷商甲骨文献,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尚书》中关于商代“有典有册”的藏书记载,也为考古发掘所证实。即使在周朝,周王室藏书的历史也远早于老子,文献也不仅限于周王室所藏。可以断言,我国古代的藏书,远在华夏文明初始的年代即已发端,并伴随了古代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之始终。
“藏书”一词,实际上便是我国古代文献收藏的总称,也是前人的一贯说法。例如“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1],“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等诸多记载,便是例证。
至于“藏书楼”一词,则是一种较为晚出的说法。藏书楼之称究竟出现于何时,目前似乎还很难确切考定,但不会早于唐宋之际,并且发源于私家藏书。
据《新唐书·李鄌传》记载:“……家有书至万卷,世号李氏书楼。”又据《郡斋读书志》载:“(唐朝孙长孺)喜藏书,贮以楼,蜀人号书楼孙氏。”这两处唐代的私人藏书,大概就是最早被称作藏书楼的文献收藏了。
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了鼎盛时代,藏书楼之称便开始风行一时。私人藏书家们往往要将自己的藏书之所标之以“XX楼”、“XX阁”的雅称,就是一些没有多少文献收藏的士大夫们,也常常为其书斋取个藏书楼的名号以附庸风雅。这种风气甚至也影响到了官方的藏书,许多皇家和官府的藏书机构也开始仿效民间的藏书楼,冠之以各式藏书楼的名号。这样一来,“藏书楼”就成了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就是近代问世的一些早期新型图书馆,往往也标之以藏书楼之名,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皖省藏书楼等。
与藏书楼源远流长的历史相反,“图书馆”在中国是个完完全全的外来名词和近代文化现象。图书馆一词,在西方语言中基本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Library,另一个是Bibliotheca。Library源自拉丁语的Liber,意为树皮。因为树皮曾用作书写的材料,所以在意大利语中把书店叫Libraria,而法语中则把书店称作Libraries。这个词后来由法语进入英语,就成了Library。而Bibliotheca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os,即书籍,由书写材料“纸莎草”(Papyrus)的希腊语读音而来。后来对于存书的场所,希腊语叫Bibliothek,拉丁语则称Bibliotheca,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中均用这一词称图书馆,只是在拼法上有些小差别。
对于Library或Bibliotheca,中国人最初译为“藏书楼”或“公共藏书楼”。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ソー)”,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但是这一新的提法似乎并没有马上为国人所接受,一些早期的近代图书馆仍以“藏书楼”称之者居多,也有的称“书藏”、“书籍馆”,“图书院”,“藏书院”等。据目前所知,在20世纪之前只有1897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使用了图书馆的名称。从20世纪初年起,使用图书馆一词的文献和机构才开始多了起来。例如,1900年9月的《清议报》上就有一篇名为《古图书馆》的文章;1901年6月的《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关于幼稚园盲哑学校图书馆规则》。
1903年,清政府颁发了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的高等教育纲领《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图书,以资考证”,并规定其主管人为“图书馆经理官”[3]。
这是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所正式采用。《奏定大学堂章程》颁布后,原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便改名为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藏书楼的主管人也由“提调”改称图书馆经理官。这是我国第一个采用图书馆名称的正式官方藏书机构。但由于有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之名在先,所以改名后人们仍习惯以旧名称之,使京师大学堂图书馆这一正式名称反而不为人们所注意。直到1904年,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和福建图书馆相继成立,图书馆的名称才开始在社会上通行,其后各地出现的各种新型藏书处所多数都标之以图书馆之名。1909年,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奉旨筹建,清政府又随之颁发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样才使得图书馆的名称在我国最后确立了下来。学界普遍认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和《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的颁布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产生的标志。[4]厘清藏书、藏书楼和图书馆的含义及其关联与区别,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史实:中国古代的藏书、藏书楼与近现代图书馆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的产物,亦即“西风东渐”的结果,不是“中华古已有之”的。
中国是世界上文献保存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连贯的文献大国,藏书楼则是这些文献的载体,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催生出新型的近现代图书馆。古代的藏书楼至多可以看作是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渊源,但不是它的母体和前身。
有人这样描述近代中国图书馆:19世纪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后来逐渐接受了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方法,因此才产生了重要的进步和飞跃。其实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中国古代的藏书楼和西方的图书馆之间,不是什么落后与先进的差别,而走的是南辕北辙的两条道路。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社会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藏书楼再发展若干世纪,也没有可能自行演变成为西方式的近代图书馆。中国的旧式藏书楼中缺乏进化成为近代图书馆的基本机制,因此不可能成为新式图书馆产生的母体。中西图书馆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别和先进与落后是两回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