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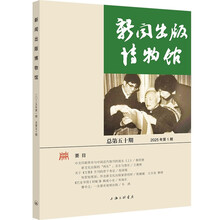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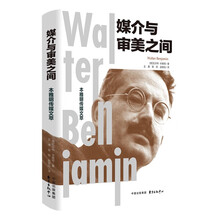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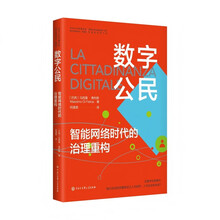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写的一部中国文献介绍类的汉学读物。在当时的背景下,把中国文献介绍给俄国,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按照专题,把中国文献分为儒家文献(其中又按时间把儒家分为两个时期),道家文献,佛教文献,历史与地理著作,律法文献,语言学、批评、古代。
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差别较大,这也是它与埃及文字的不同之处。埃及文字的书面语同口语是一致的。汉字的情况恰好相反,至今尚未写作或出版过任何一本与口语表达相一致的书面语著述。朗读汉语作品时,如果听众是文盲,那么他根本听不懂书中所写的内容。这并不是由于听众不理解文章,而是因为汉语作品并非写给人听,而是让人自己去阅读: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不是用口语书写,而是按照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模式的书面语。
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会因为说话人的亲人、朋友和同乡不明白他的话,而像与聋哑人对话一样逼他写出来。有些人在阐述汉语的这一特点时根本不明所以。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方言土语。除了固有词汇,每个词汇和短语(“走”这个词北京的东城区说“去”,西城区说“开”——著者注)都有各自的发音和称谓:北京人说“十”,甘肃人说“四”(在北京,油毡子是一种“漆布”——著者注)。这样一来,如果对话双方都不懂书面语,在无法猜测对方说话的内容或者不熟悉彼此发啬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翻译帮忙,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对话。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书面语就起到了桥粱的作用。在我们看来,指责中国人愚蠢、不接受字母表的观点并不正确。中国人接触字母表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4世纪,而且对它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如何能让当时的所有人都会书面语呢?
汉语书面语同口语的区别在于,书面语中的词在一个听力最好的中国人(欧洲人就更不用说了——著者注)听来均是单音节,它们或者由一个韵母构成(e,u.iu等——著者注),或者由声母与带有上述韵母合成的音节构成(ba. bu,be),或者后面再加上一个声母(ban,ben),或者只有声母n,ng,因此经常(某些外来音节除外——著者注)会出现听不懂但能读懂的状况。例如,众所周知,一个“yi”音在汉语中就有一百多个汉字与之相匹配,不但每个字意义不同,而且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意义也各不相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两个中国人在对话,当一方说出“yi”音后,他就可以断定对方知道自己想说“一个”。书面语“一”的意义不在口语中使用。但是如果再按照四声发音(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词语,夹杂我们的字母和陌生发音——著者注),那么就需要在前面或后面补充上另一个单音节词,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新词,例如:一个,衣裳,意思,早已,礼仪,所以,等。
但是因为这些发“yi”音的汉字书写各不相同,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字,没有任何汉字与其组成词语,读者也能明白其意义。对此我们会另做叙述。口语中所说的某种树木、石头、鸟类等,一般由两部分构成——词根(一般为形容词——著者注)和词缀。但是书面语中只使用发音和对应该意义的词根;为了不必专门写出树木、石头、动物等词汇的全称,往往将这些单音节词的标志和意义结台起来;也就是说,书面语中往往使用单音节词。读者一读到带“木”字旁的“樟”,就知道这是“樟脑”的意思,与带“王”字旁的“璋石”和带“犬”字旁的“香獐”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音节词来源于双音节词(双音节词中的形容词在单音节词中作名词用——著者注)。
我们不应该忘记,古汉语的词大都是数量不多的单音节词;虽然是单音节词。但是在不同语境中因词根的不同而意义各不相同——即加上一个同义或近义的实词素,与原来的单音节词构成双音节词,以及加上一个虚词素,作为前缀或后缀构成双音节词。汉字的词根可以不考虑词源(死,使之死——著者注)形式和句法形式,不过由于书写的不同,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词义都得以保存。例如“节”字,原意为“截断”,然后有了“节子”(竹子和树木上的疤痕——著者注);后来我们又知道,“jie”字可以指“界线”“节制”“戒条”,甚至“戒律”等。发音同为“Jie”的汉字书写却各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混淆。汉字的意义非常多,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天或地”意指“天与地”(“喝”与“使之喝”,立与“使之立”——均用一个字表示——著者注)。在此我们以“对”字为例进行解释。“对”是“对立的”(敌对的——著者注)或者“相关的”的意思,但是我们想象一下贴在门上的对联的“对”,它可能是“对立的”和“相关的”的意思,因为“对”可以释义为“对答”“反驳”。这就说明,即便汉字的意义是确定的,但是它在应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都可能具有其他意义,例如,“道”字意指“道理…方法”‘道德”。此外,如果我们说,汉语书面语来源于口语中的双音节词(或者多音节词,类似文学上的迂说法——著者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书面语单音节词就不能彼此,合构成双音节词。相反,与口语相比,这种结合在书面语中使用更多,不过往往让人听不懂。例如,在口语中习惯说“喜欢”,书面语中却变为“欢喜”,然后出现了“喜新”“新欢”“欢欣”“欣悦”等口语中根本不使用的词。
上文中曾说过,声母的不同会导致不同地方发音各不相同(“是”与“系”——著者注),书写也不相同,而这成为保存有方言(特别是中国古代各诸侯国的文字①——著者注)的书面语的共同财产。
由此我们明白,一方面,词的构成除了存在于单音节字中的本义外,还会出现其他词根的变换;另一方面,同一个词根的本义应该有不同发音的汉字相对应。而这恰恰是造成汉字同音字较多的原因。
如果认为,以副词为首的单音节词没有任何变体,即单音节词始终如一,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