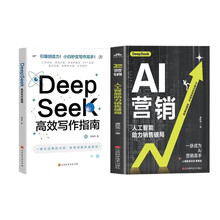(二)民族国家的教育权占主导地位
国家确立教育权的过程以义务教育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形式。制度是指具有合法性的社会性行为规则。制度变迁的前提假设是有利可图。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一组彼此相对的制度变迁模型,皆指对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新制度安排的创造①。前者是政府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自上而下地强制执行的制度变迁模式,后者是非政府组织、个人在政府允许的制度环境中,通过自发行为逐渐形成的制度变迁模式。不管是哪种制度变迁模式,都是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义务教育制度本质上是人们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一部分,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政策来规范教育主体的行为,形成一套相对固定的互动机制,是国家、社会、国民实现正和博弈的产物。对于国民而言,义务教育实乃国民之义务。义务教育实质是国民教育在法治社会中才形成并普及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此之前,通常底层民众的受教育权与教育权处于自在状态,只有强迫教育,没有“义务教育”。
1.义务教育之“义务”
早期义务教育以国家教育权为中心,强迫国民接受。家长或监护人送儿童入学,仅仅是一种义务。当时把受教育与当兵、纳税并列为国民三大义务②。西方市民社会在经历工商业革命时逐渐形成了法治社会。在宪政体制下,义务教育获得了较以前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发展环境。在法治阶段,义务教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义务本位阶段,家长有送适龄儿童入学的义务,而国家则无为适龄儿童提供学位的义务;第二阶段是权利本位阶段,国家负有为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提供学位的义务,家长具有让适龄儿童接受适当教育的义务。在第二阶段也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家长送适龄儿童到学校接受教育;第二种是家长自己教育孩子,其形式被称为家庭学校。家长送自己孩子到学校接受教育的义务逐渐转变成为家长选择自己孩子接受何种教育时自己的教育权及其孩子的受教育权。
德国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以教育为凝聚国民意志、提升国民素质、形成民族国家意识的途径。从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由孱弱走向强盛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受教育机会逐渐扩大直至普及的轨迹,也能观察到民族国家是如何通过强权确立对教育权的垄断地位。在国民教育权与受教育权的意识没有完全觉醒的情况下,以强权为后盾,以法律为形式,以免费为妥协条件,民族国家的政府成功地从宗教和家长的手中夺得了对学校的控制权。国家通过义务教育将未成年的社会成员纳入社会共同生活的轨道之中。这种共同生活走向何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所倡导和践行的“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被奉为圭臬,甚至走向极端。在铁血政策的牵引之下,义务教育服从国家利益,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培养集体利益的忠实服从者。
2.家长的教育权
家长的教育权可以被视为自然权,亦可以被理解为亲权,不仅具有个人权利的特征,还具有公益性。家长首先是人,其次是公民,然后是特殊法律对象。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家长因生殖的关系对孩子具有天然的最初的抚养与教育的权利。生殖是一种极为普遍和正常的繁衍现象,生育和养育子女对于每一位父母来讲具有不证自明的人权。在现阶段,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种事实上昭示着自然人对自己子女的生育与抚养的权利都不会被否决,它是普适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因而家长的教育权具有个人权利的特征。同时,儿童并非是由自己意志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家长对儿童的发展具有绝对责任。在儿童没有完全责任能力之前,家长不能放弃这种具有责任性质的自然权利。因此,家长的教育权实质上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种义务不仅是对儿童而言,还对社会其他成员而言。子女的社会化进程顺利,不仅有利于个体发展,也有利于社会健康运行。因而家长的教育权具有公益性。家长的这种教育权主要体现在作为监护人对儿童受教育权的保护能力。具体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对教育内容、教育形式的选择权,突出表现为家庭教育与对学校教育的选择权。这种权利相对应的义务主体是除家长之外的其他有能力影响到教育权的分享的自然人或法人,比如国家、教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