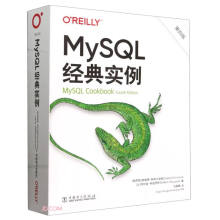将以上几段引文的意思总结起来看,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首先,在一个宣扬集体和一统的时代和社会,弘扬个性和自我的诗歌自然会遭遇尴尬和打压;但是颇为悖论的是,诗歌又往往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一种装点手段或颂扬工具,诗人和诗歌于是便时常处在强烈、刺目的政治聚光灯之下。其次,诗歌是检验人的精神修养和道德水准的一把标尺,是让人保持良心和尊严的一种手段,一个时代诗歌水准的高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道德和文化水准。最后,诗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布罗茨基称曼德施塔姆为“文明的儿子”,正是就这层意义而言的。诗歌是最为简洁的文学形式,因此也就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文化记忆手段。曼德施塔姆有一部文论集题为《词与文化》,他认为“词与文化”之间的桥梁就是诗歌;另一方面,就像曼德施塔姆就“什么是阿克梅主义”的问题给出的著名回答一样,诗歌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念”,就是一种最精致、最高级的文化记忆手段。如此一来,弘扬个性的诗人在一个戕害个性的时代蒙灾受难,传承文化的诗歌在一个敌视文化的社会四面楚歌,似乎就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了。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作者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已大规模呈现”,而其两个主要表现形式或日实施手段,“即消灭富农运动,以及文学的组织化”。(《灭亡之路》)前者是对物质文明的毁灭,后者是对精神文明的毁灭。作为一位“大恐怖”年代的见证人,曼德施塔姆夫人展示出的那些年代的生活场景和社会氛围让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有没有安装窃听器。当我在战后来到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录音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查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恐惧得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有时会让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直到如今,我们的这一病症仍然没有痊愈。”(《理论与实践》)“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人遭受了最卑鄙的折磨:他们被割去舌头,他们被命令用剩下的舌根去颂扬统治者。”(《颂诗》)“大恐怖就是一种恐吓行动。为了让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状态,就需要让牺牲者的人口达到一个天文数字,就要在每个楼道里都清除掉几户人家。在被铁帚扫过的家庭、街道和城市里的剩余住户,一直到死都会甘做模范公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