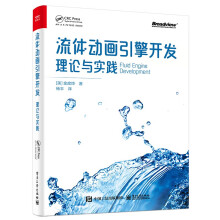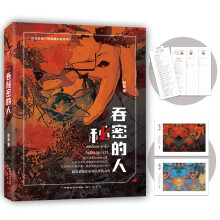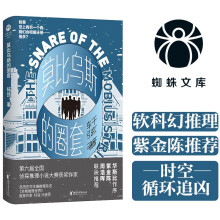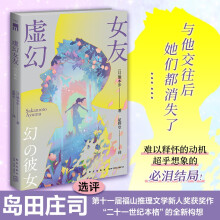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历来有一个误解,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就中国而言,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文学的功利性即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孔子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某种意识上,我们的圣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将文学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直接对应起来,片面强调了文学的直接功利性。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文学的社会功能就被强调得更为明显和直接了:“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这种文学功利观,成为中国几千年社会的主流,支配着人们对文学的衡定标准,一以贯之。以至于,柳永因为他的创作无关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科举之路上就被判了“死刑”。殊不知,柳永的诗词,正是一个人情感的真实流露,正体现了文学的心灵功能呢。文学的功利观的强调,直接导致了历代统治者对文学的密切关注(赘语)甚至直接控制。也就上演了一个个无休止的“文字狱”,文人们轻则断送仕途,重则丢了脑袋。所以,几千年来,只有文人失意之后才会在文学中流露出心灵的一角,这种珍贵的“真”人、真性情,则往往又被压抑与掩盖。到了晚清,由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文学的工具性和实际功能再次强化,被赋予了救国救亡的使命。如梁启超就强调文学与新民的作用。任公所谓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法不够精确,行文中也过于武断,没有认真的分析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到底与人心之间有怎样复杂微妙的关系。这种粗疏的提法容易产生流弊,事实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为文学的工具化功利化张目。
五四时期,现代化的极端焦虑也对文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期待和强迫。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异军突起,文学的工具化被突出地强调,有文学家就明确宣称文学要成为普罗大众斗争的工具,文学就是阶级的传声筒。君不见,“匕首”“投枪”一度成为对某些文学作品最高的评价,最高的赞誉。抗战军兴,文学自然被要求成为抗战的武器。这种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功利传统延续滋长,发展到极端,就出现了“文革”期间的文学荒漠化。“样板戏”“一枝独秀”了,文学则完蛋了!
对文学的看法,中国如此,那么西方又如何呢?在西方,摹仿说与反映论一直在文艺观念中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就强调文学艺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摹仿,强调现实对文学发挥的主体性作用。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文学的能动“反映论”,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能动性反映。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被极端化和庸俗化的反映论甚嚣尘上,一度被奉为圭臬。这种直接将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等起来的做法,占据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部分时间。
二者的根源是相同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社会观、功利观还是西方的摹仿说主流观念,都强调文学是现实的直接反映,强调文学对于社会的直接功用,这种观念必然导致将文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工具,使得文学承担起本来无法承担的重任,进而也导致对文学创作的控制,文学失去了自由。社会和人就彻底失去了文学。让文学归位,就成为必要。
……
展开